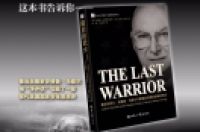
克雷佩尼维奇和沃茨所著《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和现代美国国防战略的形成》具有优秀传记作品的不少要素和条件。其中首要的——也是一般历史学家和记者的传记作品中并不多见的,是两位作者作为马歇尔的门徒、同事和智识伙伴,也作为美国战略研究的局内人,对马歇尔的经历、工作和环境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尤其对这位传主的思想有专业性的深度理解。而这并不是局外人能轻易做到的事。书中当然也像所有传记作品一样,清晰交代了传主的生平经历;但最优质和可贵的,还是对马歇尔思想和智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的探究和讨论,因而该书可被视为一部思想传记(intellectual biography)。这是再好不过的一种取径了。因为在笔者看来,对马歇尔这样一位战略思想家或者说战略“哲人”而言,他的思想即便不比他的事迹和功业更重要,也更有趣。
马歇尔的思想有多方面的牵连和意义,其中最直接的当然是“国际战略研究”(似乎越来越多地被称为“国际安全研究”,经常区别于以大学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政策相关性”的专业研究领域。作为这一领域的外行,笔者以往觉得这种为决策者服务,而且其组织平台很大程度上在政府内部(“净评估办公室”就设在五角大楼空间中心的“A”环)的研究领域,其基调风格应该是“务实”、直接、简洁的,其知识产品的主体应该呈现为办法、方案和操作具体性。然而在阅读中获得的马歇尔形象,颇有超出我此前的想当然之处:一个政府智囊人物,竟有那么浓重的“哲学”意味,能够调动那么多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来填充政策研究,对“战略”的定义和处理又是那么具有包容性和扩展性,把对军事战略的研究和思考的空间推广到那么大!以前读美国对外政策史,感到美国政府名目繁多的对外政策文件、情报文件和智库报告中颇有一些不乏“学院气”,喜欢呈现学术质量和“智性”。但马歇尔那种给人以凌压之感的智力高度、厚度、广度,确是笔者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所仅见。
对其平生志业所系的“净评估”,马歇尔本人总是回避给出结论性、定义性的说明,甚至不愿意“出示任何与某种方法相关联的东西,因为这种方法有可能会被机械地应用到净评估的过程中”。(第109页)对“净评估”做出严格规范性定义的确不易,但笔者所见一个研究者的描述颇为简明允当:“净评估是一种用以思考战略问题的框架,在对多种力量、运动和理念的回应中不断发展,把制度的、个人的、智识的和官僚机构的变化都纳入其中。”[1] 净评估是一种非常包容、灵活的松散型认知主张,是一只容纳了各种概念工具、研究手段和思想方法的工具箱。或者说,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methods),却没有专属的、排他的“方法论”。这种东西很难用“硬”社会科学和更“硬”的“行为科学”中单一、连贯、严整的“方法论”来形容,对曾经在智识上哺育了他的兰德公司的“硬学科”风格[2]无疑是一种偏离和超越。
马歇尔显然具有偏向 “软性”的智识风格,这与他的下列重要看法和倾向相匹配:他主张战略研究中应将识别和提出重要和恰当的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而清晰、详细的答案则可遇不可求;他认为范围狭窄的问题(如武器系统的效能和使用方法)远远不够或者意义不大,而偏好和看重一些包容广泛的问题(如经济基础与军事效能之间的关系);他对美国军事学术当中盛行的定量指标、理性选择和系统分析等高度确定性的方法往往持怀疑态度,或者倾向于严格限定其应用范围;相反,对理论性社会科学家鄙薄的经验性和“情境具体性”(context-specific)知识、历史方法与描述性方法,乃至于基于历史经验的直觉判断,却很是注重并善于使用;他对很多情况下精确预测的可能性和价值予以怀疑和否认;他坚持净评估不提供“药方”和“关于操作步骤(programmatic)的建议”,而只提供“诊断”,即对问题和趋势的判断性意见,以及对趋势中存在的“机遇”的说明。(第6页,第131页)就此而言,我总是觉得“net assessment”还是应该翻译成“网评估”,以标识马歇尔方法中的复合、包容和软性——或者说在“艺术”和“科学”的平衡中更偏向前者(第138-139页)——的特征。用以赛亚·柏林的著名说法,如果说兰德充斥着“刺猬型”的头脑的话,那么马歇尔的智力风格就是“狐狸型”的。
政策研究和智库工作经常被认为面向行动、方案,也就是关于“怎么办”(how)的研究。但是马歇尔显然更偏向 “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的论说。(这里也受王缉思教授的启发,在我们对他的一次访谈中,他指出大学智库尤其应该关注what和why,而不必去理会关于how的问题。)马歇尔是智囊人物中的“求道者”,这当然是其超拔的“智性”的一种表现。他显然像很多哲人那样,将“道”置于“术”之先、之上。而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思考如果足够深入而高远,就往往会或多或少具有“本体论”哲学的意味和性质。马歇尔“净评估”当中当然散布着对战争、和平、军队国家行为体,乃至于人性[3]的本体论思考。
然而马歇尔思想当中更引人注目或者更有价值的,其实可能还不是关于what和why的本体论部分,而是其关于“怎样思考”(how to think)的思考,也就是其中的认识论部分。在这里,马歇尔其实和19世纪末以来的很多思想巨人一样,是对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对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易谬性(fallibility)和困境有着深刻的体认,具有战后美国军事学术中弥漫着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氛围中少见的“认识论谦卑”(epistemological humbleness)。
而要完整理解马歇尔的认识论思考,还要将其置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脉络中,其中首要的是跨学科思想的演进及其机理。19世纪晚期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在进入大学的同时步入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进程,形成了明晰、强固的学科间边界。现实世界被各个主要学科在概念上加以抽象、提取和分割,并奉自然科学为典范,追求精确性、确定性和通则,理论的趋势越来越强。这些学科都立足于很大程度上隔离于现实世界和公共生活的大学体系中;在“效率来自分工”的律令、“为知识而知识”(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的信念之下,知识人在制度上和观念上大都安居于学科藩篱之中。然而,这种趋势也很快在大学和社会科学共同体内外引发不适、反思和试图加以矫正的努力,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多种形式、在多个方面出现关于跨学科的认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而跨学科态势一方面来自学科体系中各成员之间的交往互涉(cross-fertilization),来自各个学科和次级学科自发产生的扩张和深化趋势;另一方面,其动力和理据可能更多地还是来自现实世界对自闭的学科范式构成的强迫和压力,来自学科在面对现实提出的问题和需求时暴露出来贫乏、短缺和无能为力。
专业性、学术性的学科只能给自身而不是现实世界设定边界;现实世界向人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从来不按照学科的边界来设定,而具有学科很少顾及、也从来不能有效应对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而且,正如战后初期美国社会科学的领袖人物罗伯特·霍尔所说的,社会科学标准学科作为知识的一个个“垂直支柱”,相互之间存留着很多未经照见的大片空隙地带,经常需要新的研究领域产生来予以填补。而这些新领域又经常以原有学科和研究领域为理论源头、方法工具库(及所谓“上游学科”)以及知识素材来源。常规学科的缺陷和不足在危机和战争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一战、大萧条和二战都同时具有动员专业学术知识参与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学科交往和互涉,以及增生新的知识领域的效应。
建制化学科自我改变固化状态、自我更新、自我扩展的动力终究不足;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正在这里得以发挥和凸显。19世纪晚期以来美国一个基本趋势是大学在学术和知识生产中占据主导甚至垄断性地位。但自20世纪的危机事态,特别是国际危机和战争又因此而产生提升政府在知识生产和学术生活中的分量和影响。这种影响又有三个基本表现,一是“大科学”,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二是跨学科,政府部门的课题和研究项目成为学科知识的集成和组装平台;三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增生,而这更多地发生在政府的制度平台之上或其卵翼之下。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OSS)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就按照实际问题而不是学科加以组织,在其中工作过的约900名各学科社会科学家在那里从事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工作,战后返回大学时更把跨学科的理念和实践方法带回学院学术界。OSS的平台就是战后跨学科的地区研究主要起源之一。战后社会科学中兴起的其他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和进路,如传播研究、敌情和士气研究、发展/现代化研究、系统论、博弈论和运筹学,等等,都是对政府和军队知识需求的回应,及其知识议程的延伸。美国的“反国家”政治传统本来向来阻滞政府供养和介入学术。但二战以后政府和军队中的一些部门对动员和利用知识方面有着特别高的期待和特别大的兴趣,乃至于脱开美国的成例而直接出面供养和组织知识生产,比如战后新建的美国空军就挟带着对科学理性的迷恋而降生,培育出一种风格独特的智性军事文化——兰德公司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
马歇尔所属的战略/安全研究领域,还有这个领域以及马歇尔本人与兰德的渊源关系,也必须在政府介入知识生产和跨学科研究的繁荣两个方面相互连带、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加以理解。政府需求尤其会促生一些学院学术中并不存在的知识议程、研究领域甚至新的“学科”,而所有这些新学术分支都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跨学科性质,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机理性质的东西。政府介入知识生产、跨学科的大幅度推进,以及新的研究领域的增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二战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史的一个重要机理;对马歇尔、“净评估”和战略研究的理解必须置于这一机理当中。
马歇尔的思想和成就是在美国社会科学史的库存和脉络中发生的。就此而言,超拔出众的马歇尔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马歇尔方法主张中最核心的要素是非常宽泛而灵活的跨学科理念,而跨学科首先以学科和学科所提供的成果为基础。他是一个自我教育的典范,而这是在没有藩篱界墙的广袤知识空间中展开的。从家乡底特律的公共图书馆开始,经芝加哥大学、兰德,最后落脚于五角大楼,他的漫长生涯其实就是一个“通识教育”的过程。而通识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和智识生活中乃是作为专业化和学科分化的抗衡力量,作为跨学科智识主张的伴生物而存在的,芝加哥大学正是其重要策源地之一。经历了通识教育的头脑并不鄙视和弃置学科,而是以学科所提供的知识为资源、基础和训练平台。战后政府和军队影响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推进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渗透。马歇尔有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天赋、出身和深厚训练背景,对于“精确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全无隔阂。他的“认识论谦卑”,也是针对他的最初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领域。他的独特和高超之处,是以广泛的知识修养和高超的识断力,对来自各学科的知识加以鉴别、选择、动员、组织和集成的巨大能力。而且,被他所动员、利用和汲收的,还有在他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之外的知识和人员。他从不命令和限制他的手下和门徒,而只是予以启发和“间接的指导”(第227,288页),这或许与他平和温润的性格有关,但很可能更多地来自他对他人的专业和智力有着纯粹理智上的尊重。用中国人的话来说,马歇尔颇有“法无定法”或者“游于艺”的味道,但这是一种由专精向博通的过渡和升进,是一种基于高等知识、精确科学,因而得以超越它们的状态。这与我们常见的以表面上的“宏观”“综合”或者“实用”来逃避专业知识、专精研究,实际上大而不当、疏阔空洞、缺乏专业含量和智性品质的“智库”工作不可同日而语。
马歇尔的个案还有更广泛的“知识社会史”意义。这涉及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美国不断培育,也历经起伏兴衰的知识和行动、学术和政治之间沟通互动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机制。马歇尔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美国人用以使专业化知识注入国家权力的发达制度机制,看到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不停息的“旋转门”。但问题不仅仅止于制度方面,这里还有深刻复杂的文化问题,或者说“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问题。在现代专业和职业领域高度专业化和分化的条件下,理念和实际、思想和行动、智识人和决策者之间往往有深刻的分裂和对立,官僚机构、军队和政治领导人不可避免地有自发的、制度性的反智因素和倾向,研究和决策之间不仅存在着有时非常漫长的距离(尽管马歇尔作为研究者是处在距离决策最近的位置),而且这当间其实有着无数有形无形的障碍和干扰因素。对这个复杂问题本文无力处理,但马歇尔本人在这方面的一个察见很有趣也很重要:他可以把“马”也就是决策者引到水边,但无法迫使他们喝水,也就是无法促使它们思考。不喜欢给出“药方”和具体政策方案的马歇尔,与其说是中国人概念中的“策士”“谋臣”,不如说是一位向决策者不仅提供知识和分析性意见,而且以温婉含蓄的方式提供关于理念和思想方法的指导和启发的教师。这种“师生关系”不是强制性的,它首先取决于决策者有没有做学生和接受这种“教育”的意愿。而我们都知道,这种意愿的发生和维持,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智库”里有多少“智性”,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
[1]Mie Augier, “Thinking about War and Peace: Andrew Marshall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for Net Assess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2, No.1, pp.1-17.
[2]关于兰德公司的“硬学科”特征,参见Alex Abella, 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3]马歇尔具有“进化论和文化论的人性观”,Augier文,pp.8-10.
安德鲁·马歇尔
出生于1921年。他从来不是一个军事意义上的武士,尽管他曾是美国“民主兵工厂”中的一名“战士”,也是一个“冷战斗士”,但他更像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所描述的“伟大的一代”中的最后一个人。这一代人成长于大萧条年代,年纪轻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勇敢地面对美国与苏联之间“漫长的冷战”。在作者看来,这一代人典型的特点就是具有迎接挑战的决心,不是因为这些挑战很容易,而恰像肯尼迪总统说的那样,“因为它们很难”。马歇尔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中最后一个在政府高层供职的人,因此,作者将本书命名为《最后的武士》。
内容介绍
2015年,美国珀修斯集团基础书局首次出版英文版。
201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首次出版中文版。
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是五角大楼的一个传奇。他任净评估办公室(五角大楼内部智库)主任一职逾40载,辅佐12任国防部长和8任总统,始终位居美国战略思想前沿。在兰德公司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马歇尔帮助确定了美国核战略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直到今天仍然适用。赴五角大楼任职后,他又率先提出了“净评估”的概念和方法,由此构建了分析美国与苏联之间长期军事竞争的新的理论框架。冷战结束后,马歇尔通过“净评估”成功预测了军事方面新兴的颠覆性转变,包括新军事革命和中国作为美国重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崛起。
马歇尔之前的两位部下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和巴里·沃茨(Barry Watts)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访了马歇尔本人,掌握大量一手史料,同时还得到史密斯基金会的资助,获取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首次通过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最为关键的事件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来讲述马歇尔的故事,揭示了马歇尔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国防战略幕后顾问的思想发展轨迹,并由此提供了从冷战初期到当前美国国防战略总体变化情况的独特内部视角,同时展示了美国国防机构演变的历史。
作者介绍
[美]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
(ANDREW KREPINEVICH)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主席。著有《七个致命想定:一位军事未来主义者对21世纪战争的探讨》和《美国陆军与越南》等多部军事历史和战略著作。现居弗吉尼亚州利斯堡。
[美]巴里·沃茨
(BARRY WATTS)
曾任五角大楼项目分析评估主任,2002年起任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高级研究员。沃茨在军事历史和战略领域同样著作颇丰,著有《克劳塞维茨的“摩擦”与未来战争》等。现居马里兰州毕士大。
译者介绍
张露
上校,现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兼《战略研究》杂志主编。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战略学博士,并在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过专项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发展战略、地缘政治理论与中美关系。在《太平洋学报》《现代国际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等发表学术文章五十余篇,代表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中西正义战争思想比较分析》等。
王迎晖
上校,现为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外军系副教授。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军事科学院,美国研究和战略研究双硕士,国际战略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战略、东南亚地区安全、东盟研究。独立或参与完成著作、译著十余部,发表学术文章七十余篇,代表作为《冷战后美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研究》《论“一带一路”构想布局中的东南亚地区战略运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