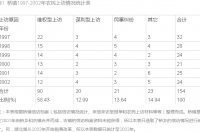大约20年前(即上世纪末),曾任新加坡外交官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出版了一本题为《亚洲会思考吗?理解东西方的分歧》的著作。在作者看来,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横跨从日本、印度尼西亚到阿拉伯世界,涵盖了伊斯兰、佛教、儒教和印度教等几大文明,人口占了全球的60%。(当时的)经济总量即将在未来15年内超过欧洲和北美。但是,西方人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对亚洲人的态度依然如故。作为外交官的马凯硕因此有感而发,希望促成西方对亚洲的新思考。
今天,离这本书的出版20年过去了,不仅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印度也正在快速崛起,但“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如果说亚洲人不会思考,很多人必然会感觉到被“侮辱”,并且这样说也不公平,因为如果说亚洲人不会思考,亚洲的变化又如何解释?亚洲书写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故事。
二战之后,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之后是“亚洲四小龙”创造了公认的“东亚奇迹”,之后便是中国的经济奇迹,现在全世界的眼光又落到了印度的崛起上。但问题在于,即使亚洲人有思考,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亚洲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即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话语感到不满意,但在行为上一切依然以西方话语为依归。
马凯硕的《亚洲会思考吗?》想给西方读者传达出“亚洲会思考”这样一个信息,希望西方对亚洲事务做重新思考。如果那样,这本书的书名应当为《西方会思考吗?》而不应当是《亚洲会思考吗?》。但从现实来看,这本书的书名最也恰当不过了,因为现实的情形是:不会思考的不是西方人,而是亚洲人本身。
这本著作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在亚洲所产生的影响。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西方人对亚洲不是不会思考,而是经常做“错误”的思考。当代亚洲的崛起是西方人最为关切的事情,无论是日本的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都在西方得到相当充分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当代中国崛起的研究了。
同时,对亚洲事务的关切也充分反映在西方诸国对亚洲政策的变化上。相比之下,亚洲人本身除了照抄照搬西方话语之外,对亚洲经验的“知识化”可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有关亚洲的话语仍然为西方人所掌握。
所以,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西方对亚洲事务的“不当思考”,而在于为什么亚洲人有丰富的实践但不会思考。
一句话,亚洲还没有脱离西方的“殖民”,或者说西方仍然在“殖民着”亚洲。
亚洲的两个殖民阶段
就殖民来说,亚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近代以来的“被殖民”阶段,即西方强权的殖民地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大多亚洲国家被西方国家所打败,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即使中国也成为了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地国家”。所要强调的是,这个阶段是“被动”的殖民。
第二个阶段即二战之后的“主动”的思想殖民阶段。在这阶段,通过亚洲各国的反殖民运动,物质意义上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思想上的殖民地主义根深蒂固,不仅无意识地存在下来,而且变本加厉。在“被动殖民”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抵抗,但在“主动殖民”阶段,不仅毫无抵抗的迹象,更有自我“摧残”现象的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存在已久、产生的原因也很复杂,但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首先是近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亚洲国家力量弱小,无法改变西方持有的亚洲话语权。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俄国)的亚洲国家。日本曾经试图通过把欧洲列强赶出亚洲的方法,确立自己的亚洲霸权,即建立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没有帮助日本确立亚洲霸权,其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更是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战争。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被“吸收”进西方阵营。尽管日本战后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无论内政和外交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制约。日本之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也基本上属于西方阵营,无法改变现状。进而,为了让西方接受他们,这些经济体往往采用“投降”政策,把自己伪装成西方,即尽量强调其和西方的雷同之处,而不敢张扬其和西方的不同。
当然,其中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主要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李光耀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可以视为是亚洲“异见者”的政治宣言。这些“异见者”还包括当时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和日本一些政治人物。
在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做过努力,把“亚洲价值观”学术化,试图来解释和叙述亚洲的成功。不过,“亚洲价值观”不仅遭西方的围堵,而且也遭到亚洲那些追求西方式民主的政治人物的批评,主要来自韩国和台湾,因为这些社会当时正经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浪潮”。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价值观”便在大众媒体上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亚洲一些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对西方式民主自由的信仰和追求。他们简单地把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强大和亚洲国家的落后归结为民主与自由,即前者实现了民主自由,而后者没有民主自由。亚洲很多追求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并不知道西方民主是如何产生、如何运作的,但一旦民主自由成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无论怎样也不会对西方产生一点点怀疑,他们的选择是全盘接受。
这也很容易理解,只有那些理解西方民主的政治人物(例如李光耀),才会对西方制度持批评的态度。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确一些亚洲国家和社会建立了民主体制。不过,尽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些亚洲民主并非西方式民主,这些社会也要伪装成为西方民主,尽量不站在西方的对立面。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并不符合西方政党轮替的民主概念。西方学术界对日本民主一直持批评态度,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西方政界,这个事实也说明日本“伪装”的成功。
第三,利益和话语之间的冲突。亚洲这些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整个冷战期间属于西方阵营,它们各自从西方阵营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它们的发展更离不开西方阵营。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社会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量,不想塑造自己的话语权。很显然,一旦具有了和西方不一样的话语,就很容易主动地或者被动地被西方视为“对立面”。一旦这种“对立面”形成,就必然会影响这些社会在西方主导的体制内追求自身的利益。
亚洲国家之间无共识
第四,各种冲突阻碍着亚洲国家之间的共识,没有共识,自然就没有亚洲话语权。亚洲是一个多文明、多文化的地区,并且各国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相差甚远。多文明和文化使得它们之间少则缺失共识,多则导致冲突。这种情况既反映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大国之间,也存在于东南亚各国之间,或者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
即使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北亚国家之间,也因为历史和战争的原因而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亚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赋权西方,使得西方总能找到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在殖民地结束之后继续主导亚洲事务。同时,也是因为亚洲国家之间的冲突,使得一些亚洲国家主动寻求西方的帮助来对付另一些亚洲国家。这种现象自近代以来一直很为普遍,存在于整个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更不用说包括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亚洲了。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亚洲教育市场的殖民地主义。近代以来,亚洲精英人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另一部分是从内部成长起来的。但无论起源如何,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接受了西方价值观。二战之后,亚洲国家独立了,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系统并没有独立。一些国家进行了“去殖民地主义”运动(例如新加坡),但教育系统的独立性也是有限的。更多的国家则是主动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系统。
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仅在于西方教育系统在客观上较亚洲先进(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更在于亚洲国家没有自己的信心和能力,把自己的发展经验提升成为以亚洲为经验基础的社会科学。尽管亚洲国家的学者也提出了“东方主义”的命题,并且也一度盛行,但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后来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都是解构型的,而非建设型的。
就是说,这些理论仅仅抱怨西方话语霸权,但并不能成为建立亚洲话语的理论基础。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然不能改变。亚洲国家还没有能力发展出自己的评估系统,一些以西方为标准,甚至比西方更为西方。自然科学还说得过去,但社会科学则令人担忧。例如,较之西方,亚洲的教育市场大多由官僚主导,官僚主导的教育市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主要是排名),对本国的教育系统进行主动的“殖民化”,一切以能够在西方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能够发表西方式的文章为最终依归。这都使得亚洲教育市场俨然是西方市场的内在一部分,没有看到任何独立的迹象。
西方教育市场的强大在于其思想,而非思想的学术表述方式。而亚洲社会则以极端机械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表述方式,在这个接受过程中,亚洲的思想也不知不觉地被西方“社会化”了。
因为这些,今天亚洲只有发展、没有思想的局面并不难理解。这种局面也使得亚洲国家处于一种极其难堪的状态:尽管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不能解释亚洲经验,但人们仍然不得不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今天中国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中国实在太大了,不能像早些时候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伪装”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一点也不想“伪装”自己。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做法刚好相反,其他亚洲国家强调的是自己和西方的雷同,而中国张扬的是自己和西方的不同。不过,中国并没有能够让西方(甚至亚洲国家)理解和接受的“故事”。这使得今天的中国和西方(及那些接受西方话语的非西方国家)处于意识形态的对立。
当然,未来印度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情况。尽管印度到目前为止,仍然被西方视为最大的民主,但随着其发展,印度和西方的冲突也只是时间问题,而非可能性问题。如同中国,一个庞大的印度也很难“伪装”自己。
“亚洲”的概念本来就是西方殖民地的产物,很多亚洲国家也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但如果亚洲不能从思想上独立出来,如果继续没有自己的思考和思想,一切以西方为依归,前途很难说是光明的。搞不好,亚洲很难避免“中东悲剧”,即被西方“分而治之”。今天,当亚洲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时候,这种危险性也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