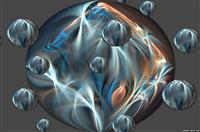
圆桌会谈:对话爱德华•威滕(七)
爱德华·威滕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自然科学学院教授
大栗博司 卡弗里数物连携宇宙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户田行信 卡弗里数物连携宇宙研究所助理教授
山崎雅人 卡弗里数物连携宇宙研究所助理教授
大栗:早在1970年代晚期人们就发现朗兰兹对应跟S-对偶有所关联了。你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呢?
威滕:我并没有全盘讲出我跟迈克尔·阿蒂亚在1977年的互动。他告诉了我两件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事情。一个就是蒙托宁-奥利弗的文章,另一个则是朗兰兹对应。这一对应在数论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但我却从未听说过。他注意到朗兰兹的对偶群和进入到蒙托宁-奥利弗猜想中的对偶群(之前由彼得∙戈达德、珍·纳依茨和奥利弗引入)是完全相同的。基于此,阿蒂亚猜测朗兰兹对应跟蒙托宁-奥利弗猜想是有所关联的。
大栗:这是在1970年代晚期?
威滕:是在1977年12月或是1978年1月。那是我第一次访问牛津大学。
大栗:你在那时就已经认真对待朗兰兹对应与这一规范理论动力学之间有所关联这回事了?
威滕:好吧,我没有忘记它,但既然——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对蒙托宁-奥利弗对偶是有所猜疑的,我没有认真尝试去将它关联到朗兰兹对偶,而我也就没有试图弄清朗兰兹对偶是什么。一直到1980年代晚期我都没有学到关于这些内容的更多东西。接着我学会了朗兰兹对应的一些皮毛。如果你知道哪怕一丁点朗兰兹对应和哪怕一丁点黎曼面上的共形场论,你都能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我写了一篇以此为动机的文章,但之后我意识到我的理解实在太过肤浅,得不出任何深刻的东西,所以我放弃了这一问题一些年。
大栗:我记得我1988年和1989年在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的时候,罗伯特·朗兰兹他本人其实对共形场论相当感兴趣。不过,我不确定他究竟对那个方面感兴趣。
威滕:我不认为他是被朗兰兹纲领所激发的。不过我觉得他的工作很有影响力。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并没有具体做出任何重大突破,他帮助找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刺激了随机洛纳演化的后续发展。随机洛纳演化在数学上具有重大影响,甚至还启发了物理学家思考共形场论中一些问题的新方法。我认为朗兰兹是这一工作背后的推动者,但我不相信他对共形场论的兴趣是被朗兰兹对应或是规范理论对偶所激发的。这是我跟他多年互动所得出的印象。
如同我已经评论过的,在1980年代晚期花了一些时间试图发展共形场论与朗兰兹对应之间的类比之后,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说,我所发展的这一类比的形式过于肤浅了,所以我停手了。但是接着在1990年前后,我听说了亚历山大·贝林森和弗拉基米尔·德林菲尔德关于几何朗兰兹对应的新工作。首先,它证实了我对这一对偶在物理中意味着什么的理解确实太肤浅了。他们所得出的比我对朗兰兹对应和共形场论的相当粗糙的类比远为深刻和细致。他们的工作证实了我所知道的物理是相关的。但我又很困惑,因为他们使用使用共形场论的方式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们研究处在负整数级上的共形场论——在物理中正整数在这里才更自然——并且使用它的方式看上去相当古怪。
如同我昨天在京都奖研讨会的讲座中解释的,多年以来,牵扯到琼斯多项式的“体积猜想”(从2000年左右开始由里纳特·卡沙耶夫,村上仁史以及村上淳等人给出和发展,而我大体上是听谢尔盖·古科夫解释的)一直困扰着我。尽管他们的论断表面上很像物理上动机充分的断言——事实上跟我自己在1988年关于琼斯多项式的原始文章中所做的论断很像——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差异。它们看上去拥有贡献指数级增长的复临界点,而这在物理中通常是不可能的。我不确定这一点是否也让其他人感到困惑,但它让我困惑不已。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好问题,因为我最终找出了一个好的解释,而这也成为了我得以利用规范理论来理解霍万诺夫同调的转折点。
贝林森和德林菲尔德关于几何朗兰兹的工作也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困扰着我。他们使用了物理学中熟悉的要素,但他们使用的方式看起来并不恰当。看起来好像某人拿了一堆国际象棋棋子,或者在日本这儿我应该说一堆日本将棋棋子,然后把它们随机地放在棋盘上。棋子排放的方式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这让我很困惑,但我不知从何着手。
事实上,我能理解的贝林森和德林菲尔德所说的极少一部分让我猜测奈杰尔·希钦的工作跟它们或许是相关的,所以我向他们指出在希钦的文章中已经构造出曲线上丛的模空间上的对易微分算符。换句话说,希钦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量子化了他几年前构造出的经典可积系统。尽管我对贝林森和德林菲尔德所说的几乎完全不懂,我确实将它们与希钦的工作关联起来了,而且实际上,在他们关于几何朗兰兹的那篇非常长的,未发表但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奠基性文章中,贝林森和德林菲尔德非常大度地致谢了我,远远高估了我所理解的部分。真正发生的一切是,基于一个猜测,我跟他们说起了希钦的工作,然后我想这使得所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显而易见了。可能他们觉得我知道一部分这些内容,但我并知道。不过无论如何,那些年存在充分的理由认为几何朗兰兹和物理学有关,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仍然没法弄懂它。
大栗:那么,是什么激发你回到这一问题的?
威滕:十年后在高等研究院有一个针对物理学家的几何朗兰兹研讨会。你去了吗?
大栗:我被邀请了,但日程上有些冲突,所以我没去。我错过了。
威滕:有两个长系列的讲座,接着又有几个离群的。长系列做得非常好,但它们并没有帮到我多少。马克·戈瑞斯基做了一个长系列的讲座,旨在告诉物理学家什么是朗兰兹对应。对于我来说唯一的麻烦是,假定听众除了域(在代数的意义上)的定义基本上对代数学一无所知而你用几个讲座能对这一主题解释到的程度上,我已经很熟悉朗兰兹对应了。也就是说我并不真正理解它,但对于你从零开始在几个小时里能解释的,我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所以从这些讲座中我并没能获得太多。
此外,爱德·弗伦克尔(他是这一研讨会得以举行的主要推动者)也给了一系列讲座,但就我而言,也基本上是关于随机摆放着棋子的将棋棋盘而已。我确实也没能从这些讲座中获得多少是因为我已经知道研究几何朗兰兹的人们是从一副将棋中拿出熟悉的棋子,然后把它们随机地摆放在棋盘上,就我而言。
此外还有几个不属于任何系列的额外的讲座。其中之一是由大卫·本-兹维做的。他告诉我们几何朗兰兹对应的一个所谓近似。我想他主要谈论的是另一个数学家迪玛·阿林金的工作。所谓几何朗兰兹对应的近似是希钦纤维化的纤维上的T-对偶。本-兹维是在一种特别的复结构中描述的,其中希钦纤维化的纤维是全纯的,因此这一T-对偶是一个全纯对偶。物理学家们已经知晓希钦纤维化的纤维上的T-对偶来源于四维中的蒙托宁-奥利弗对偶,而自从得知阿蒂亚1977-78年的观察结果,我当然已经意识到可能某种版本的朗兰兹对应会关联到蒙托宁-奥利弗对偶。但如何理解本-兹维实际上声称只从T-对偶推导出了几何朗兰兹对偶的一种近似,而不是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我开始猜测原因不过是本-兹维使用了一种错误的复结构来描述这一情况。具体想法是,希钦模空间上的这同一种T-对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给出某种复结构下的B-模型与某种辛结构下的A-模型之间的镜像对称。这一镜像对称理应就是真正的几何朗兰兹对偶,而并非其近似。事实上,我开始与安东·卡普斯京研究几何朗兰兹的原因正是他曾研究过两维对偶中的广义复几何。在那个框架下,一族对偶可以退化,而镜像对称可以退化为一种全纯对偶。
当你开始沿着这些线索思考的时候,这一切就很合逻辑了:几何朗兰兹对偶其实是一种镜像对称,并且可以退化为一种全纯对偶,而这正是本-兹维讨论的近似。不过仍然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最难的一个我之前已经描述过了。没有赫克算符你是无法着手朗兰兹对应的,所以你必须利用规范理论中的霍夫特算子来为赫克算符给出一个物理的解释。你还必须知道如何将一个复流形M的余切丛上的A-模型用M上的微分算符来解释。这其实跟卡普斯京之前做过的东西相当接近了。一旦这些要点都被弄清了,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已经相当清楚几何朗兰兹对偶是什么了。
但很难就此写出一篇文章来。这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在那一年里,我感到自己像是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但却无法向任何人解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仍然那样感觉,原因如下。具有弦论或规范理论对偶背景的物理学家能理解我和卡普斯京关于几何朗兰兹的文章,但对于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这一主题过于细节而不那么激动人心。另一方面,对数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主题,但却难以理解,因为太多量子场论和弦论背景知识是不熟悉的(而且很难去严格表述出来)。跟卡普斯京合写的那篇文章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遗憾地对数学家们保持神秘。
山崎:可能那意味着我们还得再等10或15年才能……
威滕:可能我们真的得等那么久。我觉得确实很难看出近期能有什么进展可以让数学家们领会几何朗兰兹的规范理论解释。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对霍万诺夫同调更加兴奋的原因之一。我解读霍万诺夫同调和几何朗兰兹的方案用到了许多相同的要素,但在霍万诺夫同调的情形,我想很有可能数学家们会在近期理解这一方案,如果他们对此很感兴趣的话。我相信它会更易于理解。如果让我来打赌的话,我认为我有很大的机会活着看到规范理论与霍万诺夫同调的工作被数学家们认可和欣赏,但在规范理论与几何朗兰兹的情形我想我得很幸运才能看到了——只是个人的猜测罢了。
户田:你是否认为你关于S-对偶与几何朗兰兹的想法能以某种方式应用到原初的朗兰兹纲领中?
威滕:我觉得那还有点遥远。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梦想着什么时候数论最终会与物理学联系上,但我怀疑这不会很快出现。
在物理学的很多个分支里,特定的数论公式出现过,而这些可能是我的梦想某一天会实现的迹象。但要真正让我激动起来的话,数论得设法以一种更结构化的方式进入物理学。我对一个特定的公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出现在一个物理计算中不是那么感兴趣。数论得跟物理学更加水乳交融才能让我兴奋起来,而我不觉得那会在近期发生。
在我的工作中,我专注于几何形式的朗兰兹对应是因为我能看出来在触手可及的物理工具的框架下真正有希望去理解它。将来某一天或许会有关于数论朗兰兹对应的类似工作,但很可能太多东西仍然缺失,而我不知道首先必须从哪着手。我感觉我之所以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我的关注点要集中得多,比起试图理解数论中的朗兰兹对应。
户田:S-对偶与几何朗兰兹的关系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数论这个研究领域看起来离物理学很遥远。
威滕:但是已经出现了很多进展,这些将来有一天可能会被视为重要的线索。最深刻的进展之一是由萨维蒂普·瑟西和迈克尔·格林在差不多15年前发起的,并接着由格林和许多合作者延续了下去。在原始工作中,瑟西和格林试图理解十维ⅡB型超弦理论的某些低能R4相互作用(这里的R是黎曼张量)。他们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我必须得说:其结果由权为3/2的某种非全纯爱森斯坦级数给出。尽管我的数论知识非常肤浅,但我认为这类结果更接近现代数论学家们的兴趣所在,相比于两维共形场论中通常出现的那类古典模形式而言。
大栗:那些不完全模性的对象也出现在数论中。
威滕:对的。许多数论学家钟爱的事物已经出现在物理学里,有些甚至出现在我自己的工作中。大量迹象表明我们作为弦论学家所研究的物理理论在数论中同样有趣。这些理论透露出数论中的某些东西,但我个人看不出有什么机会能在可见的将来以一种结构化的方法与数论真正取得联系。我甚至构想不出来取得这样的联系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也就不能准确地告诉你我们在什么地方还做不到,但我想做这个的时机还不成熟。
不管怎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专注于几何朗兰兹而不是数论方面,而且几何朗兰兹也已经足够难了。理解它花费了大量的工作,但我想理解它以后,数学家们所做的牵涉到表示论的几何层面的许多事情可以当成物理的部分而易于接受得多了。比如,我没能理解中岛启昨天在京都奖研讨会上解释的内容,但我觉得理解它需要用到我在探讨几何朗兰兹后弄清的一些事情。我不能担保,但它值得一试。
这里只提一件明显的事情,那就是尽管中岛没有时间解释整个的图像,在他的讲座最后他向我们提到了仿射格拉斯曼空间。霍夫特算符的同构类是与仿射格拉斯曼空间中的闭链相关的,所以当数学家跟你说起仿射格拉斯曼空间时,你可能想把你听到的至少部分内容用霍夫特算符来思考。我无法做出允诺,但我感觉这确实值得一试,去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视角来理解中岛所说的内容。
无论如何,我很确定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做并且需要去做,才能从物理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几何朗兰兹理论。事实上,贝林森和德林菲尔德关于几何朗兰兹的原始工作有些部分仍然没有被理解到令我满意的程度。这里我所想到的是在他们所谓的临界级(级为-h,h是对偶考克斯特数)上使用共形场论来构造某种B-膜(用贝林森和德林菲尔德的语言来说,就是关联到算子方程的那些B-膜)的A-模型对偶。大卫·盖奥托和我几年前得出了电-磁对偶如何作用于算子方程簇的一个合理认识,但我仍然觉得没有真正理解它与共形场论的关系。不过,在过去几年里,研究四维超对称规范理论及其六维近亲的物理学家们已经就临界级共形场论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许多发现,所以解决这一疑难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了。
大栗:我想我们还有大约10分钟。最后还有什么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