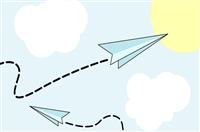和人一样,每棵树木,都有自己的年龄计算方式,它无需人来推定,而是自己述说;一环一轮,疏密间也决定了自己一展身手的将来。这好像和我们述说的主题相去甚远,其实不然,文化也一样,也有自己的计龄方式;坐落于世界各地的建筑,每一座在述说自己生前身后历史的同时,作为凝固的时间,绵延流转为文化的年轮。
十多年前,还在大学的时候,听到赵传的那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时只是为他高亢的嗓音、忧伤的味道所“震服”,其中自然也包括时下新鲜的流行元素;只是到了这把年纪,才忽然地感受到,当时的自己是多么肤浅,——“在钢筋和水泥的丛林里”,道出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反思,也道出了现代性的落寞和孤寂。主导20世纪的工业文明,作为其重要特征的分工,它所实现的简单化、齐一性,使每个人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相同部分,丰富的个体性最后符号化为《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它所简单化的还不只是人,甚至是人类社会中的任何部分。回到那首歌,工业时代的建筑也简单化为两者的集合——钢筋和水泥;如果说有其他的什么变化,几处的变化中也难以挥去纽约、巴黎、东京建筑的影子,那里不仅仅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世界建筑范式的张力中心。
我国的建筑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也许重复这样的话,很多人不高兴,但是,“明清以后无建筑”,是否是个事实,可以散见于凋落各地的“推陈翻新”。建国后的很多建筑打着“中西合璧”的名号,其实很多就是钢筋和水泥的集合,而且外形上屡试几何的方型图而不爽。至于建筑单体与建筑群体的差异、序列问题,建筑物与外部环境整体间的互构性问题,建筑与城市的功能甚或结构与审美间的兼顾等等,则更是一种奢谈。“明清以后”没有建筑并不可怕,至多是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形式和建筑审美风格发生断裂或缺失,可怕的是我们的建筑不再述说自我的历史,却成为西方文化年轮上的赘生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国度的不同建筑,在履行自身功能的同时,也述说着一个文明的特性和文化的变迁。我们不是建筑方面的专门研究者,无法就建筑本身或建筑的意义问题给出更多的建设性观点。但是,仅仅从记忆中抽取以往的习得也不难发现,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现了不同朝代的审美旨趣和价值取向,从中还可以触及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西安的半坡遗址,那些木架构遗址不仅使人联想起“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韩非子·五蠹》)”“上者为巢,下者营窟”(《孟子·滕文公》)等神话性的史料述说,还可以知晓一个文明初期的生存状况,看到人类早期的居住文化和墓葬俗成,以及它对今天的文化所形成的种种影响等;再有,杜牧的那首“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仅14个字,不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1400多年前的江南烟雨春景;同时,矗立于苏州城西枫桥镇的、四百八十分之一的寒山寺,不啻为“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南史·郭祖深传》)的时间化石,也为我们诉说着南北朝时那段东行转盛的佛教文化史;更有万里长城,除了作为民族的象征,同时作为世界国防工程的缩影,诉说着我国春秋以降冷兵器时代的国防史。
现实往往比文化的化石更为冰冷。前段时间北京的“会馆拆迁”问题,引起网络一片热议。会馆作为一个建筑群体,同样是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时间凝固,看到它,也就看到了明、清两朝以后的乡谊祭祀、科举会试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民俗和制度文化;不仅如此,每一个会馆作为个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履历,看到安徽会馆就会让人想起李鸿章曾是它的力推者,由此延伸并可能浮现于我们脑海的,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看到绍兴会馆才会知晓鲁迅曾是那里的过客,由此我们会联想到那个长有一字型胡须的新文化运动主将;看到浏阳会馆就会想起“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由此而呈现出戊戌六君子的历史群像等等。与发生在京城的现象相反,有很多地方正在充分地保护和开发“会馆文化”,如广州地区为“加快广州丝绸博物馆的建设”,而计划将广州丝绸博物馆放在锦纶会馆之内;扬州则大力推介“明清古城会馆产业”;而潮安会馆设宴140桌与同乡欢庆,为的是纪念潮安会馆建成46周年。而北京琉璃街、潘家胡同内的任何一个会馆,凭它们的“年纪”是否都值得过上一次这样的周年庆典,而不是在这场“拆迁运动”中灰飞烟灭?
这种担忧绝非呻吟于无病,而是类似的文化印记正被周而复始地抹除。
号称“长城之父”的楚长城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2010年3月,历经考古专家一年多的调查,分布于河南境内25个县区的楚长城的分布线路,逐渐呈现于世人面前。正是通过这些古代建筑,民族的记忆回到2600多年前才得以可能;通过这些历史遗迹,我们才找回了遗失已久的文化记忆;通过这些历史遗存,有关楚长城的研究,才得以从以往的历史文献研究、演绎推理研究转向实地的考察研究。但令人惋惜的是,时隔一年之久,“长城之父”也不得不为一些电力项目或“荒山绿化”等“发展”行为“让路”,已有多处成为了文化碎片。
不知道我们家国内这些尚存的古代建筑,是否也像“欧洲遍布着哥特式建筑的珍品,它们使数代人看了个够”(阿尔弗雷德·N·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已经让我们的国人感觉“饱得发腻”,而产生了审美疲劳?这里,我们不是针对“‘饮冰室’会馆拆迁”相关的新闻报道,也不是针对“楚长城”的未来宿命,更不是想给辖区的政府部门增加麻烦或施加压力。我们担心的是在这样一种“发展”的国家话语下,那些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发展派”,曲解了科学发展的真正意义。
如果当前这场“拆迁运动”所进行的“拆迁”文化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必然会在不断的重复中而强化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并形成一种新的“拆迁文化”。而在这样一场运动过程中,拆掉的将不仅仅是会馆、楚长城等建筑本身,同时抹掉的是民族的记忆,文化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