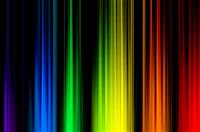
有的时候会看见生活的真相,却不敢发出质疑的声音,而坚持遵循“上面的指令”,把这种坚持当作超越生活的行动和能力,作家每每自责“理解上面的精神实质不够”,于是作家真正思想力被消解,“三突出”创作的泛滥正是作家“三个能力”反向即恶性发展所推动的,
一
郭宝亮《面对现实,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文艺报2015/6/3,以下简称《面对现实》)指出:当代作家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他们面对现实生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作家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应该去“拥抱”,去主动体验,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还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作家缺失思想力,作家应该学者化。
该文又通过余华、贾平凹、刘震云这些“后拨”作家的分析,把当代作家的如是缺失的原因归结为,“当下的一些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漂浮在时代生活之上,成为特殊的一群,享受着比较优越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解决之道在于作家放下身段深入生活,于是《面对现实》强调“深入生活”,以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前拨”作家为样榜,对作家“深入生活”的精神内涵做出上述界定。于是《面对现实》呈示这样的认知:像这些前拨作家那样“深入生活”就会拥有“思想力”,创作出好作品。
在一般意义上,《面对现实》揭示了当下的创作症候,也是对当下作家“深入生活”热议的回应,但联系上述前拨、后拨作家“深入生活”和创作的真实情状,《面对现实》却显现了粗略不详隔靴抓痒逻辑混乱的“短肋”,就是说,在力图指出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上,《面对现实》也暴露了必须得到正视的“缺失”。
二
跟我们面对许多社会现象(包括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认知其实包含着“共识撕裂”(“各说各话”)一样,对相同名词命名的某种社会现象事实上却存在不同的、甚至南辕北辙的理解(比如莫言获诺奖的激烈争论,对获鲁迅奖作品的争论),《面对现实》谓之的“深入生活”同样如此。
《面对现实》提出的“体验生活能力”、“思想现实问题能力”和“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在我简称为“三个能力”即思想力,以及它的“重提深入生活”,作家和读者的实际理解,各不相同。当然,有着不同的理解是生活的常态,我们不应当、也无须追求“千篇一律”,用一种模子一种口吻一把标尺去解释并理解某个“高见”。
《面对现实》开出的正宗验方是,“像当年的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一样,为了要写正在进行中的合作化运动而离开北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小说的写作获得第一手素材。”由是他们获得了“对生活穿透骨髓的生命体验”,而写出了好作品。用《面对现实》的话做阐述,就是为了要写正在进行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一些批评家喜欢用“伟大时代”来强调某个时代的重要性),作家必须深入这种伟大时代的生活,获得第一手素材。显然,这种生活不是作家日常中自在自为、无条件置身其中的包括小我的生活,而是按时代布署(即主流政治要求)展开的富有“服务大局”意味的突现大我的生活,即具有主旋律意味的社会生活,如是才写出伟大的时代,才可能是好作品。换言之,作家要写大题材好题材,为伟大时代提供文学支持,不要以一己或小圈子的庸常喜悲编织作品。
无数的文学事实表明,对时代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往往是作家自在自为的、无条件的生活——包括自己庸常喜悲的生活,创作灵感得以爆发,写作的动力由此产生,思想的力度得以呈现,而且他具有能深刻反思并超拔这种生活的能力,他写的“这一个”恰恰具有认识时代、社会、民族和人类心灵的高度。
这里,《面对现实》所展示的“深入生活”——深层的生命体验——好作品的逻辑关系(说白了只是一种“倡导”),只是一种提纯了的创作可然律,并非必然律,因为在“深入生活”、深层的生命体验、好作品的认定及具体内涵上,有着复杂而深巨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在中国作家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且不说“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是“深入生活”的一种,还有着无条件与有条件、短暂与长时段的区别,具体到特定的作家,由于其际遇和情境,肉身深入生活的层次不同,精神(心灵)层次的不同,至于“对生活穿透骨髓的生命体验”,跟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干部下乡方式”并不呈因果关系,就我自己下放12年的农村生活,我自己不会说、别人也不会说我在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12年农村生活,于我是无条件的,唯一的基本生存环境,一切喜怒哀乐我必须面对和咀嚼,加上阅读文史哲的书,才使我获得深层的乡村体验,当然也是我的深层生活体验,故“超越性认知”、思想力及艺术表达并不是“深入生活”就能解决的,还得在超越农村之外的精神生活(读书和思考)中获得;倘说在乡村生活就是深入生活,也存在思想向度问题——是为主流政治提供“艺术形象”(文学支持),还是写出自己有着独立思想见解的形象(民族和人类心史)。
就是说,深入生活,作家依然存在“继续保持与现实紧张关系”和“缓和与现实紧张关系”的精神向度。
《面对现实》褒扬性提到的柳青、赵树理、周立波,批评性提到的余华、贾平凹、刘震云,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深入生活的途径也不同,写出的作品更不同,余华、贾平凹、刘震云这些后拨作家和作品的欠缺,难道是他们没像柳青、赵树理、周立波这些前拨作家“深入生活”所致吗?事实证明,这些“前拨作家”作品的欠缺,正是他们“深入生活”所凝固并显豁的,这就意味着,深入生活并没有解决其“三个能力”——在“外在律令”指引或胁迫下,“深入生活”有可能有意识地摒弃有价值的文学素材,而创作出一部虚假的作品,这样的文学实例还算少吗?
因而,《面对现实》以厚以前薄当今作家的对比方式,浅尝辄止,其论据由于基础不牢而显现文章的空洞,所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缜密分析的,它着意强调的“三个能力”也就大打折扣,就连“深入生活”、“面对现实”这类关键词也显得笼统而乏力。
三
让我们回顾“深入生活”曾经的时代情境。
年轻时候我读过柳青、赵树理和周立波的代表作《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知道他们都是写19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写贫苦农民实行合作化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必需性,其时地主阶级已被打倒(但无时不刻想复辟),富农和中农成了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的代表,必须贯穿阶级斗争(阶级话语)这条红线,丑化和打倒富农,争取富裕中农——每一次政治运动必得把一些人剔出农民队伍,稍后的浩然及其《艳阳天》等一系列作品正是柳青们的延续(《面对现实》不提浩然并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糟糕而严峻的农村现实跟这些作品所示的光明恰恰形成了反讽,这就证明他们“深入生活”也没有没有写出真正的反映民族心史的好作品。
这些作家是在1960年代初阶级斗争理念升温的政治背景下创作的,其作品充斥着1960年代主流政治的脉动。拿李建军《被时代拘制的叙事——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李建军《大文学与中国格调》,作家出版社,2015,以后的相关引文均出自该文)的话,这类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就是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的观点提倡的“文学支持”,就必然艺术地突出当时主流政治所强调的灭资兴无阶级斗争的内容。
当时柳青以县委副书记身份下乡,在农村住了很久,这就决定他以县领导的形象出现的,他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是相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居生活而言,即使在农村,“三同”也是有条件的(如继续领会主流政治界定的农业合作化的实质,增强党性)。从他个人文学资源,苏联实行集体化小说《未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给他很大的激励,他深入生活是为了创作伟大时代的史诗作品,他这种文学抱负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是作家们源于时代服膺政治的一种选择和追求,有其文学正当性的一面,跟他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现行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的“深入生活”(实为无条件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柳青在“深入生活”之后写出的《创业史》,成色又如何?
还是引用李建军的研究为证:“柳青的确不是一个具有批判的激情和勇气的作家,而《创业史》则因此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我们认知那个时代提供多少新鲜的信息和真理性内容”;“从语言能力和小说技巧方面,《创业史》无疑内蕴着值得挖掘的财富。在当代作家中,柳青的文学才华无疑是第一流的”;“总体来看,他对生活的观察力和认知力,都是很不成熟甚至很幼稚的,——他不仅没有从混乱的经验里分辨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反倒通过自己的叙事将它们给掩盖了。柳青按照他者的思想,预设了一个主题:‘全书要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不仅如此,他还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修改自己的作品。”
就是说,柳青如此深入生活,面对芜杂的乡村经验,并没有提升观察力和认知力,而是从既有理念出发,把活生生的生活内容纳入阶级斗争理念的链条,“缺乏充分的现实感、亲切感,缺乏对生活及人性的理解的和包容性……在宏观的、本质的意义上,他却不得不歪曲理解生活和表现生活。”
这就告诉我们,深入生活之中之后,作家显现两种思想向度和思想力。在柳青,当然是他基于作品主题“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其实是他借鉴反映农业集体农庄的苏联小说,而不是基于他原创性的思想)。后来的社会进程和社会演变,恰恰否定了他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这就表明,柳青的“思想力”其实是回应当时主流政治的艺术阐释能力,并非他基于乡村真实体验的思想力,深入生活并未让他产生真正的思想力。
我以为,柳青第一流的语言能力,是他早年(包括童年)无条件的乡村生活打下的基础,他在阅读中善于领悟苏联文学的语言艺术。所以,有意识地深入生活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并不是起决定作用,并不决定创作主体能够回到当年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面对现实》提到了胡风这个观点)。
1977年(经过“文革”)柳青冷静多了,开始清醒,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群众中间考验,再过五十年就没人点头。”这不正等于对他的“深入生活”效果的一种否定吗?
四
对于前拨作家,同样是深入生活,“三个能力”的呈现是不同的。分析过柳青,现在略讲周立波。
在写出《山乡巨变》之前,他写过获斯大林奖的写东北农村土改(反映伟大时代)的《暴风骤雨》,之后他写过反映1958年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的《铁水奔流》,其创作指导思想都是“按照他者的思想,预设了一个主题”。但是,他写他家乡湖南农村合作化的《山乡巨变》,在刻划农民入社那种犹豫、彷徨、思想反复,虽是持批判的笔触,还是透露出他对南方农村真实情形的认知和他的思想倾向。他对家乡农民和农村的了解,显然是无条件的青少年生活所积累的对农民同情式常识性的了解(化为他的无意识或潜意识),以及在深入生活过程中对合作化各种意见的接触,亦即传统农村意识在他头脑里起作用。就在他像书中所写县工作队长到农村促合作化——深入生活,积淀在心灵中的理解农民(不愿入社)的思想与“预设主题”(走上农业合作化的康庄大道)即上级指令产生了紧张关系,于是书中就烙下了他对农民意愿的同情式描写,拿《面对现实》的话就是具有体验生活能力和思想现实问题能力,以及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即思想向度与思想力。应该说这样的思想力是不经意流露,在周立波却是薄弱的,而这样有价值的“思想一闪”在“文革”中仍被揪住不放,被上纲上线反复批判。当时主流政治越来越趋于阶级斗争极端的情势,其实也否定了周立波的“深入生活”所坚持的思想向度。
因而,作家深入生活并不必然地拥有“三个能力”,在既定政治理念的拘制下,反而会弱化甚至消解“三个能力”,换言之,有的时候会看见生活的真相,却不敢发出质疑的声音,而坚持遵循“上面的指令”,把这种坚持当作超越生活的行动和能力,作家每每自责“理解上面的精神实质不够”,于是作家真正思想力被消解,“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创作的泛滥正是作家“三个能力”反向即恶性发展所推动的,其中不乏“深入生活”后的作为。这是当时普遍的作家状况。
五
正是基于作家深入生活所呈现的生动复杂的精神状态,赵树理成了我着重分析的个案。在赵树理身上,体现了一个良知作家在深入生活过程中强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显示了“深入生活”也可能形成并强化作家真正的思想能力。
王彬彬《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和朵渔《赵树理:一个旗手的倒下》(载《同舟共济》215年第6期,共识网转载,简称《赵树理》)让我们更加确切而鲜活地看到,“深入生活”的赵树理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
赵树理比柳青写农村合作化更早思考革命中的农民处境问题。
1948年2月,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习仲勋《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报告》中,他指出了土改中一些政策的不合理,他列举了土改造成的负面后果(对地主、富农的“乱打乱杀”现象,侵害中农的现象,乡村流氓地痞乘机掌握基层政权的现象很普遍),他强调贫农本身很复杂,因为导致一个人贫穷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与此同时,在山西的赵树理也同样不安与忧虑,他的不安和忧虑完全是原发性的。这既反映了洞悉农民心理的赵树理与当时土改现实的紧张关系,也曲折地印证了富有农耕传统的中原大地农民的精神质素,促发了赵树理的忧虑和思考,这是深层次的,不易更改的,它涵养了他的文学良知。晚年赵树理说“一辈子为农民写作”决非虚言。
有作品为证。1948年10月赵树理发表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乡村“流氓无产者”怎样在土改中把持乡村政权,怎样“打倒皇帝做皇帝”,怎样鱼肉百姓、欺压良善。后来他的文学创作如《三里湾》对农民(中农)的同情式描写就贯穿这样的认知,却屡受当时主流政治的鄙薄和批判。赵树理这种认知是他无条件生活得来的,只跟这块土地即农民的文化传统有关,而不是“深入生活”的全新发现。要说发现,对于他,恰恰在深入生活中坚持并强化了这种认知,与现实的关系(即与主流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张,并顽强地作出艺术表达,说“再认识”更为准确。这跟当时根据“他者的思想”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柳青迥然不同。
1940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赵树理已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多部成功之作,受到热捧,1950年代初期被当作“文学旗手”“赵树理方向”。他是以一个“旗手”的身份进城的。但是他始终没改变自己的农民立场和率真的农民感情。
朵渔文章说:已近花甲之年的赵树理,是1965年2月离开北京,全家迁回太原的。赵离开“风暴眼”回到了故乡,担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局工作。从1949年进城,到1965年的离开,这17年中,他是在不断地“离京”和“返京”中度过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地“离乡”与“返乡”。17年中,他无数次返回故乡,徜徉于故乡的风俗人情里。可以说,这就是他始终保持“深入生活”的姿态。
为写农村合作化作品,同样是“深入生活”,赵树理和柳青在艺术表达上呈现既相同又不相同的面貌。相同的是,他们是为创作表现这个“伟大时代”执意写出大作品,以作家身份来到农村,深入生活,他们作品均体现“他者的意图”,由此构成其“深入生活”的合法性,这当然得化成作家自己的意愿,即下乡是出自转变立场进行写作的需要。
不同的是,在“深入生活”中,赵树理主观上想跟上时代体现“他者的思想”,但积习所导致的与合作化现实紧张关系,仍继续着,并在创作中顽强地表露出来,他创作的温吞水态势就是个印证;而柳青则坚决地摈弃农民情绪,将梁生宝理念化理想化,“取消他身上属于人的本能冲动和自然属性,取消他对家庭生活的正常愿望和正常需求,进而将他写成一个无个性的人,一个无趣味的人,一个凌空蹈虚的人。”柳青甚至以措辞严厉的文章反驳质疑梁生宝的批评家严家炎。于是也就看清了深入生活的两种思想向度及思想力。
《赵树理》这样写道:
赵树理进京后,一有机会就跑回山西乡下,他到那里并非走马观花,也不是简单的“体验生活”,而是身体力行,同吃同住同劳动,深扎进农村。这种介入并非肤浅的“乡情”,更不是简单的对农民的“同情”,而是对自身身份的“恪守”——他要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代言。为此他不惧于在高层领导面前公开自己的观点,不惜与当地其他领导干部发生激烈冲突。就是本着这种执着,他甚至“与一般文艺界的朋友、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界人士往来不多,关系不很融洽”(陈荒煤语)。
赵树理曾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赵树理所说的“问题”,不仅仅具有政治层面的含义,更多的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并不符合主流政治的要求即“他者的思想”。在政治的话语空间相对开阔的时候,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可以被当作“经典”;而这种空间一旦收缩,赵树理小说就被指责为“不曾反映重大的斗争主题,不曾反映英雄人物,不曾反映激越的精神面貌”而加以否定和批判了。
赵树理还对当时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1956年,他致信长治地委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接触乡村现实生活,赵树理并不回避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的思想向度鲜明,为农民代言的思想力得到磨砺。赵树理是“深入生活”对于作家正面作用的一个例子。
不过,赵树理“为农民代言”而深入农村生活,从他关注农民的精神品质到只关注农民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的生存状况,固然说明当时乡村生存状态的恶化,也说明他无法超越生活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六
应该指出,上述两拨作家所面对的很不相同的两个时代,经济形态及基础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创作语境不同。当今作家所谓“比较优越的生活”,在余华、贾平凹、刘震云这类后拨作家,指的是功成名就后的生活状态,他们难道没有深入生活?他们有的就在本然即无条件的生活之中,有的如贾平凹前几年还被安排到南方“体验生活扩大视野”呢,他们写出的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欠缺,跟他们的“三个能力”有关,而跟“深入生活”并无多大的关系。
《面对现实》分析余华的《第七天》,说它缺少了真实体验的现场感,那种生动的、来自生命体验的细节的现场感却是严重缺乏的。
正如黄发有在《余华的惯性》(见贾梦玮主编《当代文学六国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指出的,余华有暴力书写、苦难书写、重复书写惯性,余华坚信“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加上写了大量作品基础上的创新追求,《第七天》就有这样的成色。作家的文学实验是他自己把握的事,生命体验细节的现场感,这跟作家的“深入生活”没什么直接联系,倒是跟作家包括童年在内的无条件生活息息相关,现实的触发激起他富有疼痛感的记忆,作深刻而完美的艺术表达,只跟思想力相关。在他早期的写作(如《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唤》)其实有过“生动的、来自生命体验的细节的现场感”的描写。也许,余华自身思想力呈弱势,也许,他在创作摸索中还没有找到、而且从容表达的思想力所需要的文学形式。
《面对现实》分析贾平凹的《带灯》,说它叙写了乡镇信访干部的现实生活,是作家体验的结果,但它仍然没有完整传达出作家对时代的思考深度。这些欠缺是作家“深入生活”就能解决吗?实际上,贾平凹是经常性深入生活的。
贾平凹深入生活有两种途径或模式。1995年,贾平凹在中国作协负责人翟泰丰的关怀和指导下,去华西村“生活”,从西北乡土到华东农村,这就是标准的“深入生活”的一种,但他没写出以华西村主原型的新的农村集体化光辉大道的作品,这就表明他保持着自己的思想能力(现在的华西村又是如何?作家不妨去“深入生活”,当然也可能创作出新世纪中国的“金光大道”)。另一种则是——他更多的是自己选择的下乡方式,在家乡走走看看,一方面接触现实,另一方面激活无条件家乡生活的记忆。一定程度他重复了柳青当年深入生活的做法,也同样重复柳青“被时代拘制的叙事”。他的新作《带灯》缺乏“思考深度”,根本上还是跟他的思想力相关联。
这方面洪治纲的《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参看《当代文学六国论》)有较准确深入的分析。他这种深入生活的姿态给其创作带来内在消极的影响,拿洪治纲话就是,“他的创作(特别是后期创作)一直缺乏本质性的超越”,他自身的原因,“他又总是在一些小小的挫折面前显得‘懦弱’不堪,诉说不已,面对一些人生的轻波微澜偏偏超脱不了……折射了他在自我超越上极为艰难的精神质地,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精神境界上的本质性飞跃。”“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作家,他所操持的价值立场和艺术观念,在本质上应该体现为他必须与现实秩序及其表象经验保持必要的距离。”“深入生活”使得他与现实秩序及其表象经验结为一体,“在主观上,他渴望回到民间,回到自我独立自治的精神空间,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又显得顾虑重重而巧取中庸。”
这也说明,作家思想力的获得并强化,其实跟“深入生活”是两码事。如此观之,凡此等“深入生活”的作家都会经历这样的创作尴尬,因而,对当代作家,“深入生活”也不必然地就能够获得“三个能力”,这倒是作家应该警觉的。
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以极为反讽的笔法写尽了世道的荒诞,写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秉公办事的的各级官吏而无法解决小人物的小事,他生活体验之后的感悟,看到了现实生活背后的逻辑,他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时代”。看来《面对现实》较认同刘震云“体验生活之后的感悟”。其实刘震云借鉴了存在主义的思想方法(法国作家加谬的《局外人》)。
刘震云以日常现实主义写作起步(《新兵连》),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促使他在一个期间向历史深掘(如《故乡天下黄花》),把对时代的体验贯穿于这类“历史写作”,在他找到以存在主义思想方法表达现实的利器,他又回到了现实题材的写作,不过从历史找文学灵感的优劣却沿衍下来。显然,他“体验生活之后的感悟”并不是他深入生活的结果,而是阅读和借鉴——超越现实的精神提升强化了他对现实书写的超越能力,也就是创作主体具有思想力的结果。这是前拨作家所不具备的。
凡影响社会进程和人类心灵的战争、浩劫、灾难的题材应该是大题材,当然比一己及小圈子庸常生活的描写更有价值,但是,即便写一己及小圈子,所刻划的人类心灵和情感与前者相通,都是有价值的创作,在这点上,到处是生活——现实主义有着广阔道路。“深入生活”只有在扩大见识、增长知识、了解某个生活细部、深化对社会和人的理解这些层面,对作家有帮助,而在提升作家的思想力上,作用有限。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缺少的不是“深入生活”;我们每一个作家都无条件地置身这个时代,每一滴水能够映照太阳——反映时代的本质,关键在于具备超越生活的反思能力,它体现在,超越现在着眼未来,也体现在着眼未来而向历史掘进上——全方位的激活人类生活塑正人类心灵。
2015年6月8日——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