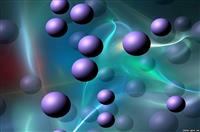在一个由人情和面子构成的关系本位的文化中建设民主、法治,决不能仅从这些制度自身的逻辑出发,而需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国文化习性的制约。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新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开始复燃,如今已蔚为大观:大批媒体和社会组织纷纷办起了国学讲堂,国学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出现了许多少儿读经班、弘扬国学性质的民办书院或团体,成立了大量国学培训部门和机构,以及许多设于大学内的国学院或儒学研究中心等。可以说,这一轮国学热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后劲。这与中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支持分不开,也与今天中国人重新寻求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心理有关。
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核心问题
一百年来,新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五四学人曾激烈批判儒学,认为“纲常礼教”倡导等级尊卑和绝对服从,束缚了人性,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中国迟迟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儒家传统中虽有落后的糟粕,也有优秀的精华。比如儒家的忠孝思想、家国一体思想等曾成为日本、韩国等国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也有学者指出,古人所讲的等级尊卑,只是身份差异和分工之别;“三纲”的倡导者都同时主张谏争,反对绝对服从,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种从大局出发的、尽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责任而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百瑞(Wm.deBary)指出,儒学中并不缺乏尊重人格平等和个体权利的资源,儒家传统中洋溢着自由主义精神,只是形态与西方有异而已。
跟现代化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儒学与民主的关系。五四学者认为,儒学维护大一统的专制统治,与民主水火不容。但是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就指出,儒学中存在民主思想的萌芽。比如儒家经典中一直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等。许多学者认为,儒家的基本倾向是民本主义,“民本”不等于“民主”,但从民本可导向民主;从民本转化出民主,需要一番功夫。夏威夷大学安乐哲(RogerAmes)教授指出,北美的民主实践表明从儒家传统可以发展出一种基于社群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除了西方模式外,还可能有东亚模式或中国模式。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很多学者曾认为儒学不同于宗教,本质上是高度人文化的学说。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儒家传统一向支持对“天地君亲师”的祭拜,并有一整套严密的礼仪规范,这不能说不是儒家传统中的宗教维度。另外,就宗教所指生命的终极关怀而言,儒学中“天人合一”、从天道到人道的传统一向发达。
儒教说、儒宪说成为2013热点,但并不能解决问题
近年来的国学特别是儒学研究中,还出现了如下几个热点:
一是儒教说。蒋庆等人继承康有为的儒教说,主张重新将儒学立为中国的国教,形成新的“政教合一”政体,遭到很多学者强烈批评。陈明等人主张将儒家立为可自由选择的“公民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和佛教等相互竞争,由此彰显出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优势。
二是儒宪说。这一派学者基本上禀承康有为、张君劢以来的传统,主张建立一个由儒家主导的宪政国家。蒋庆曾提出一个由通儒院(由儒生构成)、庶民院(由民选代表构成)、国体院(由社会贤达构成)三者为基础的“议会三院制”架构。
不过,这些观点只代表目前儒学界炒得比较热的声音,如认为它们代表儒学研究的主流就大错特错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现代儒学的最大困境始终是儒家价值体系与现代性需要的紧张,尤其是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之间的张力。这个问题在牟宗三那儿表述为儒家内圣与民主、科学等外王的关系问题。如何求取解决之道,一百多年来耗尽了不知多少人的心血;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儒教说、儒宪说没有任何突破。“儒宪说”将儒家理想中的政体称为宪政政体,恐有削足适履之嫌。蒋庆的议会三院制,乃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个人建构,没有可操作性。至于“儒教说”,可以说过分注重形式,而忽视实质。今日中国需要重建价值,但这套价值为什么就是儒家的,才是今日任何一个信奉儒学的人最应该用心思之、奋力为之,也是最能体现当代儒学有无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地方。然而,恰恰在这些地方,目前的儒教派和儒宪派皆未能展示儒学的生命力和他们的创造力。
总而言之,儒宪说也罢、儒教说也罢,只是换个词汇来讨论中国文化的出路或核心价值问题,但对于儒家价值与现代性(民主、宪政、法治等)的关系,没有提供任何新思路,没有解决任何老问题。
民主法治建设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国的文化习性
要解决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就要弄清中国文化连续性的根源在哪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人情和面子是其中最重要的整合机制;这与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本位,以外在超越和普遍法则为最重要的整合机制形成对比。正是文化习性的差异,导致个人自由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因为个人自由不是中国人人生安全感的源泉。正是关系本位的作用,导致人与人相互攀比,社会风气成为比任何制度都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中国人崇尚人情是和蔑视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中的制度因人事而立,也因人事而废。所以,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制度走的是“礼大于法”的道路,因为礼是因人情而立的;另一方面,要想在中国人的社会立制度,必须从任贤能做起,靠贤能的示范来引领社会风气;再一方面,要想建立牢固的社会自治体系,必须从理顺人伦关系做起,因为人伦关系是一切社会道德最重要的基石。
从文化习性的角度讲,可以发现:其一,民主政治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克服党争和大众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问题,因为关系本位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帮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其二,法治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避免被人情所冲破、从而在中国人心灵中真正确立起神圣感的问题;其三,人权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谁能帮人民捍卫的问题,个人自由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不恣意失控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中的人权问题,严格说来往往是由强者欺压弱者所造成,而强者的背后存在的往往是一个关系集团;而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容易演变成永远达不成共识的散漫。总之,在一个由人情和面子构成的关系本位的文化中建设民主、法治,决不能仅从这些制度自身的逻辑出发,而需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国文化习性的制约。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同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化传统一样,儒学只有在不断地回答时代新问题、迎接现实新挑战的过程中才能复兴。我们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传统出发,从文化习性的角度分析今天这个时代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症结,从而说明未来中国现代性的方向,以及未来中华文明重建之路。只有当儒学能回答我们时代的一系列重大课题,给中华民族指明一条通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让中华儿女重新找回安身立命之本,为中华文明开辟波澜壮阔的事业前程,它的复兴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