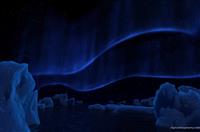●当今世界,无不重视科技的发展与文化的振兴。抑制粗放型经济的负效应,发展创意型经济,引进新经济的创新元素,提振经济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已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课题。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吸引、保留和发展创意人才的能力。
●美国的新兴科技产业、日本的动画产业、韩国的设计产业的兴起,英国、德国、法国等老牌工业国的成功转型,均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从国家、都会、社区等多个层次,形成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创意激励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
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意是支撑创意产业的两大核心。从全球创意经济集聚区的兴起与衰败、崛起与转移,可以发现激励机制作为创意经济“隐形的手”发挥的关键作用。当今世界,无不重视科技的发展与文化的振兴。抑制粗放型经济的负效应,发展创意型经济,引进新经济的创新元素,提振经济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已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课题。中国在GDP高速增长之后,正期待迎来国民“大创意”时代。探索符合中国体制、市场发育程度、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创意激励机制迫在眉睫。
在经济学视野里,创意即科技,即文化,或即科技与文化的融合。罗伯特·索洛认为,用技术和传统投入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导致了80%的经济增长。保罗·罗默在1986年指出,“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上个世纪的欧美,在工业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遇到了资源瓶颈与“环境病”,提出了“增长的极限”警示,从此驱动发达欧美诸国转向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模式。近20年,强化科技应用、知识投入的新经济、创意经济在这些地区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
事实证明,欧美近年的创新引领、创意驱动的国家战略效果明显。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统计,近几年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高附加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美国则达14%、英国达12%。此外,韩国、新加坡、日本、瑞典、意大利等国,创意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已超出传统工业。在科技研发、文化增值双重动力下,这些国家在全球软件、影视、新闻出版、设计、展览等新兴创意产业拥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
如何评估国家或区域创新的绩效,如何配置促进创意经济增长的制度?美国、欧盟最早开展了区域“创意指数”的测评,以量度区域创意产业发展的绩效。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的3Ts模型,较早阐释“人才、技术、宽容度”三个维度激励创意经济发展的规律。2004年,理查德·弗罗里达牵头研究提出“欧洲创意指数”,相比3Ts模式有较大发展,但其核心思想仍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吸引、保留和发展创意人才的能力。2004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进行“香港创意指数”研究,提出把“创意的成果、结构及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五大因素作为创意经济测评的主要要素。美国学者兰德里是创意城市研究的倡导者,他对巴塞罗那、悉尼、西雅图、温哥华、赫尔辛基、格拉斯哥等城市进行个案研究之后,提出创意城市共同的成功点是“富有想象力的个体、创意组织机构和有明晰目标的政治文化”。上海在国内最早测评了创意指数,提出人才、文化与社会环境对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作用。
有关研究无不证实,人才是文化与科技创意产业的首要核心。上个世纪,罗默、卢卡斯、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之于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进行了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事实也是如此,美国电子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早在2006年,纽约、大华府、圣荷西(硅谷)、波士顿、达拉斯是美国高科技与文化产业就业人数最多的都会区,其中纽约有31.7万人、大华府有29.6万人从事高科技与文化领域的工作。目前在硅谷集结着来自全球的科技人员达100万以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硅谷任职的就有近千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达30多人。2010年以来,我国创意人才的回流,也是因为国内科技产业的发展营造的机会、集聚的资源所致。
研究证实,吸引创意人才、留住创意人才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意社区”。近年,全球陆续出现了一批融合创意人才集中居住、创意产业集聚的都市区,例如美国的硅谷、好莱坞,日本筑波科技园、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英国的区域通讯技术集群、爱尔兰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无边界创意集群、丹麦的大型通讯技术集群、荷兰多媒体集群,这些区域的创意产业集群形成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这些区域生态质量较高、交通便捷、社区生活便利、集中了金融、投资、社区服务等中介机构,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分享网络、资金流动网络、文化沟通网络、社会交往网络、技术扩散网络,由此被誉为“创意社区”。
创意社区符合创意人群追求“获取价值”、“获得个人实现”的需要。在创意社区,创意人群能轻松获得实现个人创意的工作机会,能随时获得创意导师的指教,更容易获得天使资金、风险投资资金的激励。美国硅谷文化促进协会认为,创意社区还最可能为创意工作者提供相应的文化活动、社区活动,以满足他们文化、生活层面的需要。该协会提出要想让硅谷保持在新世纪的发展优势,需要借助艺术与文化,激发更多的创意与创新能量。
创意产业集聚区与创意社区在空间上毗邻、融合,对创意人群形成巨大“引力”。根据科思等经济学家的观察,产业的空间集聚,减小了企业的商务成本,让企业直接获利。创意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为创意企业寻找创意人才、获得政府资助、享受税收优惠、获取金融支持提供了机会和便利。同时,创意企业也由此获得了显著的科技“溢出”效应。创意企业除了基于实体空间的集聚,更可以发展基于虚拟组织的集聚。虚拟经济组织模式如互联网经济,为后发展区域提供了参与国际创意市场的机遇。
过去的理论普遍认为促进创意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加大研发(R&D)投入总量与配置税收优惠、成果奖励等特殊政策。毋庸置疑,这些直接、显性的手段正在起到巨大作用。笔者测算了几组数据:我国从业人员约8亿人,创意人群总数约占20%;我国R&D经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例(R&D指数)在2002年为1.07%,到2007年上升为1.49%;2002年我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科学才能指数)2002年是0.44%,2007年上升到0.59%;我国每一万R&D人员获得专利数(创新指数)从2002年1275.4件上升到2007年的2027.6件;如果将2002年的创意指数基数为100计算,2007年我国创意指数为104.5。通过测算得知,国家创意能力、创意绩效与GDP总量并非完全一致,发展创意经济不能唯GDP论,也不能单一依靠R&D与文化专项投入。
美国的新兴科技产业、日本的动画产业、韩国的设计产业的兴起,英国、德国、法国等老牌工业国的成功转型,均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从国家、都会、社区等多个层次,形成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创意激励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在我国GDP总量位居全球前列而创意经济整体弱小的格局下,在国家层面亟待从物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等角度,城市需要在创意社区打造、促成创意集聚等方面,共同发力,逐步提升我国科技研发、文化原创动力,促进文化与科技创意的空间融合与网络融合,最终健全我国创意产业价值链体系。在历史上,我国拥有“四大发明”这样伟大的创意成果。在历经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洗礼的今天,全球均在反思稳健、持续的经济发展形态。我国已经具备了国民经济相当的基础,当要继续发挥“中国制造”的优势,完善国民创意激励体系,创造“中国智造”的模式,成就创意经济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