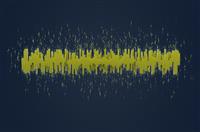
18世纪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黄金时期。随着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陆续入华,中国的礼仪、法律、制度、科技等知识传播到欧洲大陆,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催化剂。孔子的儒家精神,刺激着西方人走出神学时代而步入启蒙,同时中国的器物、艺术乃至抖空竹等民间游戏都进入了西方并产生了持续影响。在艺术品和器物领域,西方人爱不释手地把玩欣赏中国茶具、屏风、扇子,中国元素影响到教堂、花园和室内装潢的艺术风格。
打破古典主义回到自然风致
在“中国热”中,中国园林的一些特点以文字和装饰画的方式传入了欧洲,在整个欧洲引发轰动,这一时期古典主义的巴洛克艺术渐趋衰亡,而洛可可艺术在“中国热”的推动下风靡一时。在英国,经过坦普尔、艾迪生等人的介绍和坎特、勃朗等人的设计,中国园林同英国人对自由无束景象的热爱融汇起来,产生了所谓“自然风致园”,特点是将花园布置得像田野牧场一样,就像从乡村的自然界里取来的一部分。
中国园林在英国掀起了园林热。从当时设计的叠石假山、山洞拱桥以及18世纪坎布里奇和沃尔等建筑师留下的文字中可以推断,18世纪上半期英国出现的自然风致园受到中国园林较大影响。
巧夺天工赏心乐事
18世纪后半期,中国园林的影响进入第二阶段,钱伯斯爵士依据中国园林风格设计的“丘园”是“图画式园林”的典型代表,甚至开始援引中国园林来指责自然风致园。
欧洲人对于中国园林的了解渠道还不多,王致诚写于1743年的信件介绍了位于北京海淀的畅春园、圆明园、绮春园和长春园。王致诚以画家的眼光发现了中国园林的自然天成之美,宛如“大自然那鬼斧神工的杰作”,没有笔直的甬道,而多是弯曲的盘旋路和羊肠小道。这段文字在进入欧洲后,对当时的园林建造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王致诚的介绍十分详尽,且初步涉及中国园林的某些美学特征,遗憾的是未能深入揭示中国园林背后的某种精神,回答“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建造园林”的问题,未能揭示中国人如此运用写意技术的真谛。
不过,《中国杂纂》中收录了两篇韩国英的信件,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园林有更深入的认识。韩国英也是一位画家,据说他同一个叫刘舟的中国人切磋过中国造园艺术。韩国英的闪光点在于第一封信,他翻译了司马光关于“独乐园”的长诗,并附上他本人的一篇短文介绍中国园林;第二封信题名为《论中国园林》,概述了中国造园史和造园艺术的原则。
也许受刘舟的影响,韩国英试图用中国人司马光的作品来解释园林的功用,但他用诗体译成的这首《独乐园》的长诗,却不见于司马光的各种诗文集,与其意思接近的是司马光的散文《独乐园记》。《独乐园记》中确有一段话表达出重视独处与静思的念头:“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韩国英在《论中国园林》中强调中国园林对于心灵宁静的营造:“还要想到,人们到园林里来是为了避开时间的烦扰,自由地呼吸,在沉寂独处中享受心灵和思想的宁静,人们力求把花园做得纯朴而有乡野气息,使它能引起人的幻想。”由此看来,他应该是读过司马光《独乐园记》原文的。
传教士对园林艺术的介绍缺乏相应文学的支撑,也就使得中国园林的真实面目被西方人有意无意间误解。英国人选择中国园林作为自然风致园的模板,也经历了一定的文化过滤和改造。在法国传教士对于中国园林的相关文学作品保持沉默的前提下,英国人却经由中国园林强化了自身对于“荒野”的迷恋,甚至将中国园林与恐怖、惊异乃至崇高这样的审美心理联系在一起,掀起了一阵“误读的盛况”。
相比于同时期的古典主义法国,英国更为重视感性和自然的因素。但英国人心中的自然与中国人的自然不太一样,英国人更迷恋“荒野”的气氛,强调野趣、自由、奔放甚至有些恐怖的场景,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与神话、传说、显赫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在狂放的自然中完成对于个体自由的确认;中国人则关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这样的和谐境界,追求的是“物我两忘”“陶然共忘机”的和谐状态。
在18世纪,英国人却没有注意这个差别,从坦普尔到钱伯斯,这些英国造园家从未看过真正的中国园林,而是从自身传统出发,对于中国园林做出了种种臆想和推断。钱伯斯在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开篇指出中国园林的基本特点:大自然是他们的仿效对象,他们的目的是模仿它的一切美丽的无规则性;中国园林重视整体、剪裁和提炼等特征。但论到园林中“景的性情”的分类,他说,“他们的艺术家把景分为三种,分别称为爽朗可喜之景、怪骇惊怖之景和奇变诡谲之景”。这一点则是他者的眼光,需要中国人进一步去理解。
所谓的“怪骇惊怖之景”,中国园林中即使有,也应该是极少数的另类,大概只存在于钱伯斯的想象中。这样强调恐怖,其实就是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欧文明对待荒野的既恐惧又迷恋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西式思维,根源于从朗吉努斯再到博克等西方哲学家对于“崇高”与“优美”的二分。
博克认为“惊惧是崇高的基本原则”,他在1756年发表的《论崇高和美的观念的起源》中,对崇高下了如下定义: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能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钱伯斯毫无根据的臆想却引起了博克的注意,1758年,博克自己主编的《年鉴》中甚至转载了前述1757年钱伯斯的那篇文章,试图将钱伯斯描绘的“怪骇惊怖之景”作为例证纳入到自己对于自然界崇高之美的理论体系中。正是在种种奇特的转译与文化误读之下,中国园林成为了“崇高”美学风格的化身。
中国园林的本来面目更接近于“优美”而非“崇高”,它有着洛可可艺术式的优雅与日常,不是靠惊骇与恐怖来征服游园者的,而是孕育着悠久的文人雅致,这一点英国人很难一下子理解。
在中国园林影响最大的英国,18世纪的模仿热潮中存在着对于中国艺术与文化精神的严重误读,将其特征定位为崇高与惊惧,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化隔阂。在此隔阂之下,西方完成了一次对于中国和远东艺术的想象。园林的实质是文人化的艺术,是中国文人寄意山水田园、寻求自然雅趣的结果,中国诗词歌赋中遍布对于田园、山水、风景与归隐生活的赞叹,倘能多为西人所知,当不至于郢书燕说到如此地步,也会少一些在历史细节面前怅然若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