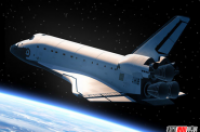当你将中放进世界的历史中进行对比,你才会发现中国的各种特点。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文明。通过已有的文字和建筑能证明国家的出现而论,中国比苏美尔要晚近2000年,比埃及也要晚了1500年。但是中国后发先至。在西周时期,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饬的大一统封建制度,比欧洲早了近1800年。
接下来,中国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同样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实现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统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动资源。这是同时代世界上其他国家不能梦想的。欧洲国家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开始了构建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的统一集权国家的过程。而直到17世纪达到顶峰的法国中央集权,仍然做不到像秦始皇那样对社会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更何况统一欧洲。
1、中国这种相对西方近2000年的领先,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社会面貌的“现代化”,流动性增强。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候,秦朝就已经从制度上废除了贵族制度,实现了“万民平等”,出现了空前的社会流动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大一统国家之内,语言文字和度量衡统一,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这种状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历史上有句独特的话叫“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就认为皇帝干了几十年,一二百年就得推翻了再换一个,这很正常。中国从秦代之后,社会流动很强,导致中国人的竞争意识也很强。
西方直到中世纪后期,才解除了领主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国内重重封建税收关卡。日本做到这一点,要到明治维新之后。印度直到今天,种姓制度还有强大影响。
其次是大一统带来了比较长的和平时期。中国的地理特点和文化心态,决定了分裂状态下,群雄通常争战不休。“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结果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才能享有长期和平,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秦汉帝国崩溃后,虽然也经常经历分裂时期,但是大一统郡县制度总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统一。
因此,在所谓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历史发展却进入了高峰期。在长期的和平下,一个王朝的经济通常会稳定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贞观、开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诗宋词。也留下许多雄伟的建筑和工程,比如万里长城、故宫和大运河。
2、当然,中央集权制度领先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导致了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走向,也致使了中国和欧洲社会面貌的不同。
第一,传统中国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一元化结构。
中国大一统大王朝的面积极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为了保持国家的一元化和一致性,大一统王朝通常会对全国进行格式化的整齐划一。
这种整齐划一令西方人惊叹。英国人说:“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在和平时代的社会治安之良好,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也远优于同时代的欧洲。
但是整齐划一也有代价。在中央集权制下,因为皇权的独占性,君主通常对地方社会的动态发展表现出恐惧,对其他社会力量始终处于压制防范状态。因此总是采取“消极性带防御性”的做法,“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一般迁就经济落后地区”。比如很多朝代经常命令大片区域种植同类作物,结果加重了社会的负担,造成经济倒退。明初为防海盗骚扰,下令“片板不许下海”。清初迁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迁30里。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大大超过了海盗的掠夺。
因此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长时间和大面积的和平,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也压制了地方的效率。
而欧洲因为一直没有完成统一,各民族国家出现强烈的竞争态势。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规模浩大的郑和下西洋因为皇帝的一道简短的命令突然停止,这在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小国林立虽然动荡不休,但另一方面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发挥。
第二,中国传统王朝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但是也容易出现周期性的崩溃。
与中国君权缺乏有效约束伴生的,是官僚系统非常庞大,权力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如我们分析过的,中央王朝每收取到1分税赋,官僚系统可能会额外贪污10分。因此中国传统王朝到中后期,总是出现收取能力过度的问题。在皇帝穷奢极欲的同时,官僚系统更侵吞了大量财富。结果是“皇帝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导致一个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积腐败当中。
由于中国传统王朝的收取成果很多时候不能为社会共享,用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这种过度汲取总是表现为压垮脆弱的小农经济。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没有妥协性渠道,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战争,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欧洲在持续的小规模的动荡中发展,人口发展曲线比较平稳。而中国大一统王朝总是“脆断”,崩溃所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损失,要远超过封建制的西欧。
3、“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西方式制度;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的社会动荡。”(陈季冰:《从土耳其的历史,看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难题》,2016年7月18日“腾讯大家”专栏)
确实,放眼世界,全球18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其中所谓发达国家20多个,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后发国家”。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
相反,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
土耳其从300年前起就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其艰难与中国高度相似,经历了土耳其版的“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重重失败,直到凯末尔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的起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一脚,却在近些年开始走上了回头路,离欧盟越来越远。其原因是凯末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虽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但触角难以深入到边远而广大的土耳其农村。集中在农村的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仍然浓厚。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以后,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开始显示力量,伊斯兰因素又堂而皇之地一步步彰显存在,近年来更达到高峰。
拉丁美洲的民选政治也步入泥潭。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中焦虑不安的拉美民众很容易受到那些激进口号的影响,他们喜欢那些提出诱人目标和简单快速的解决方式的领导人,谁的气质和姿态最权威,最像“父亲”,谁的许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就最容易上台。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许诺要为穷人提供“超福利”(免费住房、免费汽油),因此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上台之后,为了兑现承诺,查韦斯大力推行国有化,把所有行业都收归国有。但赶走了有管理能力的外国投资者之后,委内瑞拉本国却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接手,国有企业陷入效率低下和严重腐败当中,激进的国有化不久之后就导致各种物资短缺。堂堂的“石油富国”已经沦落到需要进口石油,超级市场没有食物,人们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国家的经济崩溃了,穷人获得的福利也自然随之成为泡影。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之所以在这么多国家遭遇重重失败,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力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移植的,这种移植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艰苦,并且成活率很低。除了制度原因之外,现代化还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够提供这种土壤的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清教文化,另一种是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共同特点是积极进取,推崇勤奋节俭的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看作被“上帝选择”的证明。“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新教推崇勤勉这一品质,认为饥饿和贫困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
儒家文化则更为入世,它不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刚健进取的奋斗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正在生动地向世界展示华人强大的竞争能力。比如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说》中讲的,在硅谷打工的华人,如果3年还没有升职,就会感觉不满。而印裔工程师30年不升职,仍然心平气和。秉承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神遗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求变意识。儒家精神的强毅进取,中国人个体强大的竞争能力,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是表面上很求稳,但是又有很不安分那一面,总是很勤奋地去往前趱,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中国人到海外,到意大利做皮鞋,去西班牙开各种店铺,都比当地人勤奋。这种竞争意识,不懈奋斗的意识从秦朝就开始了。
与清教和儒教比起来,通行于西班牙、葡萄牙及法国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则是一种中世纪性格的宗教。它宣传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前提。既然凡事上帝已经天定,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一切都托付给了上帝,索性就万事不着急了。因此天主教文化圈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对每一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的明天”。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现在都已经完成现代化。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儒教主体国家和地区,其共同之处在于,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的勤奋进取精神,同时又拥有借鉴自西方的法治环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儒教文化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一点,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比较公允的看法是,这两方面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