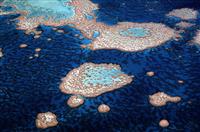历史的河流流淌到明代,皇权专制的演进轨迹出现了一个急骤的转折点——“政归中书”的共治政体在明代被抛弃,皇权专制程度达到秦汉以降的高峰。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诛杀了权力膨胀的左丞相胡惟庸,干脆废除宰相制,还下发诏书:“今我朝罢丞相,……事皆朝廷(其实就是皇上)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朱元璋《皇明祖训》)宰相的权力被皇帝包揽过来,事无大小,咸决于上。只是天下政事太多,皇帝精力有限,不得不成立一个机要秘书处来协助皇上。这个秘书处,就是“内阁”。此内阁当然跟现代责任内阁完全是两码事,就是跟以前的宰相制相比,也大不相同。明内阁不是政府的领袖,“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明史•职官一》),其职不过是替皇上起草诏书,以及草拟批答奏章的意见稿,时称“票拟”。“票拟”不算正式政令,需要皇帝用朱笔抄正(时称“批红”)之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如此,皇帝既可以减少工作量,又能将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出于监视文武百官的目的,朱元璋及他的子孙又先后设置锦衣卫、东厂、西厂与内厂,为直接听命于皇帝、凌驾于官僚制之上的皇室耳目与爪牙。朱元璋还因为孟子说过“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藐视绝对君权的话,大发脾气:“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文庙,取消其配享资格。又尽删《孟子》中所有“非臣子言”的文字,编成《孟子节文》(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五)。这固然是秦制对儒学的赤裸裸的强暴,又何尝不是反映了儒家与秦制之间的严重冲突。
大致而言,废除宰相制之后,明代前期的确出现了皇权膨胀,但随着内阁制的成熟,中枢权力运行形成惯例,皇帝“批红”基本上都采纳内阁“票拟”之意见,且按照惯例,“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明史•夏言传》)。内阁实际上获得了类似宰相的权力,只不过缺乏宰执的名分。这时候,皇帝如欲独裁,则会被当成不合成例。当然,明代的皇权拥有绝对强势,皇帝越过内阁迳发中旨的情况也是不少见的,但比之废相初期,皇权专制的烈度已大大下降。
被专制皇权压制下去的儒家“公天下”与“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也在晚明儒家士子的意识中复苏。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顾端文公年谱》)要求朝廷决策应遵从天下公论,这是对绝对皇权的挑战。事实上,东林党人也是作为一支以天下公论对抗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出现在晚明的朝野。这里还要提醒一下,东林书院,特别是后起的复社,虽名义上为文社,但已发展出近代政党的若干性质,有组织,有会约或盟词,不讳言自己是朋党,公开活动——活动也不仅仅是讲学,而且“往往訾毁时政,裁量公卿”,以至于“岩廊之上(指朝廷),亦避其讽议”(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送沈公厚南还序》)。它上承汉代处士、议士、太学生的清议传统,下启晚清政治性“学会”的兴起,显示了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内在动力。#p#分页标题#e#
明末儒家对专制皇权的反思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顾炎武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与儒家的共治主张一脉相承;明代废相后君主专制所产生的诸多政治恶果,更让另一位明末大儒黄宗羲认识到“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为限制君权,应当“公其是非于学校”,使“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学校》),黄氏设想中的“学校”,已具有近代议会的功能;同时代的王夫之甚至提出了“虚君立宪”的构想(严格来说,称其为“构想”并不准确,因为王夫之认为这乃是“三代”已有的古法):“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卷三十)。
如果说西汉董仲舒试图用来约束君主的“天道”多少有些缥缈,那么船山先生构想的“预定奕世之规”,显然已有了“立宪”的意义。只可惜,明室已倾覆,明儒的君宪思想没有获得去指引建立一个君宪政体的机会。以异族入主中原的八旗部族,所恢复的是专制程度比朱明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制,揉合了秦制传统与草原主奴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