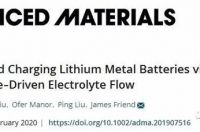“如果人类有了更强的观测手段,薛定谔的猫的模态并非不能观测……”朋友在饭桌上的一席话差点呛到我,我想对他说,你太在意那只猫的生死了,完全没有理解这只与芝诺乌龟,拉普拉斯兽、麦克斯韦妖齐名的物理学界四大神兽对于整个人类科学的意义何在。
自1088年欧洲第一所大学诞生“自然魔法”的教学标志着以实验为基础的当代自然科学登上历史舞台,到之后文艺复兴奠定了人本主义,所有现当代科学最坚实的根基就是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而意识不过是附着于人类这个物种上产生的东西,除了脑科学,意识这个概念甚至都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之中。
然而薛定谔的猫这个隐喻却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人类细思恐极的发现这将通往《三体》中要了叶文洁女儿杨冬半条命的那个结论:物理学并不存在,而这与三体人的智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切都是由薛定谔意识中产生的这只该死的猫引起的。
当我们不观察时,月亮是不存在的
作为量子理论的先驱并戏剧性的变成其死敌的薛定谔,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只已经逐渐成为量子理论图腾的猫其实是他为了嘲笑哥本哈根学派,用来反对量子论而设定的一个思想实验。
他在1935年为了响应爱因斯坦对于量子理论的攻击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量子力学的现状》(Die gegenwartige Situation in der Quantenmechanik),文章极尽讽刺刻薄,一副与哥本哈根学派誓不两立的样子。
在论文的第5节,薛定谔描述了那个常被物理学界视为噩梦的实验。哥本哈根学派不是说,在没有测量之前,一个粒子的状态模糊不清,处于各种可能性的混合叠加。比如一个放射性原子,它何时衰变是完全概率性的。只要没有观察,它便处于衰变/不衰变的叠加状态中,只有确实进行了测量,它才能随机选择一种状态出现吗?
很好,那么让我们把这个原子放在一个不透明的箱子(薛定谔想象了一种结构巧妙的精密装置)中让它保持这种叠加状态。,每当原子衰变而放出一个中子,它就激发一连串连锁反应,最终结果是打破箱子里的一个毒气瓶,而同时在箱子里的还有一只可怜的猫。事情很明显:如果原子衰变了,那么毒气瓶就被打破,猫就被毒死。要是原子没有衰变,那么猫就好好地活着。
但这样一来,显然就会有以下的自然推论:当一切都被锁在箱子里时,因为我们没有观察,所以那个原子处在衰变/不衰变的叠加状态。因为原子的状态不确定,所以它是否打碎了毒气瓶也不确定。而毒气瓶的状态不确定,必然导致猫的状态也不确定。只有当我们打开箱子察看,事情才最终定论:要么猫死掉了,要么它活蹦乱跳。但问题来了:当我们没有打开箱子之前,这只猫处在什么状态?似乎唯一的可能就是,它和我们的原子一样处在叠加态,也就是说,这只猫当时陷入一种又死又活的混合状态。
奇哉怪哉。现在就不光是原子是否是幽灵的问题了,现在猫也变成了幽灵。一只猫同时又是死的又是活的?它处在不死不活的叠加态?这未免和常识太过冲突。
薛定谔的实验把量子效应放大到了我们的日常世界,现在量子的奇特性质牵涉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牵涉到我们心爱的宠物猫究竟是死还是活的问题。这个实验虽然简单,却比之前爱因斯坦的攻击要辛辣许多,甚至连哥本哈根学派都不得不承认:是的,当我们没有观察的时候,那只猫的确是又死又活的。
但这个推论如果成立,那么不仅仅是猫,一切的一切,当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都是处在不确定的叠加状态的,因为世间万物也都是由服从不确定性原理的原子构成的。
因此,在物理学派内部一直有一个非常极端的论调:“当我们不观察时,月亮是不存在的。”因为月亮也是由不确定的粒子组成的,所以如果我们转过头不去看月亮,那一大堆粒子就开始按照波函数弥散开去。于是乎,月亮的边缘开始显得模糊而不确定,它逐渐“融化”,变成概率波扩散到周围的空间里去。当然这么大一个月亮完全“融化”成空间中的概率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不过问题的实质是:要是不观察月亮,它就从确定的状态变成无数不确定的叠加。不观察它时,一个确定的、客观的月亮是不存在的。但只要一回头,一轮明月便又高悬空中,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如果月亮是如此,那么整个宇宙呢?
无限复归
事实上,到这里为止,还没有失控,虽然那时候物理学家们已经有些觉得不对劲了。
猫处于死/活的叠加态?人们无法接受这一点,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奇异的二重状态似乎是不太可能被一个宏观的生物(比如猫或者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猫当然不能告诉我们它当时在箱子里到底处于什么状态,那如果把一个会说话的人放入箱子里面去。这个人如果能生还,他肯定无比坚定地宣称,自己从头到尾都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什么半生半死的状态出现。可是,这次不同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是一个观察者了啊!他在箱子里不断观察自己的状态,从而不停地触动自己的波函数坍缩!
奇怪,为什么我们对猫就不能这样说呢?猫也在不停观察着自己啊。猫和人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区别就在于,一个可以出来愤怒地反驳量子论的论调,另一个只能“喵喵”叫吗?令我们吃惊的是,这的确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分别!人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存活,而猫不能,换句话说,人有能力“测量”自己活着与否,而猫不能!人有一样猫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意识”!因此,人能够测量自己的波函数使其坍缩,而猫无能为力,只能停留在死/活叠加任其发展的波函数中。
意识!这个字眼出现在物理学中真是难以想象。
这太荒谬了,这个时候冯·诺依曼出场了,没错,就是那个在现代计算机、博弈论、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领域内的科学全才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计算机之父”、“博弈论之父”的天才,他给出了一个更为刺激的结论。
每当我们观测时,系统的波函数就坍缩了,按概率跳出来一个实际的结果,如果不观测,那它就按照方程严格发展。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过程,后者是连续的,在数学上可逆的、完全确定的,而前者却是一个“坍缩”,它随机,不可逆,至今也不清楚内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这两种过程是如何转换的?是什么触动了波函数这种剧烈的变化?是“观测”吗?
冯·诺伊曼敏锐地指出,我们用于测量目标的那些仪器本身也是由不确定的粒子组成的,它们自己也拥有自己的波函数。当我们用仪器去“观测”的时候,这只会把仪器本身也卷入到这个模糊叠加态中去。怎么说呢,假如我们想测量一个电子是通过了左边还是右边的狭缝,我们用一台仪器去测量,并用指针摇摆的方向来报告这一结果。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这台仪器本身也有自己的波函数,如果我们不“观测”这台仪器本身,它的波函数便也陷入一种模糊的叠加态中!诺伊曼的数学模型显示,当仪器测量电子后,电子的波函数坍缩了不假,但左/右的叠加只是被转移到了仪器那里而已。现在是我们的仪器处于指针指向左还是右的叠加状态了!假如我们再用仪器B去测量那台仪器A,好,现在A的波函数又坍缩了,它的状态变得确定,可是B又陷入模糊不定中……总而言之,当我们用仪器去测量仪器,这整个链条的最后一台仪器总是处在不确定状态中,这叫作“无限复归”(infinite regression)。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我们把用于测量的仪器也加入到整个系统中去,这个大系统的波函数从未彻底坍缩过!
可是,我们相当肯定的是,当我们看到了仪器报告的结果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我们自己不会处于什么荒诞的叠加态中去。当我们的大脑接受到测量的信息后,波函数就不再捣乱了。
奇怪,为什么机器来测量就得叠加,而人来观察就得到确定结果呢?难道说,人类意识(Consciousness)的参与才是波函数坍缩的原因?只有当电子的随机选择结果被“意识到了”,它才真正地变为现实,从波函数中脱胎而出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只要它还没有“被意识到”,波函数便总是停留在不确定的状态,只不过从一个地方不断地往最后一个测量仪器那里转移罢了。在诺伊曼看来,波函数可以看作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一个矢量,而“坍缩”则是它在某个方向上的投影。然而是什么造成这种投影呢?难道是我们的自由意识?
换句话说,因为一台仪器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指针是指向左还是指向右的,所以它必须陷入左/右的混合态中。一只猫无法“意识”到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所以它可以陷于死/活的混合态中。但是,你和我可以“意识”到电子究竟是左还是右,我们是生还是死,所以到了我们这里波函数终于彻底坍缩了,世界终于变成现实,以免给我们的意识造成混乱。
延迟实验
如果说“意识”使得万事万物从量子叠加态中脱离,成为真正的现实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自然的问题:当智能生物尚未演化出来,这个宇宙中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它的状态是怎样的呢?难道说,要等到第一个“有意识”的生物出现,宇宙才在一瞬间变成“现实”,而之前都只是波函数的叠加?但问题是,“智慧生物”本身也是宇宙的一部分啊,难道说“意识”的参与可以改变过去,而这个“过去”甚至包含了它自身的演化历史?
很快就有人证明了这个结论。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在他生前工作的普林斯顿召开了一次纪念他的讨论会。在会上,爱因斯坦的同事,也是玻尔的密切合作者之一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提出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构想,也就是所谓的“延迟实验”(delayed choice experiment)。根据哥本哈根解释,当我们不去探究电子到底通过了哪条缝,它就同时通过双缝而产生干涉,反之,它就确实地通过一条缝,顺便也消灭了干涉图纹。然而,惠勒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思维实验指出,我们可以“延迟”电子的这一决定,使得它在已经实际通过了双缝屏幕之后,再来选择究竟是通过了一条缝还是两条!
想象你去看电影,虽然你对电影内容一无所知,但很明显,既然已经剪完上映,说明这部电影早已杀青。但走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你却被告知,只要你从左门进去,就会发现是吴秀波主演,而只要从右门进去,它就会是胡歌主演的。换句话说,这部电影当初的主演是谁,可以由你换个场次来决定!
延迟实验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虽然听上去古怪,这却是哥本哈根派的一个正统推论!惠勒后来引用玻尔的话说,“任何一种基本量子现象只在其被记录之后才是一种现象”,光子是一开始还是最后才决定自己的“历史”,这在量子实验中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在量子论看来,历史不是确定和实在的——除非它已经被记录下来。更精确地说,光子在通过第一块半透镜到我们插入第二块半透镜之间“到底”在哪里,它是个什么,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我们没有权利去谈论这时候光子“到底在哪里”,因为在观测之前,它并非是一个“客观真实”。
在惠勒的构想提出5年后,马里兰大学的卡洛尔·阿雷(Carroll O.Alley)和其同事当真做了一个延迟实验,其结果真的证明,我们何时选择光子的“模式”,这对于实验结果是无影响的!与此同时,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小组也作出了类似的结果。
这下彻底乱了!
意识决定物质
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宇宙的历史说不定可以在已经发生后才被决定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目前宇宙似乎是在以一个“恰到好处”的速度在膨胀。只要它膨胀得稍稍快一点,当初的物质就会四散飞开,而无法凝聚成星系和行星。反过来,如果稍微慢一点点,引力就会把所有的物质都吸到一起,变成一团具有惊人密度和温度的大杂烩。而我们正好处在一个“临界速度”上,这才使得宇宙中的各种复杂结构和生命的诞生成为可能。这个速度要准确到什么程度呢?大约是1055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你从宇宙的一端瞄准并打中在另一端的一只苍蝇(相隔300亿光年),所需准确性也不过1030分之一。类似的惊人准确的宇宙常数,我们还可以举出几十个。
在薛定谔的猫实验里,如果我们也能设计某种延迟实验,我们就能在实验结束后再来决定猫是死是活!比如说,原子在一点钟要么衰变毒死猫,要么就断开装置使猫存活。但如果有某个延迟装置能够让我们在两点钟来“延迟决定”原子衰变与否,我们就可以在两点钟这个“未来”去实际决定猫在一点钟的死活!
这样一来,宇宙本身由一个有意识的观测者创造出来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虽然从理论上说,宇宙已经演化了几百亿年,但某种“延迟”使得它直到被一个高级生物观察之后才成为确定。我们的观测行为本身参与了宇宙的创造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参与性宇宙”模型(The Participatory Universe)。宇宙本身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其中的生物参与了这个谜题答案的构建本身!
你肯定很奇怪:为什么宇宙恰好以这样一个不快也不慢的速度膨胀?人择原理的回答是:宇宙必须以这样一个速度膨胀,不然就没有“你”来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个速度膨胀,生命和智慧才有可能诞生,从而使问题的提出成为可能!从逻辑上来说,显然绝对不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的宇宙以一个极快或者极慢的速度膨胀?”因为如果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成立,那这个“宇宙”不是冰冷的虚空就是灼热的火球,根本不会有“人”存在于此,也就更不会有类似的问题被提出。
参与性宇宙是增强版的人择原理,它不仅表明我们的存在影响了宇宙的性质,甚至我们的存在创造了宇宙和它的历史本身!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各种宇宙常数首先是一个不确定的叠加只有被观测者观察后才变成确定。但这样一来它们又必须保持在某些精确的范围内,以便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令观测者有可能在宇宙中存在并观察它们!这似乎是一个逻辑循环:我们选择了宇宙,宇宙又创造了我们。这件怪事叫作“自指”或者“自激活”(self-exciting),意识的存在反过来又创造了它自身的过去!
这仿佛就是最后的结论,我们的这个宇宙竟然是由于我们的意识才产生或者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