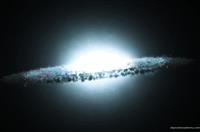
(本文根据2012年5月21日晚作者在南京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也许各位在座的来宾已经注意到了,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南京的文学现代史”,而不是现代文学史,这样一个词汇的特别安排是有着自己的用意的。长久以来,我对于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兴趣。在我们现在一般学科所定义的文学史的观念和实践上,往往是以文学作品作为串联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起承转合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学史似乎只是以大的历史作为进入文学脉络的一个方式而已。但在以下的一个半小时里,我却希望刻意地调动文学与现代史这两个关键词,让这两者之间真正地产生互动。我所谓的文学现代史,未必只是文学的创作在一个历史的时间进程里所呈现的纪念碑式的意义;我所谓的文学史,更应该和历史本身的互动产生无数交汇、或者是冲刺、或者是对话、或者是矛盾的机缘。以下以十一个不同的关键时刻,或是十一个不同的故事,来说明我个人的看法。然后在问答的时间,想听听大家对我的意见和批评,同时也说明在这样一个讲题之后它所隐藏的方法学和理论上的架构。
最后说说关键这两个字,关键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相当古远的修辞。早在近代时期,这个“关键”已经被用在作为家具尤其是门锁、窗户等的开关设置,通常我们讲到关键的时候,我们希望锁定一样东西,尤其是留住它的意义,然后经过关键的作用,来认知在历史上某一个时刻、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作品它所带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今天却想讲,关键这个词不但是锁定的意思,相反,它也可能是开启的意思,经过关键的作用,让原来看起来密丝合缝的任何机构、任何机制再次展现它的可能性。与其我们用关键这样一个观点或方式,把任何的事件再一次凝聚到一个时间的、一个似乎是不可逆转而且在意义上变成非常固定的这样一种做法,不如以以下的十一个关键时间,把这个历史再次开创出来,再次地展现出文学和历史在时间的脉络里所呈现的不同意义。
南京在文学史和所谓的广义的历史上它所承载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在座的很多同学肯定在来到这所学校之前,早就对这座城市有固定的认知以及心向往之的一些投射的想象。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号称十朝古都,而南京从东晋以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名字,从建康到建业,从秦淮到金陵,到今天我们约定俗成的南京。在历史上的各个不同点,各种不同的命名方式,也诉说了这个城市在不同时期不同命运的转折。而在过去我们看待南京的这个文学所铭刻的历史经验里面,最早从六朝以来,像左思的《三都赋》之《吴都赋》、庾信的《哀江南赋》中的“大盗移国,金陵瓦解”等等这些描写,这个城市已经见证了历史和文字铭刻无数可能里面的不同的书写方式。而后呢,大家更熟悉的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更不用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南京的形象总是隐隐约约地呈现在字里行间。到了近现代,不论我们谈到鲁迅对于南京的经验,在1897年5月7日他来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展开了他离开故乡绍兴之后的第一次人生历险。或者是到了现代之后,像俞平伯或其他文人对于南京的形形色色所留下来的他们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新颖的记录。这些都作为我今天所探讨的背景,但是如何去选择这十一个关键时刻,或者说这十一个关键时刻是不是对于在座的各位都有同样的一个所谓同理的感觉,我不确定。但是我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作为大家参考的对象,所以现在我开始说明这所谓的关键时刻它可能带来的意义。
我选择的第一个关键时刻,是1911年12月29日,在这一天,独立十七省代表齐集南京,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而我所要强调的是一位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波折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学者、诗人丘逢甲,所谓的“海东第一才子”。那么在这个时间,丘逢甲作为广东临时军政府的三位代表之一,也来到了南京,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好,可是丘逢甲却认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对他个人有刻骨铭心的意义。那么任何对于丘逢甲前半生的历练有所认知的来宾都知道,他是参与了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民主国建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么,以他的才华和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却没有办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在1896年,丘逢甲必须离开台湾,他所曾经幻想的台湾民主国在日军登陆以后的几天之内就崩溃于无形。我们先来看一首诗,这是他在1912年1月上旬在南京留下的十首诗中的重要一首:
谒明孝陵
郁郁钟山紫气兴,
中华民族此重行;
江山一统都新定,
大纛鸣笳谒孝陵。
作者来到明孝陵前,有无限的感触。看看国家对于未来的憧憬,回想他个人所来之处,他真是感慨万千。台湾民主国失败之后,丘逢甲回到了祖国大陆,在这以后的后半生郁郁以终。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就是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各种各样在文化、政治以及在宗法上的关联。我们现在看1896年4月17日,当时他已经离开台湾大半年了,他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春愁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是1896年丘逢甲在广东所作的一首感时诗,但是丘逢甲的心意不应该止于他个人在台湾的这一场没有成功的政治事业,同时他在拜谒明孝陵的时候,他的历史的眼光投向更久远的所谓大的改朝换代里面的兴亡之感,他想到的可能有郑成功。这是郑成功在1659年所题的一首诗,这首诗和南京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缟素临江誓灭胡,
雄师十万气吞吴;
试看天堑投鞭渡,
不信中原不姓朱。
这一年,郑成功击退了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大军进入长江口,几乎打到了南京,希望以这样一场战役作为恢复明朝的基础。但是,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功亏一篑,而他的愿望成为永远的遗憾。所以,丘逢甲在三百多年之后,回看这一页历史,他不禁感慨南京光复临时政府又在兹地,即1912年1月民国当有三大文字祭告孝陵、延平、洪王也。孝陵指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明孝陵这一段掌故,延平呢,延平郡王,讲的是郑成功和南京的关联,而洪王,讲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所以,一首简短的诗歌,或者一个文人他在历史上驻足的那一个刹那,让我们了解到文学所能够见证的历史兴亡往往超出了我们个人阅读诗歌所能够想象的,而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讨论文学与历史互动的时候特别能够心有戚戚焉的时间的焦点。这是今天我介绍的第一个关键时刻,这是1912年。
时间现在又过了十年,到了1922年,这一年的一月,在鼓楼北二条巷二十四号吴宓教授的家中,一群当时在东南大学教书的教授和学者们,他们商议创办了《学衡》杂志。这个杂志应该说是南京大学传统里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南京大学所代表的文人传统的骄傲。我们都知道,在“五四”之后,中国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当时,《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是引领一时之风骚。在这样一个强调“启蒙”、“革命”的激进的历程里,却有一群知识分子以南京为根据地,倡导了一种不同于北方的、不同于《新青年》式的那种完全西化的“启蒙”、“革命”观点,而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事业。这个事业最重要的一个刊物,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学衡》杂志。我想大家对这个题目都已经了然于胸,也做过相当的研究,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我在这里要讲的是,1922年前后《学衡》杂志在刚刚创办的时候,有三位重要的人物,这三位重要的人物不仅和以后的南京大学的文学传统有着深远的关系,也和我现在任教的哈佛大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他们都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们是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尤其是胡先骕,他其实是一位植物学家,但对文学的复兴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创办了《学衡》,希望以《学衡》杂志的宗旨对过去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传统进行再次的思考和复兴,而让这样一种儒家传统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古典传统有所对话,形成一个贯串的、东西对话的、比较文学式的观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事件。可是,在1920年代的初期,当所谓的革命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的时候,《学衡》杂志往往被认为是特别保守的,比如提倡文言文、提倡儒教的思想等等。所以,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学衡》杂志被认为是不够进步的、比较保守的一种学术风格,或者说是学术的一种比较保守的理念。但是,又过了很多年之后,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学衡》杂志诸君子对于“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所作的思考和贡献,突然了解到,原来中国的现代化不见得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不是只有以西方至上的革命启蒙才能达成的。
而到了今天,我们更了解到,当所谓的儒教的观点再次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项目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衡量《学衡》的贡献,尤其是《学衡》杂志和哈佛大学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因缘。至少,我们知道白璧德教授在1910年代曾经收过一些优秀的学生,特别是有一些学生慕名而来,心向往之。而其中不仅包括了刚才所说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同时包括了当时在哈佛留学的陈寅恪、汤用彤等,不管有没有选过他的课,他们基本上都信服他的理念。对于白璧德来讲,世界文明的演进,不能以简单的进化论式的方法来论成败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整个西方的工业化所代表的文明面临一次战争所带来的重大挫败的时候,眼前无路想回头,想到的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教育的重要,想到的是中国所代表的儒家传统的重要,所以,在这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思考、不同声音,再次有了交汇的可能。而在白璧德教授的教诲之下,他的弟子回到中国之后展开了他们个人的文化事业,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学衡》的事业。到了今天,尤其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当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已经超过了三四百所的时候,当孔子的塑像在大学校园里重新树立之后,当和谐社会成为政治体制的一个新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白璧德先生,或者是吴宓他们所代表的《学衡》学派的理念,并不过时,而且在这个世纪可能是一种新的突破。这一点,是我在这里所提出来的,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
时间又过了十年,到了1932年的春天,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央大学的中文系有一位新来的女学生,她叫沈祖棻。她是在1931年的秋天来到这所知名的大学的,那一年,她选了一门词选课,是由当时的院长兼系主任汪东教授所主持的,在这个课上,有一门作业是所有的学生必须以他们所学到的各种各样的词学知识来自己填词。当时,这位女学生填了一首叫做《浣溪沙》的词:
浣溪沙
芳草年年记胜游
江山依旧豁吟眸
鼓鼙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
一天风絮独登楼
有斜阳处有春愁
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以传统的风格所作的词,但是我们仔细去体会这首词的意味,然后映照着当时的中国的政治情况,我们突然理解到了,这位年轻的女学生她所作的词不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只是简单的浅吟低唱而已。她想到的是,在“九一八事件”前后中国所面临的再一次的政治危机。所以,在这里,一个古典的词的文类和现代所谓最极端的、最刻骨铭心的政治事件有了接轨的机会。在这里,古典的诗词在现代文学里何尝落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以古典诗词所吟诵出来的许多重要篇章,仍然应该被我们视作是现代文学史里一个重要的部分。而沈祖棻教授她在当时所作的诗词,还有日后她对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在教学上所作的贡献,我想这应该是今天看待南京大学所代表的文学传统时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同时,我们当然也知道,在诗词之外,沈祖棻教授和程千帆教授他们令人难忘的罗曼史,这一点比现在的偶像剧还来得更凄美感人。在很多时候,我们几乎要把沈教授和程教授他们一生的坎坷遭遇,还有他们诗词之间所互相倾诉的各种各样的国仇家恨的这种衷肠,看做是一个在李清照、赵明诚之后现代中国的再一次对诗词这一传统的文类的致敬。而且我做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程教授是1913年出生的,他比我们的沈教授年轻四岁,这是标准的姐弟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另外的一种佳话。这时我们看待文学史和文学的现代史里面各种不同的公私之间的个人境遇,还有借着文字所铭刻的各种各样的兴亡之感,就有了非常绵密交错的关系。当然我们都知道,沈教授和程教授他们在三四十年代颠沛流离的经验,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感受到的。也就是在这个患难的过程里,沈祖棻教授居然填出了将近五百六十首词,到今天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学里的古体风格的诗词范本。这是刚才讲到的第三个关键时刻。
下面我要讲到的,也是1932年,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在那一年的春天,当我们的沈祖棻同学在中央大学的校园里徘徊的时候,曾经见到一位年纪四十岁左右、长得人高马大的美国女士,当时她在金陵大学教英文,她是一位很不快乐的家庭主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她始终维持在婚姻的状态里。1932年,这位郁郁不得志的英语教师(她后来的中文名字叫赛珍珠),出版了她的英文小说The Good Earth(《大地》),这个小说让她一鸣惊人,一夜之间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的作家。在以后,她的大名不只是流行在英美的文学界,而且再一次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这片土地。我想,在中国,在西方,赛珍珠的大名真的是特别地重要。一直到了1990年代的末期,当美国前任总统布什接受南京大学的荣誉博士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他当年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也正是因为阅读了赛珍珠的《大地》以及其他作品。所以,文学的力量有时候是难以估计的。在当时,就像我所说的,这是一位并不快乐的英文教师,这位教师出生四个月之后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尤其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仍然保留了重要的古迹——赛珍珠的故居,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觉,我们的现代的中国文学史或南京的现代文学史里面,是不是也应该包含了非华语所创作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呢。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认知,是不是仍然以传统的中文或者是白话文所写出来的作品,才认为是现代的一部分呢。所以,这些问题就逐渐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对象了。附带一句话,赛珍珠女士在1938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美国第一位得到这个奖项的女作家。这是赛珍珠的故事。
时间到了1939年的年底,当时,抗战已经开打到第三年了。在这一年的年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有了结果。有一位叫阿垅的军官,得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小说奖。他的作品的名字,就叫《南京》。这部作品是这位军官1938年在战争之暇一点一滴写下来的,而这个故事的内容,讲的正是1937年11月24日到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保卫战,那对于南京现代史来说是最不能磨灭的一页。我们从今天的文学的文献资料来看,《南京》这部长篇小说都是我们在记录南京保卫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个重要的文本。这个文本何其讽刺地要搁了五十年之后才第一次出版。为什么耽搁了这么多年,这里面的故事是我接下来要诉说的。这本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以完整的面目出版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版,题目都叫做《南京血祭》,这个题目是后来的编者在删节之后所取的一个书名。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没有一个重量级的史诗的作品来见证这一场民族的大灾难。而这部作品却埋藏在各种各样的书堆之后,几十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阿垅研究的学者或者同学,或者对于胡风这个系统——“七月”的文学传统有所认知的学者或同学。阿垅是属于“七月派”里面的一位作家,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一名年轻的军官。他曾经参加了淞沪战争的闸北保卫战,军队退守之后,来到南京,之后一路撤退,所以他看到了中日战争前期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最惨烈的现象。而当时,我们这位年轻的军官,心里面已经酝酿着另外的一种政治的理想或主义,在以后的这些年里面,他发掘了胡风所率领的文学集团所呈现的革命意义,或者说所呈现的对于人能超越自己有限的肉身的限制,来形成一种新的革命的乌托邦的动力和希望。他是“七月派”里的一员大将,1937年南京保卫战撤退之后,阿垅身负重伤,他于1938年来到延安,到延安之后,由于健康原因,他又再次来到西安求医,在这个求医的过程里,他一点一滴地写下了这本书。那么这本书为什么到了五十年之后才出版呢?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疑问。我想第一个原因是,有很多很多年里,胡风反革命集团是这个政权里所不能容忍的一支文学的逆流。而阿垅在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被打入了监狱。以后在“文革”之初,他在最凄惨的状况下,在狱中因病而死,没有得到任何的医疗救助。而这位曾经出身黄埔的军官,对于革命却曾经有如此的崇高向往。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他沾染了胡风系统这样一种不同的文学诉求,而且在写南京保卫战的时候,他并没有赞美当时的军队如何英勇抗敌,而是写率领军队的一位将军是怎样误判了当时的局势,导致号称要坚持六个月的南京保卫战何以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之内溃不成军。他也没有写当时的南京人民是怎样英勇地抵抗日本这些残暴的军队进入这个城市,相反的,阿垅给我们的一个画面是,在各种各样的混乱的局面里,这些军人如何以他们自己的血气之勇、自己的对于抗战的信念作出了他们最有限的血肉拼搏。这里面,有英勇赴义的军人,也有临阵脱逃的军人,有在南京大屠杀前夕蜂拥离开南京溺死在长江中的平民百姓,也有最后一刻苟延残喘,向日寇示好的各种各样的百姓,有各种各样在乱世里面苟且偷安的军人和人民。所以,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画面,也不是以后我们在强调伟大的革命历史小说里面所向往的那种所谓崇高的、雄浑的、史诗式的文学。因此,在阿垅的写作中,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他对于现实写实主义有着一个最深刻的认知,现实或写实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它必须是泥沙俱下,它必须是掺杂了各种各样人生的可悲的、可喜的、可叹的现象。在这种掺杂之下,阿垅几乎是以一个像诗人般的作家的手笔,写下了他个人的见证。所以,不论是哪一个政权来看待《南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当然是觉得不安的。我们想象的革命应该是史诗式的革命,我们想象的战争应该是抛头颅洒热血的义无反顾的过程。而阿垅,在胡风对于文学坚持的这样一种信仰里,他强调的却是人性最卑微的、最底层的一个自我奋斗的过程,非常地艰苦,有胜利的时候,有挫败的时候。所以,我个人在阅读《南京血祭》的时候,还是非常感动的。这是1939年阿垅和南京的故事。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吴浊流,时间是1941年1月12日至1942年3月21日,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比较陌生,不管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南京的现代文学史都不怎么承认这位作家的位置。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在这里我讲到的一个原因是:他是一位从殖民地台湾地区来的拿着日本护照的中国台湾人。在1941年的年初到1942年,吴浊流曾经有一个机会来南京并在这里住了一年零三个月,他来到南京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满日本在台湾地区的暴力统治。时间已经进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时期,在台湾地区的任何有一点反抗意识的年轻知识分子都会觉得这个时间已经不再能够被容忍,而吴浊流恰恰是其中之一,他向往着他心目中的祖国。而在这一年的一月,他来到了南京,而这时的南京是汪精卫政府治下的南京。
在这个地方,他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大陆新报》的记者,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四处采访,看到了生活的形形色色。当时,他把自己所见到的各种观感写下来,是用日文写的,这些小的文章的合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京杂感》。不管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观点,从殖民地台湾来到战时的南京,从一个既是外乡人,又是一个在心目中自我认同中国的台湾地区被殖民者的观点来看待南京的这样一个记录。在吴浊流的笔下,南京所留给他的印象却是有好有坏的。吴浊流对南京的市容有很好的印象,但是他也注意到了在南京的中国人在战争里的各种各样的行径并不为他所认同。他想象的祖国是一个所谓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祖国。而在当时汪伪政权之下的南京,就是一个平常百姓过日子的南京。这当然代表了中国人一个强韧的生存意志和适应现实的能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吴浊流却不禁地感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难道真的不如在报纸上、在宣传上所显现的那样强烈吗?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到了1942年,吴浊流觉得南京也非久留之地,他又回到了台湾。书中有一段引言充分地说明了吴浊流在《南京杂感》里对他自己暧昧的身份的一种感慨的抒发:
章君还提醒我,应该隐秘台湾人的身份。……我们约好对外说是广东梅县人。……在大陆,一般地都以“番薯仔”代替台湾人。要之,台湾人被目为日本人的间谍,……那是可悲的存在。这原因,泰半是由于战前,日本人把不少台湾的流氓遣到厦门,教他们经营赌场和鸦片窟,以治外法权包庇他们,供为己用。结果祖国人士皂白不分,提到台湾人就目为走狗。这也是日本人的离间政策之一。开战后日本人再也不信任台湾人,只是利用而已。台湾人之中有不少是抗战分子,为祖国而效命,经常都受着日本官宪监视。来到大陆,我这明白了台湾人所处的立场是复杂的。
这简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吴浊流这种非常暧昧的内心情怀,一方面他希望融入到祖国的社群里,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轻易地和中国合在一起,而另外的一方面,他又绝对不能认同日本。所以这种种的观念到日后都形成了在1946年他所出版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这本书的名字到今天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而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罗大佑那首非常流行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它的源头正是来自于吴浊流在1946年以日文写出来的这本小说。而这本小说,我们通常认为是现当代台湾文学最重要的一个开端。在这个小说里面,吴浊流以孤儿这个意象来说明在那个时代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民无所适从的、荒凉的漂泊感。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而南京与吴浊流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仍然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这是我讲的吴浊流的故事。
接下来呢,到了第七个关键时刻,1947年5月至7月在香铺营文化会堂有一个新的话剧上演,这个话剧的名字叫《云雀》,而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路翎。路翎是一位天才作家,他在十六岁到十九岁这短短的几年内写尽了他到今天我们都认为是现代文学里的重要杰作,包括《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等,我想我们任何做现代研究的同学都不应该错过这位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1947年的路翎只有二十四岁,在抗战之后,他回到了故乡南京。在这个时候,他写出了五幕话剧《云雀》,来说明战后的那一代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在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时,那种不知何去何从的惶惑的感觉。作品在风格上非常像路翎的左翼现代风格,几乎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风格,但却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左翼背景作为它的基础。而在这个戏剧里面的几位年轻的男女,在当时的南京,到底对他们国家的前途、对个人自身的前途要作出什么样的抉择,我们没有答案。而又过了两年之后,当大的历史巨变来临之后,路翎才终于觉得他的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归宿。这是以后的故事了。在这里,我特别强调的是1948年路翎也在中央大学找到了教书的工作,他教的是文艺与创作,教了一年半,一直教到1949年。在这个意义上,路翎也是南京大学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路翎的后半生是极为凄惨的,作为胡风集团的一份子,路翎在1955年之后也深受牢狱之灾。等到1970年代末被平反之后,他的脑袋已经坏掉了,已经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路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故事。可是即便如此,他日后还是有很多的作品留下来,到今天都没有印出来。我个人以为,作为一个南京的作家,路翎的一生,还有路翎一生重要的作品,到了今天仍然无法以全貌发表,这可能是南京的一个遗憾。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值得我们再次致敬。《云雀》的后记在这里我们顺带一起看一下,看一下路翎式的、或者说是胡风式的对于生命和革命之间的关联的看法:
生活斗争和人生斗争,也就是社会斗争,每一面都是具有它底历史的真实的。我们底知识分子们,中国底为新的生活而斗争的人们,我们底兄弟们,是每走一步都流着鲜血,跨过他们底亲人们底尸体而前进着的。
路翎文章的风格在于这样一种非常扭曲的写作的句型,尤其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斗争”两个字不是后来毛泽东所讲的“斗争”,这是一种胡风式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斗争”。
现在,我们到了第八个关键时刻,时间到了十年之后的1957年,在当时南京的文艺界,有一群年轻的作家,因为“双百方针”的关系,他们以为形势一片大好,于是居然合在一块,想自己创造一番文化事业。但这个事业还没有起步,就已经受到了阻挠,胎死腹中了。这些年轻的作家们日后有些人是鼎鼎大名的作家,但每一个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都有非常坎坷的遭遇。他们的名字是方之、陆文夫、高晓声、叶志诚,这些名字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但至少在“文革”之后,高晓声以“陈奂生”系列、方之以《内奸》这样一部小说、陆文夫以《美食家》等作品,卷土重来,证明了当时这些年轻的“探求者”,在1980年代,仍然在不断地探求,作出了对新时代的见证或者说是回顾。而更有意义的是,他们后继有人,比如叶志诚的儿子叶兆言,是我们南京一位指标性的优秀作家,方之的儿子韩东,是以一种强烈的、惊世骇俗的风格来作出一种革命性转变的南京先锋式的作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两代之间的对话,两代人所看到的南京文坛的起起落落,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反省。
我们接下来再探求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居然发现,张爱玲和南京也有很多的关系。任何有关文学的演讲都少不了张爱玲。所以今天,我很努力地找到了南京和张爱玲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还蛮深的。我们发现,原来张爱玲在她中年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小说《半生缘》,它的故事就发生在南京。南京是顾曼桢和沈世钧开始恋爱的地方,要经常迂回于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这段恋爱谈得高潮迭起,谈得荡气回肠。而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我们回不去了。”张爱玲的家族和南京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因为她的外祖母李菊耦的父亲正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当时的整个家业都在南京。之后,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也在南京有了家产。据我个人的研究,李鸿章的祠堂还有张佩纶的故居都是以一个十分残破的状态仍然保留着。这是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对晚清这样一个构成的致敬。但我们记得更清楚的可能是,在1943年11月的《古今》杂志上,出现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当时,在汪伪政权下任职的胡兰成有一天翻开杂志,看到了《封锁》这个故事,惊为天人。于是,开始了的张胡之恋。所以张爱玲和胡兰成,以及我们永远难忘的南京,他们总算发生了关系,所以我们也觉得安心了。
但是,为什么1967年在我们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呢,话又绕回来了,因为1967年,张爱玲和他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居然因缘际会有了机会来到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驻校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很骄傲地说,张爱玲和哈佛大学也有关系。在哈佛大学,张爱玲完成了她对《十八春》这个故事的修订,我们知道《十八春》是张爱玲在1951年留在大陆的最后几本小说中的一本。这本小说,原本有许多相当正确的政治成分在里面,可是,日后她不太满意她的《十八春》,所以经过了许多年的修订,到了1967年《半生缘》出现了,故事的梗概还是相似的,但是整个故事的行进和运作更为合理,让我们觉得更为迂回不已。到了今天,我们知道其中有两段最著名的话:
“我们回不去了。”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和南京是有着渊源的。那么同时呢,连接着张爱玲,我们也来说说另外一位重要的作家白先勇。他的最有名的一个短篇小说《台北人》里面的《游园惊梦》的最重要的背景其实不是台北而是南京。对于白先勇来讲,《台北人》这样的一个小说,它的底色是以南京为基础的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到台湾之后那一代大陆人的心影的写照。而这个故事又何尝不是白先勇自己的故事的一个延伸版。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曾经是国民党时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而白先勇也曾经在1946年之后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于南京的熟悉是有亲身体会的。几十年过去了,《游园惊梦》真的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仿佛春梦一场。这是我们连带张爱玲所联想到的一些可能。
现在来到了第十个所谓的关键时刻,时间到了当代文学时期,我们有太多的选择,我们知道南京的作家是一群特别精彩的作家,那么特别选择了叶兆言,主要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是地道的书写南京的作家,而是他有一部作品《夜泊秦淮》真是说中了南京忧郁的那个抒情的层面上最精彩、最精致的片段。这部中篇小说集是由四个故事组成的:《状元境》、《追月楼》、《十字铺》、《半边营》,这四个故事联合在一起,讲述了民国时期南京庶民生活的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用“鸳鸯蝴蝶派”的方式写作在南京生长的匹夫匹妇们,在南京的这些遗老遗少们,他们所经历过的悲欢岁月,他们所曾经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啼笑因缘。所以,《夜泊秦淮》是以诗意的方式所呈现的南京故事的一个高潮。讲到《夜泊秦淮》所谓的“秦淮”二字,当然就浮上了我们的心头,这条河成为南京一个重要的地标。1923年,有两个年轻的五四青年,一位叫俞平伯,一位叫朱自清,他们也来到了秦淮河畔,夜游秦淮。回家之后,两人各写了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两人的性情也由两人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而过了许多年之后,当叶兆言来写《夜泊秦淮》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五四”的那种所谓的豪情壮志,当年的人道主义精神全部都付之流水了。时间已到了80年代的末期了,在“文革”之后的十年,回首民国的时光,叶兆言的心事,其实是非常委婉、非常暧昧的,有一点点怀旧,有一点点一切都已过去了,又有一点点像是异国情调的南京,等等。所以,那种低回婉转的风格,我个人觉得也许在某一意义上,又衬托出南京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心事。这个城市,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在现代来到之前,在现代的这几十年里,南京所经过的风风雨雨,一切都让他过去吧,“夜泊秦淮”。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故事,叶兆言最后想写出来的这个“桃叶渡”,几乎有一点要超越的宗教情怀,来超越南京“秦淮”的这些作品到底没有写出来?也许因为没有写出来,才有了更多的小说、更多的故事。所以,这是我认为叶兆言在这个时间点上所带给我们的意义。
现在,到了今天报告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我希望今天的演讲是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式来结束,而不是在怀旧的过程中来结束。所以,我最后要表扬一下我们的年轻作家,一位是朱文,一位是韩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在1980年代当先锋主义在中国文坛风起云涌的时候,这两位作家仍然处于年轻的、蓄势待发的阶段,所以我们谈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时,韩东和朱文可能并没有什么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在90年代,却居然有几位以南京作为据点的作家,以他们特立独行的风格、以敢于与时代说不的精神,来展现出他们自己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信念,而这个信念的一个高潮就是1998年所谓“断裂”的文学事件。这个事件,坦白地讲,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事件。在这一年五月,朱文和韩东他们拟定了一份问卷调查表,向当时五十位所谓年轻的文化人来探问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界的各种机制的一种评判、对于中国当前的那些文化风潮的回想,
当然语气是激烈的,结论是质疑的。他们希望和这个时代作出一种了断,我觉得到了1998年的时候,不是上海的作家,不是北京的作家,不是中国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的作家,而是南京的两位作家有这样一种勇气站出来说断裂,我想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的结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轰动,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断裂,或者事件之后,这些作家不得不和现实的各种社会政治机制有所妥协。可是在世纪末的前一刻,这两个人所做出来的反叛的姿态,再次让我们想到南京除了在《夜泊秦淮》那种幽微的心事里面有所表露之外,南京的作家也可能有他们另外一种非常强烈的意志、一种时新的先锋斗志,来和这个时代继续作出角力。一直到今天,不论是朱文,还是韩东,再次说明了在南京的文坛里有一种深藏不露的底气。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底气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城市所烘托出来的文化命脉是仍然在持续的。
我在刚才用了十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来说明我自己对于文学里的现代的南京的历史的形形色色的看法。我的看法当然是不周延的,我所谓的关键时刻当然是一种武断的选择,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希望用关键这个词能够再一次打开,而不是锁定对于历史、文化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在这里我不必讳言,在这样一个看待文学史的方法上,当然有我个人和目前中国国内文学史的一个对话的动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史,基本上是大叙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种方法,反其道而行,它拒绝了一以贯之的大叙事的方式。它企图以一种零散的观点来作为进入历史的一个门路。但一旦你选择了你的观点的时候,你又把这些似乎是零散的观点作为你看待历史的一个辐辏点,每一个关键时刻可能的意义上都会开放出更多的连锁的关系。在这样的意义下,每一个时间的关键点都可以延伸出去,作出很多不同的对于南京文学、历史的进一步的思考。尽管我没有提到很多我们熟知的一些南京的事件或文学的成就,但是每一个点似乎在隐隐地昭示着我们,只要我们继续从每一个点追踪下去,这个点所辐射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脉络,仍然会给我们更多对于南京的体验。这种做法,在中国的传统里也有它的渊源,所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可能是有很多层面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打开了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让各种各样的思维、各种各样的历史脉络,再一次活跃在我们的眼前。我希望也许经过这样的一个演讲,来和各位有一个新的对话的可能,也希望在关键之后,我们看到的有可能是延续,有可能是断裂,但不论如何,这种关键时刻所代表的一种石破天惊的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在此时此刻在南京大学一百一十周年前后的时光再一次想象这所大学和这所城市所曾经负担的一些历史意义和它未来所不断开创的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