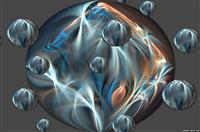小引
吃惯了北京的豆浆油条,何不尝尝广州的早茶点心?这里不涉及生死攸关的“立场”、“观点”,也不属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只是换一种口味而已。选择“纪事”的体式来浏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不是归纳总结出十大(或十二大)特征,除了换口味以及适应报纸篇幅要求,更缘于对世纪末读者(专家)“居高临下”的阅读姿态的深刻怀疑。与其给出若干众所周知而又似是而非的“经验教训”,不如引导读者回到现场,亲手触摸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
至于以年系事,只是为了便于记忆与叙说,并无微言大义。
摆脱了制造“定论”的巨大诱惑,不等于就可以随口“戏说”。依旧是专家的立场,只不过透过万花筒,眼前的风景开始晃动起来,在一系列的跳跃、冲撞与融合中实现重构。如此“百年回眸”,少了些严谨与浑厚,却希望能多几分从容、洒脱甚至幽默。在搬弄众多陈芝麻烂谷子时,叙述多而评说少,既是天地狭小的缘故,也不无制造悬念以便勾起读者阅读兴趣的意思。
作为史家,能否如此腾挪趋避,以及如此立说是否属于“推卸责任”,只好见仁见智了。
1902年,“新小说”的崛起
二十世纪初年,一场号称“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以“改良群治”为主旨,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为旗帜,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契机,“新小说”迅速崛起。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为“新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此后,刊载和出版“新小说”的刊物和书局不断涌现,“新小说”于是风起云涌,蔚为奇观。这一代作家(甚至包括李伯元、吴趼人等)没有留下特别值得夸耀的艺术珍品,其主要贡献是继往开来、衔接古今。正是他们的点滴改良,正是他们前瞻后顾的探索,正是他们的徘徊歧路以至失足落水,真正体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与艰难。
1909年,文人结社之转型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陈去病等在苏州虎丘举行第一次雅集,正式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南社。南社前后维持二十七年,最为辉煌的表现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南社社友追慕“几复风流”,辑校抗清志士的著作,刊刻古色古香的《南社丛刻》,以及选择春秋佳日雅集,但仍非“明末遗老”的复活。南社文人的投笔从戎,以及同盟会员的横槊赋诗,使得清末民初的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紧紧勾连在一起。不同于五四以后纯粹的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南社更多一份政治激情,以及直接介入实际政治运动的能力,比较接近的,其实是与之异代同调的左联。这就难怪鲁迅一反其时流行的将南社与鸳鸯蝴蝶派捆绑在一起讨伐的思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提醒大家注意“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的南社文人。
1917年,报刊与学校携手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正式就任校长;九天后,教育部根据蔡校长的呈请,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社因而由上海迁北京,与北大诸同仁精诚合作,共同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与利润,更不屑于直接地讨好读者与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也都属于同仁刊物,《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思想动力及学术资源。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虽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很难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以及《新青年》之进入北京大学,乃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1921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竞争
五四时期两大文学社团同年成立,自然形成紧张的对峙与激烈的竞争;令今人大感兴趣之处,在于二者到底是齐头并进,还是互相拆台?1月,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 叶圣陶等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文学研究会;文研会因其相对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为人生而艺术”一派。6 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在东京成立力主“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作为挑战者,加上强调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创造社在与文研会的争论中,时有过激的言辞,但总的来说,无伤大雅。值得庆幸的是,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一方有借助政治、军事力量来解决文学纷争的企图。五四时期社团林立,影响较大的,除了文研会和创造社,还有新月社、语丝社、浅草一沉钟社、湖畔诗社等。众多文学及文化观点大相径庭的社团,均以自我发挥为主;即便发生论战,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如此百家争鸣、互相砥砺的局面,至今仍令人怀念不已。
1923年,周氏兄弟的意义
周氏兄弟的离合,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无论是五四前后的配合默契,还是三十年代的情若参商,鲁迅、周作人的一举一动,牵连着整个文坛。以至研究者之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往往以周氏兄弟作为导引和坐标。兄弟俩的性格志趣、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之异同,早就是学界谈论的最佳话题。鲁迅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巨大贡献,绝非乃弟之停留在“纸上谈兵”所能比拟;反过来,周作人文化视野之广阔以及生活趣味之精妙,也自有值得夸耀之处。还是各自均为擅长、且被时人目为“双峰并峙”的文章,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周氏兄弟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散文最主要的两种体式“杂感”与“小品”的代表,除了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与二人寻找的“内应”不同有关。鲁迅之追踪魏晋,以及周作人的心仪六朝,对其或追求“思想新颖”、“长于说理”,辛辣简练得能以寸铁杀人,或欣赏“通达人情物理”,希望“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均起了重要作用。至于为何将晚清便已登上文坛的周氏兄弟放在1923年论述,其一,这一年的8月, 鲁迅出版了小说集《呐喊》,9月,周作人的随笔集《自己的园地》问世,哥俩的文学风貌及基本成就已经奠定;其二,第二年起兄弟失和,从此分道扬镳,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谜团与遗憾。
1926年,旧派小说的新变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大获成功,靠的是国民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辛亥革命后,阐发“政界之大势”与表彰“爱国之思”,不再成为小说的主要功能。“回雅向俗”的新小说家,为了满足已经变化的市场需求,转而追求娱乐性和趣味性。这一游戏文章、媚俗心态以及金钱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扫荡的主要目标。经过一番自我选择和调整,由“小说界革命”发轫而来的“新小说”,演变成为以章回小说为外部特征(夹入不少西洋小说表现手法)、以适应市场要求为主旨的“通俗小说”潮流,与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严肃小说”形成雅俗并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促使作家和读者进一步分化,有利于各自特长的发挥和各自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完善,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基本面貌和运动轨迹影响甚大。而本年度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春明外史》的出版,代表着民国旧派小说已经从最初的致命打击中恢复回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28年,新诗的自我调整
谈论中国新诗的成长,一般习惯于从胡适的《尝试集》(1920)和郭沫若的《女神》(1921)入手。之所以将话题推后几年,乃是有感于学界对早期白话诗的评价过于热情奔放,颇有将“文学史意义”与“文学价值”混为一谈的偏向。胡适的“清楚明白”,郭沫若的“激情燃烧”,在我看来,并非新诗的最佳状态。经历过最初的精神亢奋与狂飙突进,诗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新诗的出路。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诗人反省早期白话诗的过分理性化,重提“诗的本质专在抒情”;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则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批评此前诗坛的感伤与滥情,并开始“新诗格律化”的尝试;再加上王独清之突出“感觉”,穆木天之主张“纯诗”,以及象征派诗人李金发、戴望舒的浮出海面,种种迹象表明,二十年代末,新诗开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感觉”。至于为什么选择1928年,而不是同样有重要诗集出版的1927年或1929年?老实说,没有充足理由,只是执其两端取其中,这三年确实是中国新诗转变的紧要关头。
1930年,左联的话题
对于左联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1929年底开始筹备并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只直接影响了三十年代的一系列文学论争,并促成了文学创作的新潮流与新趋势。其精神遗产,起码笼罩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坛。而且,很长时间里,左联的意义及其阐发,影响到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建设。所谓三十年代文坛形成“左翼”、“京派”、“海派”三足鼎立之势,似乎所见者小。左联的活动横跨政治、文化、社会、文学诸领域,其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以及对自由主义文艺观展开激烈的批评等,都是在大转折时代谋求重建中国文化的努力。考虑到左联诸君是在国民党政治高压之下,以理想主义情怀从事艰险的探索,其功绩固然值得表彰,其缺失与遗憾,也“应具了解之同情”。
1932年,小品文的生机与危机
1932年9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闲适、 性灵与幽默,由此引发了“小品文热”。左翼作家对此很不以为然,另办《太白》、《芒种》与之对抗。鲁迅更发表《小品文的危机》,反对将小品文做成“小摆设”。三十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可以看作“散文”的重新自我定位。一主“闲适”与“性灵”,一讲“挣扎”与“战斗”,表面上水火不相容。可论争的结果,双方互有妥协:即所谓“寄沉痛于悠闲”、所谓战斗之前的“愉快和休息”。就对“宇宙”与“苍蝇”的把握方式而言,杂感与小品始终无法协调;但强调自我,张扬“个人的笔调”,鄙视“赋得”的文章,以及文体上“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又都是对于正统文章“载道”功能的消解。很不一样而又可以互相补充,这其实正是现代散文发达的奥秘。
1933年,走向成熟的中、长篇小说
经由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人的努力,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在二十年代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至于中、长篇小说的成熟,则是三十年代的故事。就在1933年,几部极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几乎同时面世,给时人、也给后世的文学史家一个意外的惊喜。1月, 开明书店出版茅盾的《子夜》;5月, 开明书店又推出巴金的《激流》(即《家》);8月,良友图书公司发行老舍的《离婚》。这三部长篇小说题材、 风格迥异,但都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时至今日,仍被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沈从文呢?稍为慢了半拍,本年度出版的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均非上乘之作,但很快地,沈便迎头赶上。第二年10月,生活书店出版了《边城》一书,证明了沈与上述三位一样,完全有资格跻身本世纪中国最好的小说家行列。
1935年,话剧的“日出”与“回春”
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样式,话剧的发展道路显得格外崎岖。从世纪初的“文明戏”,到二十年代的“爱美剧”和“小剧场运动”,
再到三十年代的“职业剧团的建立,长期公演话剧的固定剧场的出现”,借用茅盾的话,此乃中国话剧“从幼稚期进入成熟期的标志”。话剧能否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获得广大的受众,取决于话剧运动、舞台演出与剧本创作三者之间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程度。在很长时间里,缺乏优秀剧本成了制约中国话剧发展的巨大障碍。正如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所说,话剧家的努力,必须是在其剧本创作不仅可供舞台演出,而且“也可供人们当作小说诗歌一样捧在书房里诵读,而后戏剧在文学上的地位,才算是固定建立了”。1935年春天,年仅二十五岁的曹禺继《雷雨》之后,创作了更具独创性的《日出》;而长期从事戏剧运动的田汉,也在这一年的5月出版了其代表作之一《回春之曲》。 与此同时,原先主要从事电影工作的夏衍,完成了第一部多幕剧《赛金花》的写作。
1941年,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
本世纪的中国小说界,女作家的迅速崛起,绝对是个标志性事件。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歌赋乃至弹词文章,均有历代才女驰骋笔墨。惟独日渐辉煌的小说界,基本上未见女作家的倩影。这一令人尴尬的局面,本世纪初方才有所改变。五四文学革命尚未谢幕,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等已经跃上文坛,初步展现女性从事小说创作的巨大潜能。进入四十年代,对于女小说家的创作,批评家们逐渐从不敢漠视,转为大力推崇,尤其对基于独特的人生体验、女性敏感以及鲜明的文体意识所营造的《呼兰河传》(萧红,1941)、 《 在医院中》(丁玲,1941)和《倾城之恋》(张爱玲,1943)等,更是拍案叫绝。
1942年,校园诗人引领风骚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艾青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页。从1936年《大堰河》集印行,到1939年自费出版第二本诗集《北方》,再到1941年《诗论》出版,艾青已经完成了其作为大诗人的三步跳。这里想说的是,就在艾青完成诗学大厦基本框架的第二年,冯至的《十四行集》和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分别由桂林明日社印行。除了这两部诗集的经典意义外,我更看重这两位诗坛前辈与新月派领袖闻一多,以及诗评家朱自清、李广田等的通力合作,在炮火连天的大西南,为年轻一代营造出充满灵气与悟性的精神家园。西南联大热情而敏感的青年学生(如穆旦等),追随前来任教的现代派诗人兼理论家威廉•燕卜逊深入艾略特、里尔克等人的世界,并因此促成了“思”与“诗”的真正融合。在这期间,冯至等师长的积极探索,既是示范,也是无言的鼓励。
1945年,《讲话》的巨大回响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四十年代延安整风的产物,正式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此后,无论在解放区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讲话》均是中共中央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在本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坛上,《讲话》所发生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其初露端倪,则不妨以本年度两部剧作的不同命运为例。属于民间口头创作的“白毛仙姑”传说,被赋予“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全新主题,再加上融合西洋歌剧与民间戏曲,使得革命意识形态与民间审美趣味获得某种统一,因而得到政治家与老百姓的共同赞许。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只是体现了艺术创新的一种可能性(姑且不论其留下的巨大遗憾),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可惜的是,论者往往将其作为标准来裁断其他作品。同年出版的《芳草天涯》则没有这么幸运。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再到《芳草天涯》,作为革命作家的夏衍,努力摆脱日渐僵化的文学模式,从单纯关注时代与政治,转而注重道德与伦理,力图更好地展现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苦恼与挣扎。这一大有潜力的艺术探索,在《新华日报》组织的座谈会上,因其“非政治倾向”而受到严厉批评。曾经写过不少优美的散文诗、后成为重要的文艺理论家的何其芳,更专门撰文教育夏衍等“已经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问题是认识自己的思想还需要经过一番改造”。至于作为剧情主线的恋爱纠纷,在何先生看来,“究竟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问题”,不值得大做文章。
1999年9月1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