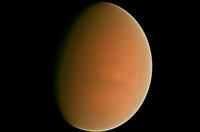陆游的《入蜀记》是宋代著名的一部笔记,后人对它的重视主要集中于其史地考订方面的成就,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评价它说:“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非他家行记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的确,《入蜀记》在考订历史、地理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除了《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的十五六则以外,还有不少颇有学术考订性质的段落,堪称精确(注:陆游的考订也偶有错误,例如《入蜀记》卷六“十月八日”条记游三游洞事,云:“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黄庭坚弟叔向、子相、侄檠,同道人唐履来游,观辛亥旧题,如梦中事也。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庚寅。’按鲁直初谪黔南,以绍圣二年过此,岁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误也。”其实“辛亥”二字无误,黄庭坚在《黔南道中行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中说得很清楚:“绍圣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关……至三游洞。”所谓“辛亥旧题”的“辛亥”是纪日而非纪年,实指绍圣二年二月十六日。陆游误把纪日的“辛亥”当作纪年了。)。然而我认为《入蜀记》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也许比其史地考订更为重要,它正是以这两方面的成就而跻身于宋代笔记佳作之林的。
一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底,四十五岁的陆游接到朝报,以左奉议郎为通判夔州军州事。由于陆游其时正在山阴养病,故而没有立即赴任。次年闰五月,他才启程前往夔州。此次入蜀之旅始于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终于是年十月二十七日。他在此次旅途中除了写作诗歌以外,还按日作记(注:《入蜀记》按日作记,即使其日无事可纪,也仍纪其日,如乾道五年闰五月的二十七日、三十日等。),成《入蜀记》六卷。对于这部游记性质的笔记,陆游本人是相当看重的,曾叮嘱其子将《入蜀记》编入文集:“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注:见陆子遹《渭南文集跋》,《四部丛刊》本《渭南文集》卷首。按:本文所引《入蜀记》即据此本,卷数则自为起讫,以求简明。)果然,《入蜀记》不但成了陆游的散文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而且成了宋代笔记体散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后人非常重视陆游在巴蜀的生活经历对其诗歌成就的影响,却很少认识到巴蜀之游对陆游散文创作的巨大作用。陆游曾说:“古乐府有《东武吟》,鲍明远辈所作,皆名千载。盖其山川气俗,有以感发人意,故骚人墨客得以驰骋上下,与荆州、邯郸、巴东三峡之类,森然并传,至于今不泯也。”(注:《徐大用乐府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入蜀记》就是在自浙东至于巴东的数千里“山川气俗”的感发下写成的一部杰作,它与作者安坐在故乡书斋里所写的散文作品有着不同的艺术风貌。
作为游记作品,《入蜀记》首先关注的是沿途所见的山川风物。陆游此行的路线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先沿着运河从山阴到临安,再经嘉兴、苏州、常州,到镇江后进入长江。第二段路程全是在长江中行进的,沿途经过的重要地点有建康府(今南京)、太平州(今当涂)、芜湖、池州(今贵池)、江州(今九江)、黄州、鄂州(今武汉)、岳州(今岳阳)、江陵府(今沙市)、夷陵(今宜昌)、秭归、夔州等。由于第一段路程中的地点都是陆游曾多次经过的,其山川风景是他非常熟悉的,所以不很能引起他的写作兴趣。《入蜀记》中仅用不足一卷的篇幅来写第一段路程,当因此故。第二段路程却在陆游面前展开了一幅全新的江山画卷,除了镇江一带的江山算是故地重游以外,其余的地点都是首次经历。而且自镇江开始溯江而上,两岸的奇丽风光接连不断且变化无穷,镇江的金山、焦山可算是渐入佳境的起点。《入蜀记》中泼墨如水地进行大笔濡染的写景即始于镇江,多半是出于这个原因。
与一般仅注重写景的游记散文不同,《入蜀记》对沿途山川的描写是多角度的,举凡地貌特征、地理沿革、郡国利病、名胜古迹、地方物产等各个方面,都映入了作者的眼帘,而且娓娓道来,富于文学意味。试各举一例:
(十月)八日,五鼓尽,解船过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初冬,草木皆青苍不凋。西望重山如阙,江出其间,则所谓下牢溪也。(卷六)
七月一日,黎明,离瓜洲。便风挂帆,晚至真州,泊鉴远亭。州本唐扬州扬子县之白沙镇,杨溥有淮南,徐温自金陵来,觐溥于白沙,因改曰“迎銮镇”。或谓周世宗征淮南时诸将尝于此迎谒,非也。国朝乾德中升为建安军,祥符中……建军曰真州。(卷二)
(七月)七日……同登石头,西望宣化渡及历阳诸山,真形胜之地。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当头仍为关要。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贯城中。六朝立栅断航之类,缓急不可复施。然大江天险,都城临之,金汤之势,比六朝为胜,岂必依淮为固耶?(卷二)
(八月)五日,郡集于庾楼。楼正对庐山之双剑峰,北临大江,气象雄丽,自京口以西,登览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楼不甚高,而觉江山烟云,皆在几席间,真绝景也。(卷三)
(九月)十一日……又有水禽双浮江中,色白类鹅而大,楚人谓之天鹅。飞骞绝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即鹄也。(卷五)
第一则写船过下牢关后所见之景。下牢关位于夷陵之西,从此溯江西上,即是长江三峡的第一峡西陵峡。陆游从江汉平原行来,陡然看到那遮天蔽日的崇山峻岭,而长江即从山阙中奔泻而来,不免产生惊愕之感。此段文字虽然甚为简洁,但是在对千奇百怪的山峰形状之描写中透露出作者对自然伟力的赞叹膜拜之情,所谓“崩欲压者”、“危欲坠者”等等,都用拟人化的写法,正是对自然伟力的传神写照。在这种伟力面前,人的渺小无力是不言而喻的。故而这一则在字面上虽然仅有写景而无抒情,事实上作者的赞叹之情即渗透在写景之中,这正是古文高手的不凡表现。
第三则写作者在建康府登临石头城的情景,重点在于论述将建康作为抗金重镇乃至作为南宋首都的理由。在宋、金对峙的形势下,陆游一向反对建都于临安,而主张迁都建康乃至关中,因为那样退可以恃关山险阻以抵抗金兵,进可以号召中原,在时机适当时北上收复失土。隆兴元年(1163),陆游曾上书朝廷,建议迁都建康:“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而他都者。……何哉?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注:《上二府论都邑札子》,《渭南文集》卷三。)如今他来到建康其地,实地考察了建康的门户——石头城的形势,更加坚定了迁都建康的想法。他甚至想到了一旦战火燃烧到建康,宋军应如何防守的问题。这则文字既及地理,又是政论,言之有物,正气凛然,是掷地有声的好文章。
其它三则对所经地方的地理沿革、名胜古迹和特殊物产作了生动的描写,也都富于文学意味。
当然,就文学性而言,《入蜀记》最值得注重的是它的写景。虽然作者并未着意把本书写成纯粹的山水游记,但是全书中优美的写景片断在在皆是,这些片断常常只是寥寥数语,却画龙点睛式地展现了长江沿岸的壮丽风光。例如:“(七月)十四日,晚晴。开南窗观溪山。溪中绝多鱼,时裂水面跃出,斜日映之,有如银刀。”(卷二)“(七月)十六日……城壕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昼,影入溪中,摇荡如玉塔。始知东坡‘玉塔卧微澜’之句为妙也。”(卷二)“(七月)二十二日,过大江,入丁家洲夹,复行大江。自离当涂,风日清美,波平如席。白云青嶂,远相映带。终日如行图画,殊忘道途之劳也。”(卷三)至于那些篇幅较长的片断,则俨然就是一篇完整的游记佳作,例如:
八月一日,过烽火矶。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当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抛江过其下,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亦与它石迥异。又有一石,不附山,杰然特起,高百余尺。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装屏风。是日风静,舟行颇迟。又深秋潦缩,故得尽见杜老所谓“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也。过澎浪矾、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小孤属舒州宿松县,有戍兵。凡江中独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类,皆名天下。然峭拔秀丽,皆不可与小孤比。自数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已非它山可拟。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态万变,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极于荒残,若稍饰以楼观亭榭,与江山相发挥,自当高出金山之上矣。(卷三)
这一则写从船上眺望江上孤峰的情景。在长江接近鄱阳湖口的江面上,有好几座孤岛,其中以小孤、大孤最为著名。此则写小孤及烽火矶、澎浪矶以及无名的一块独石。这些江上孤峰都是陡然耸起于江面上的,其共同特点是独立孤耸,但是陆游对它们的这个共性的描写却绝不雷同,烽火矶是“突兀”,无名独石是“杰然特起”,小孤山是“巉然孤起”,文字也与所写对象同样的变化多姿。此外,烽火矶的特点是石色晶莹并多洞穴,无名独石的特点是藤蔓萦络,而小孤山的特点则是高耸入云,真可谓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如此简练的一段文字,却把几座山峰写得各具面目,各显精神,即使独立成篇,也是一篇精妙的山水游记。而这样的段落在《入蜀记》中至少有二三十段,可见陆游在写景方面的高超手段。可以说,即使《入蜀记》的文学成就仅仅体现于写景,它也足以与唐宋古文名家的同类作品媲美。然而事实上《人蜀记》的文学成就绝不仅止于写景,其中对历史的思考、对民生的描摹等部分同样具有深永的文学意味。
二
从运河到长江,陆游入蜀所经历的都是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地方。多少英雄人物曾在那里叱咤风云,多少骚人墨客曾在那里挥毫泼墨。尽管风吹雨打,浪淘沙沉,但是历史文化的印痕早已与江山风月融为一体,使自然的美景蒙上了浓郁的人文色彩。陆游精于史学,对前代的史实了然于心。当他亲临曾经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点或目睹前代英杰的遗迹时,当然会情不自禁地发思古之幽情。他在路经武昌时作诗云:“西游处处堪流涕,抚枕悲歌兴未穷。”(注:《武昌感事》,《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引发这种激情的当然不是江山风月而是历史遗迹,于是《入蜀记》中涉及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入蜀记》中涉及历史而又富于文学意味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类:缅怀历史人物、评说历史事件、考证历史事实。现各举一例:
(八月)十九日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筇杖,是为雪堂。堂东大柳,传以为公手植。正南有桥,榜曰“小桥”,以“莫忘小桥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无渠涧,遇雨则有涓流耳。旧止片石布其上,近辄增广为木桥,覆以一屋,颇败人意。东一井曰“暗井”,取苏公诗中“走报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齿,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亭名见苏公及张文潜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号南坡,今已残伐无几,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国寺,亦苏公所尝寓。兵火之余,无复遗迹。惟绕寺茂林啼鸟,似犹有当时气象也。(卷三)
(七月)十一日……采石一名牛渚,与和州对岸,江面比瓜洲为狭,故隋韩擒虎平陈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风辄浪作,不可行。刘宾客云:“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王文公云:“一风微吹万舟阻。”皆谓此矶也。矶即南唐樊若冰献策作浮梁渡王师处。初,若冰不得志于李氏,诈祝发为僧,庐于采石。凿石为窍,及建石浮图。又月夜系绳于浮图,棹小舟急渡引绳至江北,以度江面。既习知不谬,即亡走京师上书。其后王师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炀帝征辽,盖尝用此策渡辽水……然隋终不能平高丽,国朝遂下南唐者,实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献南征之策……然若冰所凿石窍及石浮图皆不毁,王师卒用以系浮梁。则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卷二)
(八月)五日,
郡集于庾楼。楼正对庐山之双剑峰,北临大江,气象雄丽。自京口以西,登览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楼不甚高,而觉江山烟云皆在几席间,真绝景也。庾亮尝为江、荆、豫州刺史,其实则治武昌。若武昌南楼名庾楼,犹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晋特柴桑县之湓口关耳,此楼附会甚明。然白乐天诗固已云“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则承误亦已久矣。张芸叟《南迁录》云:“庾亮镇浔阳,经始此楼。”其误尤甚。(卷三)
对于苏轼,陆游一向怀有最高的敬意,这不仅仅是由于苏轼的杰出文学成就,也是由于苏轼崇高的人格精神。陆游曾称誉苏轼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注:《跋东坡帖》,《渭南文集》卷二九。)他在入蜀途中对苏轼的流风遗韵极为留意,仅在《入蜀记》中提及苏轼的就有十二处之多,上引第一则就是其中之一。黄州是苏轼的贬谪之地,也是苏轼的文学事业首次大放异彩的地方,他的别号“东坡居士”就得名于黄州的一处地名。而今陆游亲临当年苏轼啸傲风月的地方,怎能不思潮澎湃呢?“东坡”、“雪堂”,自是当年苏轼的经行憩息之地。连“小桥”、“暗井”这种极为常见的地名,竟然也是得名于苏轼的名章迥句。陆游每到一处,即将所记诵的苏轼名句与眼前景象对照勘察,仿佛是随在苏轼的杖履之后一路经行,难怪他要感慨万千,流连忘返了。整段文字中充溢着对昔贤的景仰之情和对时代变迁的沧桑之感,读来娓娓动人。
第二则是对南唐史事的感叹、议论。陆游是南唐史专家,对南唐一朝的史事了然于心。当他来到采石矶,目睹了当年樊若冰暗测江面留下的遗迹,不免要对这件与南唐亡国直接有关的事件评论一番。陆游是宋臣,对本朝平定南唐当然是拥护的。然而他对樊若冰因个人不得意遂卖国投敌的行为却不以为然,故再三强调宋朝灭南唐事出天意,不是樊若冰个人的举动所能决定的。不但如此,他还在此节之末引北宋张耒《平江南议》的意见,认为宋朝对樊若冰应该“正其叛主之罪而诛之”,并评论说:“文潜此说,实天下之正论也。”南宋虽是南唐的敌国北宋之沿续,但在面临来自北方强敌的威胁而将长江视作边防要地的形势上却与南唐非常相像。在陆游所处的年代里,尤其需要号召国人忠君爱国、抵御侵侮的精神,所以陆游对樊若冰那种投敌求荣的行为持批判态度,不足为奇。此外,陆游对南唐君臣文恬武嬉终致亡国的史实也深为慨叹,如果联系南宋小朝廷的黑暗现状,“暗且怠”三字难道不正是实有所指的微言大义!在指点江山之中评说历史,正是此段文字在内容上的特点。
第三则对江州“庾楼”的景观作了描绘,并考辨此楼不应以晋人庾亮命名。陆游指出庾亮当年任江、荆、豫州刺史,其治所是在武昌,所以只有武昌的南楼才能称为“庾楼”(注:《世说新语·容止》载有庾亮在武昌时,曾于秋夜登南楼与诸贤咏谑之事。陆游所云当即据此。),而前人白居易、张芸叟等人的诗文将江州之楼称作“庾楼”都是出于误传。陆游在此处充分发挥了他长于史地考订的长处,先指出庾亮作镇之地不在江州,再说明眼下的江州治所在晋时仅是一个小镇,此处的一座楼当然与庾亮没有什么关系。此类以考订见长的文字在《入蜀记》中相当常见,这是这部笔记受到后人重视的原因之一。而我在本文中对此予以重视,则是由于它们思路灵动多姿,文笔清丽可诵,绝不同于枯燥烦琐的纯考证文字,故而具有较浓的文学意味。
《入蜀记》中更引人入胜的是那些融写景、论史与抒情于一炉的段落,有些片断简直就是一篇独立的小品佳作,试举一例:
(十月)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门关,仅通一人行,天下至险也。晚泊巴东县,江山雄丽,大胜秭归。但井邑萧条,邑中才百余户。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无片瓦。……谒寇莱公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飂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遂登双柏堂、白云亭。堂下旧有莱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复,秀丽可爱。白云亭则天下幽奇绝境,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栏外双瀑泻石涧中,跳珠溅玉,冷入人骨。其下是为慈溪,奔流与江会。予自吴入楚,行五千余里,过十五州,亭榭之胜,无如白云者,而止在县廨厅事之后。巴东了无一事,为令者可以寝饭于亭中,其乐无涯。而阙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何哉?(卷六)
作者在萧瑟秋风中登上“秋风亭”,缅怀当年名臣寇准贬谪至此的事迹,遂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又想到江山如此秀美,却因地僻人贫,竟然无人愿意来此作令,更是慨叹不已。应该说,前后两种慨叹本是有矛盾的,可是由于作者是触景生情,兴之所至,笔亦随之,所以反而显得真切动人。寇准本是陆游景仰的前贤(注:陆游在《秋风亭拜寇莱公遗像》之二中说:“豪杰何心后世名,材高遇事即峥嵘。巴东诗句澶州策,信手拈来尽可惊。”(《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他当年被谮远谪而流落至此。如今陆游离乡万里来到此地,又适逢“重阴微雪”的萧条天气,怎能不生天涯流落之感?可是巴东的江山之美毕竟唤起了陆游的极大好感,想到这里地僻政简,作令者正可优游逍遥,便又对“阙令”之事表示不解。前者是一个离乡万里游宦至此的陆游的真情实感,后者则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且热爱山水的陆游的真情实感,两者通过穿插在文中的景色描写和谐地融合起来了。这正是《入蜀记》这种特殊文体所独有的优点:它只是逐日记事的笔记,而不是精心谋篇的独立篇章,故而自由挥洒,随意行止,读来分外觉得亲切。
三
如果只有上述两类内容的话,《入蜀记》也许与其它宋代笔记的题材没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事实上它还有相当丰富的其它内容,体现了陆游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那就是作者对普通的人民也很关心,对沿途的风土、民俗乃至生产、生活情形都觉得趣味盎然,与此有关的片断是《入蜀记》中最富有生活气息的部分。
首先,《入蜀记》中有一些为普通人所画的人物素描,例如:
(毛)德昭极苦学,中年不幸病盲,而卒无子。……其盲后犹终日危坐,默诵六经至数千言不已,可哀也。(卷一,六月六日)
庙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完颜亮寇边时,自河朔从义军,攻下大名,以待王师。既归朝,不见录。且自言孤远无路自通,歔欷不已。(卷一,六月二十五日)
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应募为船之招头。招头者,盖三老之长,顾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众人。既而船户赵清改用所善程小八为招头,百一失职怏怏,又不决去,遂发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余,三没三踊,仅得出。(卷五,九月二十八日)
第一则写终身潦倒而苦学不已的读书人,第二则写曾抗金立功但没有得到任何封赏的战士,他们都是默默无名的失意之人,陆游对这两类人物都很看重,故笔下充满着感情,自不必多言。第三则写一个性格急躁的船工,失去“招头”(即水手长)的职务后,竟至投江自尽。寥寥几笔,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栩栩如生。此类内容,也许是那些自视高雅的文人墨客所不屑措意的,可是它们被写得何等生动有趣!
其次,《入蜀记》中对沿途所见的风土民俗的叙写相当常见,随意点缀,涉笔成趣。例如下面这种比较罕见的生产情景:
抛大江,遇一木筏,广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所未睹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复能入夹,但行大江而已。(卷四,八月十四日)
妇人汲水,皆背负一全木盎,长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峡中负物率着背,又多妇人,不独水也。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卷六、十月十三日)
运河水泛溢,高于近村地至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妇人、儿童竭作,亦或用牛。妇人足踏水车,手犹绩麻不置。(卷一,六月八日)
第一则写飘浮在江中的大筏,居然有数十户居民居住在筏上随波逐流。这当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的无可奈何之举!二、三两则写劳动妇女的生活情景,前者展现了一幅三峡沿岸的劳动妇女的画卷,她们背负重物之情状以及其发髻装饰皆历历如画;后者写运河边的妇女同时进行两种劳作,其辛苦劳顿不言自明。
其三,《入蜀记》中也记载了其它有趣的生活插曲,例如下面两则:
(六月)二十五日,早以一稀、壶酒谒英灵助顺王祠,所谓下元水府也。祠属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无他祝史。然榜云:“赛祭猪头,例归本庙。”观者无不笑。(卷一)
(六月)二十六日,五鼓发船,是日始伐鼓,遂游金山。……山绝顶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胜。每北使来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与焦山相望,皆名蓝,每争雄长。焦山旧有吸江亭,最为佳处,故此名“吞海”以胜之,可笑也。(卷一)
金山寺与焦山寺是镇江的两处名刹,也是该地的两处名胜。寺庙僧人本应六根清净,与世无争,然而金山寺的僧人却不但垄断了水神庙的祭神猪头,而且出榜公示。佛门净地居然收进去许多猪头,难怪观者要大笑了。该寺的僧人还为了与焦山寺争胜,为亭子取名“吞海亭”来压倒后者的“吸江亭”,这哪里像是遁入空门中人的作为!陆游并不反对佛教,他此次路经金、焦二寺时还曾与焦山长老定圜、金山长老宝印相晤,只是当他看到僧人们的世情俗态时,便不免忍俊不禁了。这种生活气息浓厚的小插曲,使《入蜀记》宛如一幅千里长江的风俗画卷,读来饶有趣味。
四
《入蜀记》从两个方面记载了作者的旅行状况,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旅行笔记。现分述如下:
首先,《入蜀记》记载了作者奉朝廷之命赶赴任所的经过,为后代读者提供了关于宋代官差旅行的丰富资料。
一、赶赴远处任所不必日夜兼程,赴官者可以从容为之。陆游从乾道五年(1169)年底接到任命,迟至次年闰五月才动身赴任。如果说这是因病而迁延,那么他已经上路之后仍然“行道迟迟”,走了五个多月方到达夔州,就只能说他并未把王命看得急如星火了。《入蜀记》中对陆游一路上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他不但沿途访亲问友,而且每逢名胜古迹,都要停留数日,以尽观览之兴。例如他在闰五月十八日动身以后,至二十日已达临安,在临安逗留十日,省兄访友,游览西湖,至六月一日才离开。又如他于六月十七日抵镇江,又停留十日,到二十八日才渡江至瓜洲。其后他行经建康府、庐山、鄂州等地,也都停留五日以上。难怪他在此行途中不但写了《入蜀记》六卷,而且作诗九十多首,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二、远行赴官者的盘缠必须自筹,但是政府也提供一定的旅行便利。陆游入蜀,就是靠亲友的资助才凑足了路费(注:陆游到达夔州任所后在《上虞丞相书》中说:“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渭南文集》卷一三))。但是当他上路之后,一路上也曾得到官府的照应。八月三日,陆游行至江州,“始得夔州公移”(卷三),也就是说夔州官府已有文书前来。至二十三日,陆游行至鄂州,“夔州迓兵来参”(卷四),即夔州方面已派士兵来迎接。九月十日,陆游行至石首县附近,“遣人先至夔”(卷五),所遣之人当即夔州派来迎接的士兵。九月二十一日,陆游在江陵府,“刘帅丁内艰,分迓兵之半,负肩舆自山路先归夔州”(卷五)。可证夔州派来的“迓兵”人数不少(注:“刘帅”是谁,为何要陆游派兵送之,《入蜀记》中没有明确记载,待考。)。从这些记载可见南宋时官府对地方官的赴任之行是有所安排照应的。而陆游在路经所有的州府时都得到当地长官的宴请接待(《入蜀记》中记载甚多,文繁不录),那些官员并非都是他的旧交,可见地方官府本有接待过路官员的责任。
其次,《入蜀记》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乘舟旅行的过程,为后代读者提供了关于宋代长江航运的丰富资料。
一、陆游此行除了在临安时曾一度搭乘官船以外(注:《入蜀记》卷一:闰五月二十日,“登漕司所假舟于红亭税务之西。”),一路上都是租船而行。《入蜀记》中的租船记载始于镇江,那正好是长江航行的始点:“(闰五月)二十日,迁入嘉州王知义船。”(卷一)至二十九日又记云:“舟人以帆弊,往姑苏买帆,是日方至。”(卷一)可见船主为了在长江上的长途航行,事先须作好充分的准备。这条船是一条载重量很大的“二千斛舟”(见卷三“七月二十八日”),一路平安无事。然而经过公安县后,陆游终于换了一条船:(九月)十七日,“日入后迁行李过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卷五)原来过三峡必须换乘专门的“入峡船”。《入蜀记》中还具体记述了这种船的特征:“(九月)二十日,倒樯竿,立橹床。盖上峡惟用橹及百丈,不复张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橹六枝、百丈两车。”(卷五)可惜这条“入峡船”并没有把陆游一行安全地送到夔州,“(十月)十三日,舟上新滩,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为石所损。急遣人往拯之,仅不至沉。然锐石穿船底,牢不可动。盖舟人载陶器多所致。”(卷六)“十五日,舟人尽出所载,始能挽舟过滩,然须修治。遂易舟,离新滩,过白狗峡。”(卷六)原来由于船主贪利多载货物,导致船底被礁石刺穿,陆游只得又一次换船,才过了新滩和白狗峡到达归州。陆游自镇江至夔州,竟三易其舟,才得到达,可见那时从水路入蜀是何等的艰险!
二、更为可贵的是,《入蜀记》中还详细描写了在长江上行舟的经过,包括舟子如何与险滩湍流搏斗,以及祭神、避险及旅客搭乘等细节,生动有趣。
在长江上行舟,舟子辛苦异常。“(八月)十四日……是日逆风,挽船自平旦至日映,才行十五六里。”(卷四)“九月一日,始入沌,实江中小夹也。……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又无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才行四十五里。”(卷五)用纤挽船逆流而上,一整天才前进十多里,更何况遇到连纤路也没有的地方,竟需要用小船来拉纤,这是何等的辛苦!然而更大的麻烦是险滩急流的威胁,所以舟子常常要向神灵祈求平安:“(九月)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泽深阻,虎狼出没。未明而行,则挽卒多为所害。’是日早见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红头须小使头:长年三老,莫令错呼错唤!’”(卷五)至是月二十二日,“舟人祀峡神,屠一豨。”(卷五)至十月三日,“舟人杀猪十余口祭神,谓之开头。”(卷五)如此频繁地祭神,可见覆舟之险在舟子的心头投下的阴影有多么严重!
陆游也记载了舟子们的一些趣闻,例如下面两则:
(七月十一日)是日便风,击鼓挂帆而行。有两大舟东下者,阻风泊浦溆,见之大怒,顿足诟骂不已。舟人不答,但抚掌大笑,鸣鼓愈厉,作得意之状。(卷二)
(七月二十八日)至石壁下,忽昼晦,风势横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趋小港。竭力牵挽,仅能入港系缆。同泊者四五舟,皆来助牵。(卷三)
一写顺风行舟者与逆风行舟者的矛盾心态,一写舟子间的互相帮助,生动如画。此外如乘客搭船之事,在《入蜀记》中也有所记载:“(八月)二十九日早,有广汉僧世全、左绵僧了证来附从人舟。”(卷五)“(九月)十三日,泊柳子。夜过全、证二僧舟中,听诵梵语般若心经。”(卷五)可见陆游在镇江所租王知义之船共有两艘,其一是给从人乘坐的,二僧来搭乘的就是“从人舟”。凡此种种,为后代读者展现了当时长江航运的许多细节性的画面,如果有学者要研究宋代航运情况的话,《入蜀记》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绝佳史料。
五
读《入蜀记》时我还联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诗与文的关系。陆游是诗、文兼擅的文学家,在他入蜀途中,既写了《入蜀记》这部散文作品,也写下了六十四首诗歌(注:始于《将赴官夔府书怀》,毕于《登江楼》,皆见《剑南诗稿校注》卷二。)。那么,其诗与其文有什么异同呢?如果有所不同的话,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首先,不管是散文还是诗歌,当然都必须有感而发,必须言之有物,否则便成为无病呻吟之作了。但是诗与文的写作条件毕竟是有所差异的,后者可以比较客观地记述所经之事,或比较冷静地考证史地,不一定要有很强的感情因素,而诗歌的写作则非动情不可,这在陆游入蜀途中的写作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例如陆游在《入蜀记》中记载说:“(六月六日)宿枫桥寺前,唐人所谓‘半夜钟声到客船’者。”(卷一)这仅仅是对自己行止的客观记录,即使想到了唐人诗句,也仅止于此,并未有何感想。然而他在同时所作的《宿枫桥》一诗中却说:“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既对旧地重游表示了深沉的感慨,又对自己即将经历千山万水的巴蜀之行觉得心事重重。总之,此诗虽仅寥寥四句,但是字里行间却渗透着浓郁的情感。诗、文之别,判若泾渭。
正因如此,作者在《入蜀记》中的写法是排日作记,五个月中只留下很少空白的日子。可是其途中诗作却只有五十八题六十余首,在多数地点仅仅作记而未曾写诗,尽管陆游是以高产诗人而著称于世的。例如《入蜀记》卷六记载:“(十月)十六日,到归州。……城中无尺寸平土,滩声常如暴风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间,然地比归州差平。或云:楚始封于此。”楚王城本是一个绝妙的诗题,然而陆游此时并未作诗。《入蜀记》中的上述记载基本上是客观的描写,即使是势如暴风雨的滩声也并未在作者心头引起什么情感波动。八年以后,陆游出峡东归经过此地,作《楚城》一诗: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牢骚满腹,思绪万千,对历史的无限感慨中包蕴着对眼前国势和个人命运的深沉叹息,因为当年楚国的暗弱正是如今国势的写照,而当年屈原报国无路的悲剧如今又在自己身上重演。诗人对这些感触不着一字,只说时迁世移,只有江上的滩声亘古如斯。然而诗人心中的汹涌思绪不正如这滩声一样,会在读者心上引起暴风雨般的感觉吗?那么,如此激情澎湃的一首好诗,为什么在陆游入蜀时没有能写出来呢?当然诗歌的灵感会有一些偶然因素在内,不全可以解说,但是大致说来,我觉得这是由于诗人在八年前入蜀时对人生事业还充满着憧憬,对国势也存在着希望,所以江边那座荒芜的楚城还没有引起他太大的感叹。及至他出蜀东归,平生梦寐以求的从军机会已经消逝,对国势衰弱的局势也看得更为清晰。当他再次看到楚城及隔江的屈原祠时,便不由得诗思如潮了。而散文的写作与诗歌不同,陆游入蜀途经楚城时虽然心中并无太深的感触,但并不妨碍他客观地记述行踪、描摹风物。
其次,文学创作都允许虚构、想象,但相较而言,诗歌更需要想象的翅膀,而散文却不妨与想象暂时分手,甚至可以把实事求是当作写作的高境。陆游入蜀途中的诗文写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入蜀记》卷四:“(八月十九日)后至竹楼,规模甚陋,不知当王元之时亦止此耶?楼下稍东,即赤壁矶,亦茅冈尔,略无草木……此矶图经及传者皆以为周公瑾败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质。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败曹公。’不言在黄州。苏公尤疑之,赋云:‘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乐府云:‘故垒西边,人道是,当日周郎赤壁。’盖一字不轻下如此。至韩子苍云‘此地能令阿瞒走’,则真指为公瑾之赤壁矣。又黄人实谓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陆游指出长江边上以“赤壁”为名的山矶很多,黄州的赤壁一名“赤鼻”矶,故不一定是三国时周瑜大破曹操的古战场。文中虽说“不可考质”,但“尤可疑也”一语分明是否定的意思居多。可是陆游作于同时的诗歌《黄州》中却说:“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又说:“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则又分明把黄州的赤壁看作古战场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呢?原因即在于文征实而诗尚虚,当陆游写《入蜀记》时,他是以征史考实的态度来看待黄州之赤壁的,当然要实事求是。可是当他作诗时,只是借怀古以抒写胸中的感慨,既是借酒浇愁,当然无需细究史实,否则便是胶柱鼓瑟了。
当然,诗与文的界限不是绝对不可超越的雷池,它们有时也会互相渗透,甚至造成一些交叉地带,《入蜀记》中就有不少诗情浓郁的片断,除了前文所引的例子以外,再引数例:
(八月十六日)晚过道士矶,石壁数百尺,色正青,了无窍穴,而竹树进根,交络其上,苍翠可爱。自过小孤,临江峰嶂无出其右。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辞》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飞”者。……泊散花洲,与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犹未极圆,盖望正在是夕。空江万顷,月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平生无此中秋也。(卷四)
(九月四日)过纲步,有二十余家,在夕阳高柳中,短篱晒罾,小艇往来,正如图画所见,沌中最佳处也。(卷五)
(九月)九日,早谒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余,整洁无一枝乱。挂帆抛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矶,江滨大山也。自离鄂州,至是始见山。买羊置酒,盖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诸舟买之,俄顷而尽。求菊花于江上人家,得数枝,芬馥可爱,为之颓然径醉。夜雨极寒,始覆絮衾。(卷五)
就文学而言,正是这些片断使《入蜀记》臻于极高的艺术境界。它们像闪闪发光的珍珠点缀着全文,使之进入了诗的意境。
综上所述,我认为《入蜀记》是宋代笔记中文学价值极高的一部。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它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它从一个侧面标志着陆游古文创作所达到的水平,说明后人称陆游为南宋古文的“中兴大家”,并非过誉。第二,它标志着南宋笔记体散文所取得的成就,说明这种文体已经成为宋代散文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