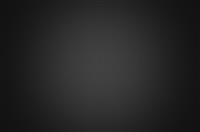近期诚请黄进校长放行,即将南走同济特聘之任时,忽接法大校报主编刘杰先生的校庆60周年特刊之稿约,还挺为难。东海新召,一蓑烟雨,人之将离,其言也废,然刘君那句临别总该有些记忆与感言,至少来点期盼之类,实难拂意,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小月河与军都山之间为期十年的两点一线,何尝没有定格在脑海的河影山花,佯装洒脱的浪迹天涯,怎能冲淡这一方水土的爱恋与离愁。
法兰西先哲孟德斯鸠尝言,只有历史故事乏味的国家与人民才是幸福的。不幸的是,华夏五千年的陈年往事就从未乏味过,至今还在电视电影中占据收视率,还不需掀开中国高校校史的那一片浩劫与悲鸣。当东拼西凑的苏联模式于1952年包打神州时,权力全能的计划教育畅通无阻, “雨后春笋”的情景剧就不在话下。
好事总是多磨的,因祸得福与因福得祸往往就只有一步之遥。法大既是院系调整的产物,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催生品,法学的 “怪胎”身世决定了法大此生将与苦难同行。根红苗正的新校竟在“砸烂公检法”的狂欢中关门了事,道统与法统的重建就难于蜀道。如今的法大校园已把首任校长抓得很紧,铜像、楼名与基金会齐上,但爱青先生离开人世前,就对那段斯文扫地的教职生涯痛心疾首,不认法大,怎不催人三思。人性的庞杂与脆弱毕竟也是校史的真实碎片,“一生一世法大人”原本就不是那一代创业者先入为主的校园歌谣。当劫后重生的法大再造钟鼓,河山两隔,郊外的尘扬与城区的喧闹也无法遮饰捉襟见肘的累累伤痕,同近世国史好有一拼,还没赶上1977—78年的招生季节。记得5年前,校方在昌平凤山度假村邀集部分教授,审订迎接教育部本科评估的“自评报告”时,我曾直言不讳,不必强调本校 “历史悠久”,也不必把近年办公桌上拍板定案的“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八字校训做过度诠释,有啥说啥,危石之下无完卵, 中华大地还有哪所院校能吹一路弦歌,遑论强行解散过的法大?
城里人的小富即安未必就是虚骄的资本,风尘仆仆的赶城回巢却不难释放昌平郊民的粗犷与朴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法大的学子是值得同情的,他们连恋爱的空间都是那么逼窄;法大的学子也是好商量的,他们大都听从我的约法一章,将阳光下的爱情展览归入个人隐私的法权范畴,摈弃生物学意义的校园竞赛,回归斯文生态,那种以永不分离的物理架势敢在师长面前班门弄斧者已日趋减少。我还来不及梳理现代先知遇罗克的《出身论》与法理精义的契合点,但唐人刘禹锡的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或可撑起法大人的自信与自尊。断断续续凡60年的法大校史不难昭示,军都山的“仙”与其说是某些名家名师,还不如说就是法大的基本人口,就是那些凝聚诸多创业潜质与揣怀法治之梦的历届法大学子;小月河的“龙”与其说是哪个练字所得的御笔或龙幸似的御跸,还不如说就是三代法大人矢志追求的法治精神。
近十年来,我也加入郊山与城河之间的畅想行列,在旧版345慢车与新版345快车的吱吱呀呀中书写职业流程。那些怀揣刊有拙稿《慎把青春读明天》的校报逃掉必修课,挤进偏科课堂一呆就是整个学期的学子,就是让我感怀至今的第一乐手,心灵的吟唱胜似飞燕沉鱼;我也感恩于亢山广场的宽敞与畅春园的肃静,让我掂量这一方水土的凝重与生动,领会夕阳穿树的神奇与玉箸无声的感伤。每当收获一份感动,我都不难想起前任校长当年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说过的一句话:“法大的生源特别优秀,但师资相对不够,请郭老师加盟法大,与我们一起培养这些特别优秀的学生。”
挥别在即,最难割舍也最感愧疚的,就是那些比不少院、校领导更重视历史学科,还在“沧海云帆”与法大BBS的投票评选中,分别把我纳入 “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位教师”之列的法大学子,包括我所谬导的硕博弟子与博士后,他们智商高,情商更高。难忘前年腊月家母病危时,飞抵洞庭湖畔的就有不顾我再三劝阻的法大在校弟子,而且先到后报,雨雪无阻;数日之后家母毁家弃养,彼等再派代表南行祭悼,又是落地益阳之后再问路。最近,昌平的学子还郑重要求,离校之前应做“最后一次”讲座,上“最后一课”,离京之后还要经常回来看望他们,继续讲座。另有学子发出请求,老师走后,个人的简历不要删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这一行,就不要与他们无关了。面对这样的学生,我真想全依他们的,他们不是还经常表扬我童心未泯吗?互相惦记与常回来看看,实乃我与法大学子恒定此生的契约,我们的公证人就是军都山与小月河,就是法大。
伊朗诗人萨迪说:“我曾在世界四方长久漫游,与形形色色的人共度春秋,从任何角落都未空手而返,从每个禾垛选取谷穗一束。”临别之前,我愿以任职十年的职业真诚与无期的爱恋,谨向法大60周年校庆筹备组恭呈三款浅见:
第一,主体 勿学北大、清华的做派,像办春晚一样找乐子,硬将校庆办成官人、商人与艺人三位一体的嘉年华,却以冷落沉默的大多数为代价,不妨先来一点换位思考。历届法大的实主已把“北京政法学院”的校名改响改大了,也搞过两校合并,校友们好像没意见,但近年把教学楼与宿舍的楼名都改来改去,这就破坏他们的记忆,威逼他们的归宿感与认同感,他们有点生气了,但愿本次校庆不再刺激他们。
第二,规模 校庆的规模不宜太大,热闹须防过度。节流与否尚在其次,我们的国家毕竟还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初级阶段,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凡此种种,都已不再是庶民难晓的国家机密。换句话说,是人大而非法大,是官大而非民大,维稳压倒一切,民权尚未成功。与此配套的是,以法的名义既能吃通、也能通吃的通人比比皆是,估计我们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也牛不到哪里去,不妨把大庆大办留给后人再说。
第三,场地 切忌10年前的50之庆,瞎搬北大百年校庆的夸张,跑到人民大会堂去交钱豪办,与权力攀亲,其实,那才叫货真价实的“买办”。既然校庆都办过很多回了,如果还没树起学术的尊严与法大人的自信,看轻自己的校园,校庆的法理依据岂不也成问题了?即使没人爱了,也要更爱自己,借故堕落却总是不值得原谅,更不值得欣赏。当然,我也不必奢求法大能以美邦哈佛350周年的校庆为榜样,竟敢公开宣布“无意于奉承总统的虚荣心”,这好像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何况我们国家还没有总统,还是搞中国特色省事。
下笔到此,已知约稿的篇幅早已逾越,但我最想说的还在后头。面对爱我与我爱的法大学子,且留三份嘱托与期待:
甲、基于忝列过两届校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之名,期待我法大学子尽力维护中国政法大学的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的声誉,尽量不要为日益增长的论文垃圾与学位丑闻做出法大人的贡献。人之落地就只具有自然法意义的平等,第二出身更是事在人为。
乙、谨借师长之名,期待法大学子牢记法大人的使命——国家与人间的法治,请先从杜绝校园的要分之风与肆意攻击真言师长的网络暴力开始,法大人的胎记和法大人的光荣与梦想都不是别的,就是法治。我已望眼欲穿,年复一年从法大走出的律师群,总该有人扮演张思之的传人吧?我也不想收回在2010研究生院毕业典礼的视频寄语中说过的大话:神州之大,只要还有一个法官或检察官严拒任何会议、电话、短信与眼色的干扰,绝不放走一个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各类高官与活老虎,他或她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
丙、谨以亦师亦友的身份,与已经毕业与即将离校、入校的法大学子共勉:人生苦短,尽量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此途虽然不太容易,有时还要遭遇不可名状的惊险,却无名额限制,海阔天空。只有在害怕危险的人眼中,这个世界总是危险的。阳光打在脸上,要想受人尊敬,就完全可以从平凡的岗位开始。如果还有人愿意与普希金一同高歌,那就更好:“我给自己建起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它将自己坚定不屈的头颅高高昂起,高过亚历山大的石柱。”
河山依旧,离心难舍。我不愿意看到我对法大学子的嘱托与期待也会人走茶凉,那就在曾经开列的参考书目中,重复四种洋著,它们都是我的临别赠言:
A、【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
B、【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C、【意】奥莉娅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D、【法】以马内利修女:《活着,为了什么》。
2012年4月3日晨草于广州
原载《法治周末》201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