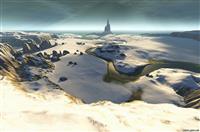这本集子由十五篇文章组成,除最后一篇外,都是发表过的文字。已经读过这些文字的朋友,可以放下这本集子,不必买了。
对于另一些朋友,比如说,想追踪自由主义学理经过五十年沉默为什么会在这一代人中重新开始? 思想史的这一环节如何在自我淘洗中缓慢沉淀? 这本小书或许能提供一个较为连贯的线索。
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很慢,半生已过,只有两步。文革时期朦脆向往法国革命式的激进思潮,改革时期重新发现并逐步走上英美自由主义,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创痛巨深,终于绷断了这两个阶段的最后一点衔接。起步晚,走得又不快,更兼分化剧烈,走着走着,很多人已经不见了,下一代人当然有理由嘲笑我们,我自己也只能把这本小书命名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第一阶段拖得太长,几乎占去了从十五岁到三十岁最好的年月。我的同代人现在很热闹地回顾插队生涯,几乎快说成又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不要说听众,我自己都已经听烦。当初离城,有一种找地方去读书的冲动,后来侥幸以同等学力考进研究生,一进去,就感到与那个学术体制格格不入。十三年后重回上海,越来越不能忍受“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这样的官定名称。当时那样命名,无奈于命名权独在一方,今天再延续这样的说法,则有继续合拍之嫌。我自己想称其为“离城出走”,哪怕是出走了十三年,回来后继续在城市的边缘游走。我曾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描述过这一出走事件留下的怀念和遗憾:
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灰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解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惟一的职业谜手? 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这个“他”是我一个朋友,现在还活在中原省份一个闭塞的小城。我只能让“他”匿名出现,一是希望能将“这一个”泛化为“那一代”,唤起同代人的共同记忆;二是留下一个小小的空缺,看看一部分学院派朋友如何反应。果然,我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些文字又惊呼起来,说这样的“他”是我“杜撰”,是一种“浪漫的炒作”。这些人也算是朋友,我称他们为“数树叶者”,要对这些习惯于计算树叶数量的朋友说清楚树底下还有多少根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是因为树叶比树根纤细,数量上占据优势,还因为树叶总有阳光,敞亮明媚,而树根却只配在地下的黑暗潮湿中此曲蜿蜒;还因为“数树叶者”总是和树叶共享学院里的阳光,凡是没有发表为“文本”者,都不算,也不看。到目前为止,有“话语权者”似乎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开创了第二话语,但是这个第二话语在遮蔽另类语言的功能上却是与第一话语共通的:一旦话语扫描不到某些对象,那些人和事则继续只能算孤魂野鬼状,在权力体系的两边游荡。
思想历程的第二步,是在怀念那些孤魂野鬼的同时,重新上路。第一个引我前行者是已故思想家顾准,那是隧道里的一盏孤灯,一灯如豆。第二个是海峡彼岸的殷海光,同样是已经过世的人物,说过时也可以。至于现在谈得热火朝天的海耶克、伯林,当然是构成可贵的思想养料,从学理深度上说甚至更重要,但就内在生命的感应而言,他们总不及顾准和殷海光来得亲切。如果实在要拉上一个在“文本”上够得上重量的人物,只能是一个更为过时的人物——十九世纪的赫尔半。一部回忆录创造了一种流亡语体,足以弥补历史上所有流亡者加在一起的孤怀遗恨。而在当时,他却是一个沾染了一身旧贵族习气的十二月党人后裔,居然有傲气蔑称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流亡者为“硫磺帮”。那一年之后,我曾两次长读《往事与随想》,它帮助我克服了上述精神创痛。至于是流亡在外,还是流亡在内,倒显得并不那样重要了。
十年里,一个精神危机克服,又一个精神挑战就乘虚而入。就在写下这篇序言的前一晚,我与一个朋友写信:
北约轰炸南联盟,这边知识界和大学生普通咒骂,感情激烈。眼见他们在反对西方国家某些政府行为时,连原来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也随之抛弃,不禁联想起五四初期大陆知识界受巴黎和会刺激,在正当表示对强权外交抗议的同时,突然弃英美亲苏俄,由此发生本世纪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规模左倾运动。第二次是四十年代中期,因受社会不公之刺激,又一次倒向左倾思潮。那两次大规模左倾造成的祸害,一次祸起于外,一次祸起于内,历历在目,至今还没有摆脱。想不到我自己活着时,还要看到一次。前年起,我对此有预感,但到今年溃疡面如此扩大,却还是有些意外。我学的是历史,但最怕看的也是历史,尤其怕看在现实中重逢历史。不幸还是看到历史锋利的刀刃,不声不响地暗中逼近。
你那里是否有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可以读读。在理念上,我与赫尔岑革命民主主义渐行渐远,但在感情上,尤其对历史幽暗的恐惧,却越来越感亲近。我曾说,人们只抱怨政治的残酷,却没有想过在政治残酷的底下,是历史的幽暗。
隔天接回函,又写了一段:
来信收悉,有些话是我上封信中来不及说的,而你说的又比我准确。比如,你说“美国没有理由因为它的制度凝结了一些我们的理想,就裹胁我们必须认同它的外交霸权行为”,就很到位。
你说“把美国的制度和它所代表的民主、自由理想区别开来是有必要的”,我上次就想说这一句。这一点至关重要。这里如能改成“政府行为”,是否更好一点? 我对美国的这个政府行为很不看好。弹劾案进行时,我其实很盼望看到克林顿下台。冷战结束后,居然是克林顿执政,实在是世界之大不幸。我看不出这个人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有像样的估计。
左派和右派都可能在这一问题上犯错误。左派的错误是因为此前把民主理想拴在美国的制度、甚至美国的政府行为上,一旦发现他们也有具体的国家利益,于是大失所望,掉头而去。大陆知识界两次发生大规模左倾化,都与这一认知模式有关。右派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把他们的民主理想全部拴死在美国政府行为上,只是跟着这架莽撞的战车跑,不能保持独立思考。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今天,完全可以在坚持既定价值的同时,理宜气壮地与西方政府的外交决策拉开距离。在自由主义历史上,罗素因为反对英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英国政府逮捕入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历史这头说,我对美国政府的外交能力始终不抱乐观。中国内战是我们这一代亲受其害的经历,它甚至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跟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太年轻,再加一点志得意满。我两次去美国,私下有一个问题: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是因为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成功,还是苏东自己的内部变化? 我的初步感觉,似乎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换句话说,美国是意外地拣了一个便宜。但他们却认为是自己的成功,冷战结束后毫无像样的检讨。历史给了美国十年,却看不到他们有全盘的世界局势考量。历史是没有理性的。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挑战的先后出现两种力量,二战前的日本、德国,二战后的苏俄,由这样的力量挑战美国,而且又都失败,实在是美国的不幸。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是有一半是由他的对手决定的,甚至是由被他击败的对手决定的。我对美国的社会和普通民众抱有好感,但也不是没有忧虑。1996年在哈佛,我曾经与李慎之先生谈到这一问题,他谈到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内在忧虑,说了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他担心美国出现中心空洞化,那将对世界历史造成灾难性影响。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西方思想历史,有时能强调这一点:自由对专制的对峙。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雅典对峙斯巴达、马其顿,一次是美国对峙苏联,古代世界那一次是以自由失败告终,现代世界这一次是以自由侥幸险胜暂告段落。自由并不是必然胜利的,从几率上说,它的失败可能比对方更大。我的历史观总有挥之不去的悲观成分,与这一点密切相关。人这样的生物,能不能始终守得住自由? 太难了,近乎对神的要求,我不敢乐观。
你说你有点左,其实我上次在那里以及你上次来上海就有感觉。我想我能理解这一点。1989年冬天我在电视上看着苏联降旗,百感交集,甚至黯然神伤。此前我预料这一制度会崩溃,但一旦看到苏联降旗,却又感到撕裂了我内心一块柔软的联系。 我甚至与这里的一个朋友说过:“我之所以在与新左派论争时狠不下心说厉害话,是因为我年青时也左过,难道只许我自己年青时左,不允许别人在年青时也左一次? ”一战时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刚上台,他的儿子就在街头参加左倾政治活动,有记者问,“如何看待你自己年青时的‘左’,以及你儿子现在的‘左’?”克里蒙梭从容对答,出语惊人:“一个人年青时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到中年时还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这句话落地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在这一问题上有比克里蒙梭更好的说法。
一个一开始就是从右起步的人,我可能佩服他,但很难与他交朋友。不同的是,60年代你们向往我们,你在台大因为读这里的红宝书而被国民党迫害,我们却在突围,向往你们,打听你们在想些什么,历史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 民主架构初步建成与否,对生活在那一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内心忧虑向那一个方向倾斜,是有巨大影响的。我比较担心的是,由于对西方政府行为的抗议,而放松对旧体制的警惕,甚至因此而走向对后者的认同。我在美国与诸多大陆留学生交往,当然有头脑清醒者,可惜不多,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留下的印象大多不愉快。我曾称那是一个留学生CHINATOWN。
这一认知陷阱,对从小受旧体制教育后来又总是被民族主义裹挟的人来说,特别有诱惑力。你曾很含蓄地表达过对大陆知识分子多半保持“中原心态”的不满,而你所抱怨的“中原心态”就和这一陷阱有关。在内为“中原心态”,在外为留学生CHINATOWN,其实是一回事。
是为序。
朱学勤
1999年3月31日沪上
目 录
序言……………………………………………………朱学勤(1)
卢梭政治哲学之一:原罪与赎罪……………………………(1)
卢梭政治哲学之二:自由之沉没……………………………(40)
近代英美政治思潮与中国……………………………………(74)
近代欧陆政治思潮与中国……………………………………(103)
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折: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132)
地狱里的思考…………………………………………………(151)
——读顾准思想手记
迟到的理解……………………………………………………(164)
“娘希匹”和“省军级”……………………………………(171)
——文革读书记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184)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194)
五四思潮与80年代、90年代…………………………………(201)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220)
“书房里的被动语态革命”与漏斗…………………………(229)
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237)
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257)
——与李辉谈知识分子
新观察文摘
原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