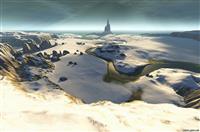说诸葛亮是个英雄,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说英雄也经常会犯错误,诸葛亮并不例外,这一点同样有人相信。千百年来评骘诸葛亮功过得失的文章、言论不知几何,其中直言不讳批评诸葛亮缺点失误的亦不在少数,这种情况早在魏晋时代便已开始,如《三国志》一书作者陈寿就不客气地指出,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并说诸葛亮的北伐中原纯粹是“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云云。然而它们多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局限于讲他军事指挥水平不高,用兵过于谨慎胆小,用人不免掺杂个人感情因素,事必躬亲以致没有及时培养好接班人等等,却放过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失误,《隆中对》并不像论者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古代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的典范之作,是杰出军事智慧的集中体现。恰恰相反,它的基本战略方针乃建立在虚幻、空想的沙滩上面,即战略筹划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或说是不存在的,故尔在实际操作中注定要碰壁的,正是它构成了诸葛亮一生悲剧命运的怪圈,不论诸葛亮怎么拚搏,结果仍是跳不出这个怪圈,“有意栽花花不发”,“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好让后人一掬同情之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 《蜀相》)
《隆中对》的核心,是建议处于多极竞争中弱势地位的刘备集团,乘天下动荡混乱之际,玩弄厚黑手段,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从刘表,刘璋等人的手中,夺取战略要地荆、益两州,同时避免过早地和强敌直接碰撞,“跨有荆、益,严其险阻”。在此基础上调整好各种关系,坐大实力,为逐鹿中原准备条件,“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内修政理,外结好孙权”。然后等到“天下有变”,时机成熟后,再分别以荆、益两州为基地兵分两路,进击中原,消灭曹操势力,实现所谓“复兴汉室”的战略目标,“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从逻辑上看,这个著名的战略构想丝丝入扣,天衣无缝,它既有全面具体的战略预测和分析;又有明确无误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内容充实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更有执行战略方针,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战略措施,真的是没有不料想到的,没有不安排好的。无怪乎,古往今来,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它顶礼膜拜,尽拣最动听的言辞赞美它!“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王叡:《将略论》)
可是,常识告诉人们,最完美的东西往往是最虚假的,完美(《孙子兵法》中称之为“全”)无疑是一种美好的事物,然而正因为它太美好了,太高尚了,故尔只能是“梦中情人”,变得可遇而不可求,在战略上,如果处处求全,事事求备,就会不分主次,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顾此失彼,进退难容,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正如《孙子兵法》所讲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总之一句话,追求十全十美,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隆中对》的弊病,同样恰恰在于它的完美,从而成为一厢情愿,在实际活动中根本行不通的战略假设。
这中间的关键,在于诸葛亮所设想的刘备集团既要“跨有荆、益”两州又要“外结好孙权”两者之间的水火不相兼容。荆州北靠汉、沔两水,南毗邻华南,东与吴郡和会稽郡相连,西和巴蜀地区相通,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谁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谁就可以四通八达,进退自如,攻守皆宜。利益之攸关,使得谁也不肯放弃占有它的企图。不但曹操方面要前来争夺,而且江东的孙权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地盘落到刘备的手中。这样的形势,决定了蜀汉要在保有荆州的前提之下,维系和东吴的联盟关系,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好比一个人借了人家的巨款不还,还要同对方讲友谊,套近乎,做好朋友的愿望注定要落空的情况一样。所以,只要刘备一天赖在荆州不走,孙权就会跟他没完没了,双方联盟破裂,兵戎相见,大打出手乃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事情。在这个棘手问题面前,不但关羽这样的武将计无所出,就是智慧超群的诸葛亮本人也将束手无策。毕竟在现实中鱼与熊掌实难兼得,谁都不是容易被算计的傻瓜!
一旦孙刘两家闹翻脸孔兵戎相见,不仅“外结好孙权”的愿望要彻底破灭,曹操集团可以从中大渔其利;而且从实力和地理形势等综合条件来看,输家也肯定是刘备一方。因为从实力上讲,刘备势力与“立国已三世”的孙权政权相比,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实力不逮,在战争中自然只能占下风。从地理形势来说,荆、益两州中间隔着大巴山、巫山,交通极为不便,战事甫起,两大战区孤立分割,首尾遥隔,相互间难以支援;而荆州和孙权盘据的扬州,在地理格局上则联成一片,形成相对完整的吴、楚地区,可以做到进退自如,配合默契。从这个意义上看,地理形势也是有利于孙权而不利于刘备。与兵要地理条件的不利相联系,刘备集团本来兵力有限,而“跨有荆益”,实际上是将有限的兵力再加以分散,这诚属用兵之大忌。毛泽东指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6页),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症结。战局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江陵之战和彝陵之战,孙权不仅一举铲除刘备势力的头号大将关公,轻轻松松地从刘备手中夺回了荆州,而且还彻底挫败了刘备重占荆州的企图,赢得了荆州争夺战的最终胜利。
蜀汉势力“委弃荆州,退入巴蜀”之后,要再北伐中原,完成统一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条件,这也意味着《隆中对》的战略目标从此变成了水中之月,镜里之花。因为巴蜀毕竟是出入不易、偏居一隅的“独守之国”,用于自守,尚勉强可行,用于进攻则实难思议。这一点古人早就有论说,且是言之成理:“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击,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以制中原哉。”(苏询《嘉祐集》卷三《权书》)它的局促与闭塞,决定了蜀汉的人力、物力处于劣势。用张俨《默记》的话说,就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指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这一现实,聪明睿智如诸葛亮者当然也心中明白:“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前出师表》)而其主要对手曹魏,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真可谓是“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更为不幸的是,诸葛亮所面临的敌方统帅,恰恰又是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司马懿,“所与对敌,或值人杰”。诸葛亮军事指挥能力上也有欠缺的地方,“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客观形势的不利,所遇对手的强悍加上自身指挥水平的局限,使得诸葛亮的北伐之举雷声大雨点小,只开花不结果,“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距离《隆中对》的战略目标是越来越远。
既然《隆中对》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两者之间是永远无法接轨的败笔,那么它就是一个无法用具体行动来证实的怪圈,是一座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空中楼阁。脱离实际的理想,便是幻想;不能实现的计划,等于空谈;无法成功的战略,实属摆设。诸葛亮走不出《隆中对》的怪圈,这意味着诸葛亮自己终结了《隆中对》的前途。这虽然令人遗憾,但是却教人信服。
可见,《隆中对》不但不是诸葛亮的光荣和骄傲,相反它倒是诸葛亮人生追求中的一大败笔。杜甫称颂诸葛亮“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其五),这作为同情之辞,可以理解;但作为笃评之论,当属臆度。
当然,《隆中对》的不足,并不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在人们的眼里,诸葛亮的人格始终是极其伟大的,这种伟大,集中体现为崇高之美,悲情英雄,即诸葛亮勇于向悲剧性命运挑战,是不计成败、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舍生就义、临危不惧、九死不悔等高尚道德情操的化身。用他自己的话讲,便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裴氏以此表出《默记》)。大家热爱他,崇敬他,主要不是冲着他的功业去的(历史上比他功业显赫的人多得去了,他同时代的曹操论事功就远远超过了他),而更多的是出于对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英雄人格与献身精神的仰慕和向往,即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