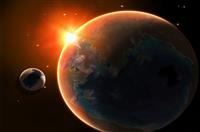自1927年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在南京开始其全国当政的历程后,奉行一党“训政”理念,在政治上建立不受监督的“党治”,经济上创立由国家政权控制的经济体系,企图经由中央统一的、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而达成其“建国”目标。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党治”得益于北伐战争的疾风暴雨而一夕告成,而其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成效也不及政治上的“训政”和“党治”那般显然。不过,抗战爆发后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战时集中资源支持战争的需要,使国民党实施经济统制政策的进程明显加速,以“四行两局”(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代表的国家金融资本和资源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工业资本,逐渐在中国经济的相关领域占据了垄断地位,而国民党“训政”体制下“党治”之无人、无力监督的状况,使负责管理、运作这些国家资本的各级官员利用其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情况不断出现并日渐严重,由此亦使国民党控制的国家资本渐以“官僚资本”之名义而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为舆论所强烈批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控制的国家资本力量达至其历史最高峰,而同时社会各界对“官僚资本”的批判声浪亦扩大至各个层面,甚至国民党高层内部也无法漠视此等批判与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战后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成效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僚资本”问题曾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本文即以此为中心,讨论“官僚资本”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引发的争论及其与腐败关联的有关问题。[1]
一、战后国家资本的急速膨胀及其社会反响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获得最终胜利,国民党也因其执政党地位而基本垄断了战后接收,从日伪手中获得了其执政以来最大的一笔经济、文化、教育、社会资源,[2]并几乎全部转入官方的控制。正是因为接收,原日伪产业中的大多数以自营、转让、标售、拍卖等方式,转移到国民党当局手中,从而使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急速膨胀,并发展到其最高峰。据估计,战后中国资本总值为142亿元(按1936年币值计),其中国家资本占54%(战前为32%);如果以分类计,则国家资本占产业资本总值的64%(战前为22%),金融资本总值的89%(战前为59%)。[3]可以说,当时的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并在金融资本中占据了压倒优势地位,反映出国民党历经20余年的经营,已经建立了由国家政权掌控的、可以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集中在官僚经营下的经济体系。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的若干垄断性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原有国家资本单位发展的代表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规格提高为部级单位,下属九个重工业部门与两个轻工业部门,共96个单位,员工22万余人。[4]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属90%以上,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5]新建国家资本单位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代表,国民党不顾当时强烈的民营呼声,将接收的日伪纺织业交国家垄断经营,在1945年12月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几乎所有部门,员工7.5万人,拥有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产量占70%,[6]从而使国家资本在原本并无任何基础的纺织业几乎是一夜间就建立起具有垄断性的地位。而且,中纺公司作为国营垄断性企业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棉花,以及免受限额收购、垄断纺织业进出口贸易等,在与民营纺织业的竞争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地位。
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有多种实现形式。[7]经济学家王亚南将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即由官僚自己参股或经营的企业;其二是官僚使用或运用资本,即名为国营企业但由官僚处置;其三是官僚支配资本,即既非自己经营,也非通过国营形式运用,但却因种种原因在多方面受官僚支配的私人资本。[8]在这三种形式中,第三种形式牵涉较广,概念有欠严密,姑可不论。第一种形式属于官僚个人资本,亦即纯粹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等。而通常所说的国家资本大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即名义上为国营公司,由国家政权控制及支配,但实则操纵在企业负责人即官僚个人之手。由于这些企业负责人的派系与人际关系及其个人素质等因素,使得企业运营往往成为部门、集团甚或个人谋利的工具。无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些企业国有而又由官僚掌控的特性,国民党内确有一批权贵、官僚、豪门、世家,利用权势寻租,以国家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从而成为社会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国家资本无论其运作形式如何,有无官僚豪门插手,均被外界和舆论指为“官僚资本”,遭至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出自经济学家马寅初。[9]而历史学家傅斯年也曾经不假辞色地抨击说,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10]曾有国民参政员提出议案,痛斥“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要求公务员及公营事业人员,应宣誓不兼营工商业,如有兼营者应在两者间作一选择,否则任何人得告发之;如有利用职权经商图利者,应依法加重处罚。[11]
对于“官僚资本”的社会抨击,多始于抗战后期,其影响逐渐蔓延到国民党内,其党内部分“清流”人士也开始呼应社会舆论,批评“官僚资本”。由于蒋介石长期信任以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为代表的财经官僚,在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派系矛盾作用下,不当权的非主流派、缺乏实际权力而又自奉“效忠党国”的党务系统干将以及抱有各种目的的其他各色人等,亦纷纷借此发难,攻击当政的宋、孔等人。一时间,在国民党内甚而形成以批判“官僚资本”为号召的特异现象。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由CC系文宣系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曾多次发表社论,抨击“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提出“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并且应该追究一下,这些年中间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一切政策和方案搁在一旁的,究竟是谁?把财政经济弄到今日不可收拾的田地的又是谁?然后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12]由此构成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讨论“官僚资本”问题并引发激烈争执的大背景。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召开的首次中央全会,也是全盘检讨并决定其战后政策及施政纲领的重要会议。有关对共关系、对苏外交、东北问题等等,都成为全会讨论的重点,而日渐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亦为与会者所关注。4日,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翁文灏分别向全会报告财政及经济工作,他们的报告就事论事地谈及财政、经济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对政府政策有所解释与维护,但对与会者关心的如何解决收支平衡、稳定物价、公平接收、惩治贪腐、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并未多见提及,结果引起部分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成为全会讨论的热点。
3月5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经济问题。萧铮(中执委)首先发言,表示对经济报告“根本不满”,认为经济问题在于忽视民生主义,没有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而培养了官僚资本,统制经济亦全失败,派遣接收人员不廉,社会指责甚多。他直率地提出,这些失策之处,应由经济部负责,经济部长如承认错误,应即辞职,否则,全会应予罢免。
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认为:现在的经济,只见通货一天天膨胀,物价一天天高涨,可说民穷财尽,水深火热,老百姓的厌恶心理都集中到政府身上;病根所在,就是没有实行民生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以致一切落空。他提出,应清算责任,明是非,严赏罚,有办法的拿出办法来,没有办法就光明磊落的退下去。他将不能实行民生主义的原因归于官僚资本作祟,认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猖獗的结果,使工商凋敝,建设无从着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财富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可谓是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他要求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
吴铸人(中执委)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如果经济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办法,前途将不堪设想;而经济问题之不易解决,是官僚资本的作祟。他疾呼,这些人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千万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
吴绍澍(中执委、上海市副市长)在发言中指责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带头涨价,应对上海的物价上涨负责。他质问宋子文对人民和公务员活不下去的情况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长应为此负责,如果说没有办法,可以向二中全会辞职。
郑亦同(候补中执委)说,国民党本来不准官吏经商,但现在官吏经商遍地都是,此问题不解决,任何经济部长也无办法。希望中央或监察院加以调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护以经商的有多少人?他们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究竟有多少财产?调查清楚以后,拿公允的办法去处理。
在当天的讨论中,以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的发言最为慷慨激昂,他强烈批评财政部和经济部的报告既没有看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认为现在的问题十分严重,时机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当局疾呼:有办法的赶快拿出来,没办法的说出来;有办法的担起来,没办法的放下来。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鼓掌欢呼,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场内气氛。
综合5日的会议讨论,发言者基本站在对国民党财政经济政策的批评立场,几乎没有人说当时经济政策的好话,而对“官僚资本”却有严厉的抨击。其实,发言者批评的官吏经商、官商勾结的情况,与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未必就没有,但鉴于会场的气氛,这些人即便不同意发言者的意见,但也不便或不敢公开反对。不过,应该注意的事实是,发言者以在行政当局没有实际任职的党务系统尤其是CC系中央委员为主(包括本文未引用的发言者的身份),他们在理论上更坚持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党统”,常常将民生主义挂在口头,故对所谓“官僚资本”谋利的情形确有不满;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国民党以行政为重心的权力体制下,不能掌握实际的资源,从而与行政当局有很深的矛盾,往往借题发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怨气。因此,他们对“官僚资本”的抨击,究属固持“党统”理念,还是企图以此掌握更多的资源,以在国民党当政时分一杯羹,还可探究,至少,后者在他们心中所占的分量恐未必少于前者。也是在此次全会因对苏外交“软弱”而备受攻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即将CC系委员的发言解读为“彼等预定之攻击计划”。而蒋介石过后亦愤愤认为,他们“目的只在攫取中央常务委员”。[13]再者,批评者的发言也没有对解决“官僚资本”问题提出多少有创见的、可操作的政策意见,空言放炮的结果,实际于事无补。
5日的会议结束时,萧铮临时提议对经济部报告认为不满意并请撤回的提案。
表决的结果是,赞成者78人,未过到会者174人的半数,未能通过。[14]该案得到与会者近45%支持的事实,说明国民党内确有不少人警醒于“官僚资本”问题的严重性,企图予以一定的补救,但其提议不过是对经济部的报告不满意,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措施,实际上相当温和,最后却未能通过,也说明国民党内的多数人还是沉迷于以往的既得利益而不能自拔,不愿将口头的不满付诸于改革的行动。
继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官僚资本”问题的激烈争论之后,8日的会议再次掀起对“官僚资本”问题争论的高潮。当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十次全体会议,由行政院长宋子文作政治报告。他通篇所谈几乎不涉政治,重点却在“当前最紧要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他坦承“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即本席个人亦觉得不但不能满意,而且是极不满意”。他将经济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战争带来的收支不平衡,但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无非还是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老套,而且承认“还需要相当时期,方能成就”,表现出他对此亦无充分的信心。[15]他曾在稍后举行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表露过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没有离奇巧妙的办法,不过无论任何办法,必须切合国内外情势环境,……政治问题非常复杂,目前的困难尤多,因此,我极希望有能力的人来代替,本人能力薄弱,与各位所理想的人,相距甚远。”[16]至于六届二中全会部分与会者在前几天会议上对经济问题的责难和“官僚资本”的抨击,宋子文在报告中几无回应,因此,作为担负主管经济责任的行政院长,他的报告遭到与会者的批评自难避免。由于宋子文报告后即离开会场,更引起部分与会者的强烈不满,他们的批评所向自始即毫不隐晦地直指宋本人。姚大海(中监委)提议,应待宋子文出席后再行检讨,得到与会者的鼓掌支持。国民党元老张继(中监委、国民政府委员)呼应说:(宋子文)这件事是不对的,这种态度太不对了。开会往往不到会,你们说你们的,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来听,在常会在国防会早尝到这种滋味,今天全会还是如此。你们质问,我听不见,这是世界美国所没有的。主持会议的何应钦和稀泥说,我们一面打电话请宋院长来,一面继续进行讨论。但张继坚持暂不讨论,等宋来了再继续讨论。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支持,何应钦只能派人请宋子文回到会场,听取发言。
宋子文到会后,讨论继续进行,不止一位发言者将攻击矛头对准宋子文,直指其施政不当及经商谋利,宋“大受攻击,体无完肤”,“神态极窘”。[17]袁雍(中监委、汉口《华中日报》社长)说,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布了公务员服务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或公司银行的董事长及总经理,但现在南洋烟草公司的董事长是宋院长,香港广东商业银行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宋院长,试问这种法律的意义在哪里?违法的是官吏还是人民?李宗黄(中执委、云南省党部主委)讽刺说,什么叫官僚?从外形看,是装腔作势,依势作威,大摆其架子,大打其官腔,不中不西,带通不通,这就是官僚。胡秋原(候补中执委、国民参政员)提出,我们的政府不是万能政府而是无能政府,行政院长应负政治上的责任,因为胜利以后政治无能,接收问题天怒人怨,我们确已到了不能不调整整个党政阵容的时候了。黄宇人(中执委)质问说,今天检讨行政院工作,感觉是失败了,没有尽到责任,官吏贪污之风不但不能澄清,且比以前更甚,尤其是收复区接收人员贪污更多,行政院不但不能推行政务,即连所属的人员也管不了,行政院下面某部次长一人兼了十一个商业机构的董事长,请问,这种违背国防会与行政院规定的行为,政府知不知道,知道了何以不办,不知道便是失察。钟天心(候补中监委)认为,宋子文就职以来,现在比从前好,已经是成大问题,假使照这样做下去,将来能不能比现在好,尤其成问题;负行政责任的人以及行政院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各部,要多替没有钱没有饭吃的老百姓设想,而不再替产业家等有钱人设想才好。
面对与会者的直言批评,坐在席间的宋子文真是如坐针毡,当发言告一段落后,他不能不起而答复与会者的批评和质询。他首先承认,今天蒙各位的批评,真是体无完肤,各位加我的罪名实在太多了。但随即为自己辩护说:各位也实在把我看得太重了,说经济问题是我弄出来的,财政问题是我弄出来的,纪纲问题又是我弄出来的,不要说像我这样没有能力的感觉困难,恐怕其他人办起来也感觉困难。对与会者的批评,他知道难以解释,而且无论何等解释也未必使他人满意,故其干脆不再解释,而是表示完全承认。至于要他承担责任、挂冠辞职的呼声,他先说自己第一个赞成,接着不无怨气地表示:财政如此困难,我又没有发明摇钱树的才具,是难办得妥当;许多事情没有计划好,工作未积极推动,但是我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一张嘴,而且又是一张不会讲话的嘴,有些事情不能办好,觉得十分抱歉。宋此说采取的是以退为进之法,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不仅他还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而且临阵换马,又是难解之局,国民党内也未必有人挺而出面接这个摊子。宋子文着重对他兼职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僚资本”问题作了解释:有人说我是官僚资本,听了实在受不了;因为南洋烟草公司是我以前办的;广东银行一度倒闭,我是广东人,许多广东朋友在我下野时候,劝我设法复业,后同孙科、吴铁城先生共同恢复业务;中国建设银公司也是在我没有到政府以前办的,但我不是直接的负责人。我做了官吏之后,所有董事监事的职务都已辞掉了,所以说我提倡官僚资本,实在不敢当。如果我利用地位职权发国难财,监察院可以查办。[18]
六届二中全会部分与会者对宋子文的猛烈批评,可谓其来有自。首先是他担任行政院长,负责战后接收与经济重建,但是,战后接收却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与贪污腐败行为,“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更,致敌伪事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丧失人心,莫此为甚。”[19]当时民间舆论的代表——《大公报》在接收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发表社评,痛责国民党“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足先抢”;呼吁“收复失土,千万不要失去人心”。[20]尽管宋子文是接收开始两个月之后才统管此项工作,接收中的种种弊端与贪腐行为未必都能由他负责,但作为行政当局的最高主管,他为此受到社会各界的责难也是很难避免的,如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所言:“自胜利以后,接收污弊,物价日增,确为人所痛心,故对宋发泄亦为情理之常。”[21]其实,六届二中全会部分与会者对宋的批评,不过只反映出外间对宋批评的一部分而已。
其次,宋子文处理接收日伪产业的政策,尤其受到外界和国民党内的批评。宋处理接收日伪产业政策的重要方面,如前所述,是将这些产业以种种方式转由国家经营,从而大大加强了经济产业的国营化和统制化。此举固然与宋的经济理念与国民党的统制经济政策有关,还在1930年代初期,宋就表示认同统制经济理念,提出“确有必要弃置各部门互不相谋各自为政而定出的种种杂乱重迭计划,成立真正有效的计划机关,以指导国家的生产力,协调各部的行动,并缜密规定各有关机构今后若干年所应达成的基本目标。”[22]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接收产业被化公为私,即便是转为国营的产业,也在一些官僚的经营下,效率低下,并成为部门、单位和个人谋利的工具,由此招致外界对“官僚资本”的强烈批评,并被解读为宋子文以此垄断接收资源,为其个人和属下小圈子谋利。由陈立夫主导的CC系党务系统本来就对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垄断行政和经济资源不甚满意,对其日常施政措施屡有批评,陈立夫还曾多次当面指责宋经济政策之不当,并通过其掌控的《中央日报》等传媒,对宋发起公开批评。[23]此时更借机向宋发难,CC系中央委员成为全会期间批评宋子文的主力,他们的批评集中在对“官僚资本”的不满并将宋子文视为“官僚资本”的代表和代言人。他们的言论当然不乏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派系矛盾因素和对权力与资源的渴求,但对“官僚资本”的问题能够公开批评并见之于国民党党报,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的问题,而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社会问题。
六届二中全会部分与会者对宋子文的批评责难,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关切,而且如此激烈的批评,可能也出乎蒋事先的意料,并使蒋感觉其不利于国民党的团结和对外形象。3月17日,蒋介石在六届二中全会讲话时出面为宋子文公开辩护说:“自去年到现在为止,各种经济上的情况日益严重,我以为这根本没有危险,尤其法币基金与外汇基金根本没有动摇。现在财政金融的情形,法币增加,物价增高,只是一时现状,根本没有动摇。……经济没有很大危险,这不是安慰各位,而确实如此。”[24]值得探究的是,蒋在其讲话中只是为宋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现状辩护,却完全没有提及全会发言者对宋批评的又一重点——“官僚资本”问题。以蒋与宋的关系和他对宋的辩护,蒋未提及此点,或许多少也表明了他的态度。不过,蒋介石的表态使宋子文的处境有所好转,与会者顾及“总裁”的面子,至少对宋的公开批评有所收敛。全会在15日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和17日通过的《财政经济金融决议案》也都没有提及“官僚资本”,而代之以“官僚主义”和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批评。[25]这样,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曾有过激烈争论的“官僚资本”问题,在其对外发表、宣示政策的正式文件中却是雁过无痕、水波不兴,正所谓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是,其对国民党统治稳定的严重影响却是其党内也无法完全回避的问题。
三、国民党执政的严重危机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官僚资本”问题之争论及不少与会者对之言辞激烈的抨击,姑不论其间蕴含的派系矛盾与利益之争的因素,确也反映出国民党内部分高层人士对其党的性质蜕变及其执政力弱化所造成的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全会期间,由国民党中央常委吴铁城(兼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陈立夫根据“党内同志对于党务革新颇多建议”而整理汇编为《党务革新方案》,明确表达了国民党对其执政前途的危机感。该“方案”将“官僚资本”问题提升到“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的高度,但又无奈地表示,“事实如此,无可谁何”;“坏者欲去而无力以去,好者欲作而无力以作。”为何如此,该“方案”追根寻源,总结其原因在于:国民党既离开民权主义,亦离开民生主义,在建国最基本之经济问题上,思想混乱纷歧,政策彷徨暧昧,既未能以减租或土地利益与农民,未能以立法保障与工人,亦未能以经济保护与中产以上之阶级,遂使政府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政府,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同情与拥护。该“方案”不无感叹地言之: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就其对国民党执政危机根源之认识而言,此等表述不可谓不深刻,亦不可谓不沉重,何况其还出自国民党中央的提案,也可见此等认识非其党内个别人的想法。既然国民党已经从当年号称代表全民实行“三民主义”的政党,沦落为不仅不能代表工、农、商之利益,甚而不能代表维护其政权基础和运作的官吏的利益,“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的政党,那么,国民党怎么还能要求哪怕是自己的党员(更不必说党外的广大社会阶层)为维护这“少数人之利益”而不惜奋斗牺牲?当国民党其时正在与中共争夺对未来中国的主导权时,这样的结论岂不预示着国民党在这场争夺中的黯淡结局?
当然,国民党并不甘心就此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党务革新方案》为此提出应该在国民党内实行彻底的“革新”,其原则为:必须坚决反对党政军内之官僚主义及与此互为因缘之官僚资本;党内须同时展开肃正运动,其对象首为有重大贪污事实而未受惩处,及官僚资本剥蚀国家利益,
阻滞本党政策,溃堕本党声誉,与专作党内奸细之挂名党员。[26]问题在于,国民党的行为做派往往是言大于行,看其言论表述是“政治正确”,然其实际作为却是言不及义;何况其党内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传统和复杂无比的派系纠葛与矛盾,使国民党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形成了久已为之的惰性与惯性,任何革新动议提出后都如石沉大海,难以付诸实施,以至其享有独裁权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也不禁感叹:“权利是个人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分担。对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就是争权夺利,互相防范”;“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信心”;“本来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27]势已至此,夫复何言;一叶知秋,何论其他。
一般认为,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腐败的普遍化而使其在与中共的争夺中失去民心,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的接收过程中,国民党各级官僚的贪腐行为所致之“天怨人怒”,是其党内也不能不承认的事实。然而,那些具体而微的贪腐行为固然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公信力与影响力,而其党内高层的政治腐败,致其对党内和全国局势渐渐失去控制力,则在更广大、更深刻的层面,侵蚀着国民党的统治力与执政力。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官僚资本”问题的争论或可为例证。无论“官僚资本”在经济学上如何界定,至少在战后的社会现实和舆论语境中,“官僚资本”已经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实际成为政治问题,成为国民党备受社会各界抨击及失去民心人望的软肋,当然也是国民党的政治对手中共可以动员民众和舆论、批判国民党、从而有利于其革命事业的利器。对此,不能说国民党没有认知,也不能说国民党没有提出解决之道,但最终的结果如何,已经为以后的历史所见证。当国民党面临其统治的严重危机之时,其党内从上到下毫无团结奋斗、力挽狂澜之决心与信念,一般党员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有权有势者更是只图利用权位、谋取个人私利,以至拔一毛而利其“党天下”所不为。后人或可由此探究其间之种种前因后果,然结论却并不高深奥妙,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蛀生,腐败与政治的关系于此得以充分的表现,难怪并非国民党员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这样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8]
注释:
[1]本文是作者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系列研究之三,研究之一和之二请见《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2]关于接收日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最少估计为33496万美元(《我国接收敌产估计表》,“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66年版,第106—107页),最多估计为79914万美元(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今人统计为67896万美元(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页)。另据国民党当局在1946年底的统计,仅苏浙皖区的接收总值即达法币12648亿元,约合美元1亿多元(《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57—167页)。以上不论何种估计,接收的日伪产业都是一笔巨额资产。
[3]吴承明、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22—723、727、731页。
[4]“国史馆”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82、131、142页。
[5]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6]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28页。
[7]据研究,“官僚资本”的概念最早来自于中共领导人瞿秋白1932年所著《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官僚资本”名称的盛行是在1941年以后。但是,“官僚资本是个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些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总序第18页)
[8]王亚南:《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1947年3月25日《文汇报》。
[9]相关论述请参阅周勇林、张廷钰编:《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0]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陈昭桐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11]《国民参政会关于严厉清除官僚资本的建议》,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12]青年远征军第二○八师政治部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重庆1946年版,第114、123页。
[13]《王世杰日记》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版,第280、288页。
[14]《六届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速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藏档,档号6.2/6。
[15]《宋院长政治报告》,1946年3月9日《中央日报》(重庆)。
[16]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8册,第930页。
[17]《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8日,Chang Kia-ngau Papers,Box 18,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18]《六届二中全会第十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档号6.2/6.19—25.4。
[19]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重庆1946年版,审4第134号。
[20]《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1945年9月14日、27日《大公报》(重庆)。
[21]《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版,第10册第540页。
[22]阿瑟·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328页。
[23]据此后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所记,陈立夫曾“批评宋子文经济政策,一对生产紧缩则通货更膨胀,二对国产工业认为不足重轻,三国营不应赢利”。(《张嘉璈日记》,1946年11月12日)
[24]《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十九次会议速记录》,1946年3月17日,党史馆,档号6.2/6.26—29。
[25]党史馆,档号6.2/11.5—15.2。
[26]《党务革新方案》,党史馆,档号6.2/8.13—1。
[27]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7)》,(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63页。
[28]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世纪评论》第7—8期,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