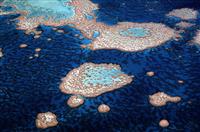
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各种变化中,与人本身关联密切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而其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在中西的碰撞、冲突与竞争之中,读书人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对所谓的近代“转化”感受最强烈,可以说“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也因此,他们的社会变动及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时代的激变。
上面一段里引号中的文字出自杨国强兄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书,该书以“士人”为对象,考察嬗变中的“世相”,确为上选。作者特别注意到,晚清朝野的改革呼吁和实际措施,本皆出于“取新卫旧的愿想”,但在“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背景下,形成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逐渐演化为一个“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过程。在此进程之中,“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再到后来出自学校的“知识阶级”,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都非常明显。而正是他们中一些人,以士议的重锤粉碎了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科举制度,因而也“自己消灭了自己”。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向有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纪传体”传统,后被梁启超攻击为无数墓志铭“乱堆错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史学仿效的是西来的章节体论著,略近于以前正统士人不屑为的章回小说。随着西方社会生活中人的一步步异化和物化,近几十年西方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形成一股很强的潮流,即人的隐去。而西方史学恰是我们想要摹仿的榜样,结果是我们自身的史学论著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类别、角色、数据、甚或指数,而越来越少见具体单个的人。
国强兄的眼界甚高,看当世和看历史略同。如今一些具有可写入履历之虚实名衔的学者,在他恐怕真是不屑一顾;同样,晚清的翰林院检讨、编修,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小京官”而已。可以说,这是一本充满菁英眼光的著作,即使关注到基层一些的士人,有意无意之间,也往往带点俯视的意味。今日研究者盛行眼光向下,若套用一句古话,见贤者贤,见不贤者不贤。一味眼光向下,或不免多见鼠窃狗偷之事;倘若“取法乎上”,即使同类行为,也在“窃国”、“窃意”之间(即“窃国者侯”、“其意丘窃取之”之谓);其间的分寸,有时不可以道里计。
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中,侧重人的嬗变,更以偏于菁英的“士人”为主要考察对象,多少有些逆流而行,实难能可贵,同时也提示了一种看问题的起点。对于近代史的研究,我自己也常提倡在关注上层菁英的同时,更多面向中下层之人。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晚清虽可见许多士人“自我批评”的反智言论,仍是一个以菁英读书人为核心为典范的社会。当年的实际情形,如鲁迅所说,是“平民还没有开口”,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社会里,史家选择什么为考察的中心,自然与其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直接相关。
但菁英读书人是不容易考察的。正因为这是一个受时代变化影响最大的社群,也因为史学本身同样受到世变的影响,这些人的“世相”已模糊到难以辨认的程度,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学术构建出的充满了翻译和简化的特定形象。很多人早已忘却了当年的功名与富贵往往不能两全,固然有和珅这样富可敌国的巨贪,也可见不少“高官的清贫”。“多金为上,位尊次之”的局面虽早现端倪,基本要到民国才形成。本书重建出的“清代功名与富贵”,其实也就是剥去我们学术言说中“作雾自迷”的翻译与简化,而回归到更接近原状的“世相”。
今日的读者观众习惯了西来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看惯了倒演现代官场术的古装连续剧,恐怕已经不清楚历史上曾经还有遥控天下士风的“清议”在,以及“中国的知识人曾长久地与清议相依存”。清议的一个载体是“清流”,他们以清议的喉舌自居,也常挟清议以制重臣。然而当朝野的追求从“富而后教”的虚悬目标转为退虏送穷的切实需求之后,名节遂不如干练,清流乃转化为无能。晚清崛起的是一批未必正途出身的“干员”(其实他们中许多人工诗文、善小楷,与清流私交不错),即使曾属清流的张之洞当政,也不能不多用这批干员。
张氏晚年最主要的业绩是办新学堂,产生出一大批能言善辩的“名士”,介乎于清流和干员之间。朱一新曾说:历史上清议出于学校,横议也出于学校。“学校之习一坏,则变乱是非之说,多出乎其中”。清廷最后的疾速崩解,一般均认为这批新学生出力甚多。从那时起,发议论的阵地逐渐转向报刊,而发议论者似乎仍是读书人社群;不过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他们与早年的议论者既前后相连,也前后相异,两者都非常明显。
类似的睿见,处处反映在关于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作为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之清末新政、半由读书人构建而生的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几代读书人的演变及其社会相等等重要议题之中。讲到士人,不能不论及学术。作者也曾畅论汉学宋学的兴衰演变,却多跳出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而从世运盛衰着眼,别有一番心意。故其所见,与所谓思想史和学术史中人所论不尽同。
以我粗浅的看法,清代学术史中一般人心目中被汉学压倒的宋学,多在今日意义所谓的“学术”界域之内。在当年考试的领域里,宋学始终是取士的标准。所以,除极个别从头至尾都不涉科场的读书人外,没有一个所谓汉学家不是从宋学里走出来的。真正导致宋学终成绝响的,是清末的废科举。民国初年有所谓新汉学的产生,不论夹杂了多少新成分,多少总偏向考据的一面,恐怕与废科举后宋学被釜底抽薪,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样看来,世局与学术的关联,的确超出我们的既存认知。
当年陈寅恪就试图表明,只要解读的方法正确,以常见史料为主的文字史料完全可以让史家与古人相通,并写出接近往昔真相的历史。他那时强调文字史料的解读,其隐约针对的是民俗调查、歌谣搜集等等北大“新史学”的新取向。本书基本不用档案,其余所用史料也大多常见,尤能注意笔记材料的使用,可以说再次证明了陈先生关于史料解读重于搜集的见解。国强兄清楚地表明,就是大陆中国近代史体系所常用的那一套史料,也可以看出并说明不一样的问题。
我这里所说的“体系”,是指改革开放初期刚开始招研究生那几年形成的一个师生学术圈子。后来师生两辈人中各自的学术观念都已有很大的区别、冲突甚至对立,但其关注的人物、事件和使用的史料则大体相近,仅少数例外,且未必都成功。这些方面,“体系”外和“体系”内是非常不同的。如清人笔记就很少被“体系”中人所使用,盖觉其不可靠也。其实笔记的特点是“常事不书”,故读之易见其变;其中的观察,每每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全看读者的眼光和识见。
简言之,这是一本非常之人写的非常之书。说是非常之人,作者治学从容,很少出席学术会议,很多人都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说是非常之书,本书较少受所谓学术规范的约束,看似并不十分在意与既存研究“接轨”。其实作者当然关注着中外的研究,例如他也认为清代处于“中世纪”(这是一个明显以西例中的词汇,有些人用此以指中国落后,但由于这一“中世纪”似乎可上溯到汉朝,仿佛也有几分中国走在西方前面的隐意),同时他也使用“内卷”一类新词。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充满睿智而光彩照人的著作,势必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书。尤其在学术著作越来越像律师文书一样简白无华的时代,似这般文采斐然的史著,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了。
作者指出,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办法串起来”。这一带有几许无奈的描述非常形象,相信很多研究近代者都有同感。我的隐约感觉,本书正是在收拾、整合那一地碎散的文辞。
这些碎散的文辞既可能是从某一系统中散落出来的只言片语,也可以是原就散乱而零碎的无系统见解。我的感觉,晚清人的思想言说或介于两者之间,每一个人表述出的见解或许不那么系统,但都处于某种观念系统的影响之下,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可整合性。
这个问题当然不那么简单,假如这一地碎散的文辞原是一串或多串的钱,它们是可以重新串起来的,因为钱币是按模具人工制作的,其共性远大于其个性;但若这根本就是一地秋风扫下的落叶,离开了与树干相连的树枝,甚或被吹离了原来的树林,它们还能复原其本义么?
“一干竖立、枝叶扶疏”的鲜活之树,多见于热带和温带的一些地区。在很多地方,秋风扫落树上的叶片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冬天的一棵树可能叶子很少,甚至光秃秃的。而我们现在见到的许多史料,可能就是一片片往昔的落叶。或许它们确实具有“独立的生命”或单独的意义,此当别论;但这样的意义却不能取代它们与树干连接在一起时的意义,如梁启超所说:历史文献中任何单词片语,都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
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能找到其原来的树,通过树枝确立落叶与树的关联。但更多时候恐怕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无法觅得其原树的状态,或觅得原树而无法重建双方的关联。于是产生了问题:如果不能确立落叶与树的关联,即使我们搜集起一堆落叶,我们怎样理解特定的一片树叶或一堆树叶?怎样把它或它们置入我们希望再现的历史场景之中?
一方面,后人用树叶构成的拼图,可能更多不过反映出拼接者对树叶的认知。另一方面,在失去了原有的穿钱绳索之后,以现代的绳索重新串起来的钱币是否还具有接近原状的意义?或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体现其原初的意义?大概都还是有争议的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这一地碎散的文辞原就是一些散乱而零碎的无系统见解,他们是否有某些时空的共性,经过整合可以表现出某种未必系统却具有关联性的意义?
这样的历史,其意义究竟类似于树叶构成的拼图,还是新绳索串起来的旧钱币,恐怕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继续发展的进程,后人对往昔的重构不论是否是复原和再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是复原和再现,它们已然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也许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然而河的下游仍然流淌着上游的源头活水;且不论后之整合是复原还是再造,多少都有往昔的因子在,因而也是往昔的一种再生。
我前些时候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历史不必是负担,它也是动力,是资源,是发展的基础。对中国而言,近代是个真正礼崩乐坏的时代。由于传统的崩解,以及新思想资源的出现,有心人不能不重新思考一些人生社会的基本问题,这是在典范具有威权的承平时代很难见到的。他们的见解可能有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味道,且其处于一个动荡激情的时代,也不以周全系统见长。然而正因思想的空前解放,近代国人在文化方面的创获,远比我们已经认知的更多、更大。
钱穆曾观察到,康有为同时的“师友交游,言考据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谭复生,皆可谓横扫无前,目无古人”。他们正像国强兄看到的那样自己否定自己:“廖氏之考据,廖氏已自推翻之;谭氏之持论,谭氏亦自违抗之。”而康有为“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钱先生从这些人“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迄于灭尽”看到“三百年来学术,至是已告一结束”。既然中国学术的状况已如“扫地赤立”,则“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
不过,韩愈早就说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天崩地裂之时,复虑及根本,则为学易变,似乎也是常态,盖其不得不一步步挣扎着游离出原有学养之束缚也。廖平对此是上升到意识层面的,主张“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他得高寿,故平生学凡六变,直至天人之际。谭嗣同英年早逝,其学变不及让人多睹。然据梁启超言,他也是少年所学,“三十以后悉弃去”,转而究心西学。曾极推耶稣教,“而不知有佛,又不知有孔子”。到与康有为相见,则对其创新之儒学大服。碰到金陵居士杨文会,又转向佛学,所得日益精深。这里显然也可见一个旋学旋弃、旋弃旋学的过程,若谭氏能享寿,正不知还有多少变化。
且不论钱先生对廖、谭、康言论之自我“矛盾冲突”的评论,他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他们那“横扫无前,目无古人”的共同倾向,其实也就是在重新思考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当时人和后人,恐怕都对他们那些根本性反思有所忽视,甚至视而不见。从创造的一面看,不古不今和不中不西,不必就是缺陷。假如我们放弃那些系统的先入之见,不以中国传统或近代西方的观念体系为预设衡量标准,直接进入他们有时可能相对直观的思想世界,平心观察,自可随处看到不少关于人生社会基本问题的睿见。发现和整合这些见解当然并非易事,我们自己若真能先从容而且包容,把各种表现得“碎散”的观念“串起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作者曾说:“在一个没有政治学的时代里,史学曾培植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因此,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精神上与史学靠得很近。”这多少可以看作夫子自道,我们在书中常可看到作者自身的感慨。或许,钱穆所谓“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正类国强兄之有意收拾那一地碎散的文辞。不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得到多大程度的再现,他们都已经因此书的写作和阅读而进入我们的思虑;也许就是在此意义之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都成了当代史。
(本文原题《 收拾一地碎散的文辞——评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初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1日,收入《变中前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掠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