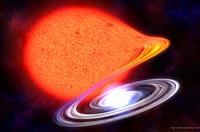
读读前辈大学者日记,不仅学术史或许可以重写,没准儿还能偷师学艺,从书目、方法和兴趣上学到很多东西。
读杨联陞日记,当然是为了了解学术史。不过,往往也被里面一些学界轶闻、名人趣事所吸引。里面故事很多,很多人也看过,如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先生,但重点应是看“人”。
当年剑桥的杨联陞家是个学术大码头,他那儿来来往往的人,当然主要是学者,通过他们来看看学术史,还有美国的中国学界的一些情况,也可以看看学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彼此关系。
现在的哈佛教授们生活太“苦”了,被全世界的学者所关注,不得不成天飞来飞去,到处演讲,忙于会议。可是,杨联陞那个时代,学术没那么全球化、国际化,除了上课,教授们没有那么忙碌。
杨联陞就总是宅在哈佛,倒是可以天天吃好的玩好的,他也忙于教课,忙于写作,但在日记里看,好像另外有三件事儿,更像是他生活重心。
一是唱戏,余英时先生说,唱戏大概是杨先生最顶尖的业余爱好,他唱老生戏的水平极高,是可以灌唱片的。
第二是打麻将和下围棋。麻将经常打,围棋下得不错,他和当时很多中国学者都下过棋,也和日本学者甚至留学生下棋。1957年他到日本访问,日记里还记载了去日本棋院京都支部,和京都大学的一些名教授下棋,其中,有中国历史教授贝塚茂树(二段)、科学史教授薮内清(初段),而梵文教授足利淳(三段)最强。实际上,作为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先生也有很高的围棋水准,不仅与林海峰、王铭琬等围棋超一流有交往,也和沈君山、金庸这些业余围棋界热心人有很多交往。
第三是吃饭,他隔三差五记录自己吃了什么菜,要么是下馆子,要么自己在家做。杨先生日记上记的菜,看起来都挺不错,他那时候常常请客吃饭,来的都是现在想起来就很著名的学者,像高友工来,还会亲自下厨。要是小辈来了,也会做个三明治便餐招待。
读他的日记,看到好多有意思的事儿,也看到好多过去不知道的事儿。比如章太炎的儿子章子杭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据他说,是兴趣广博而肤浅;又比如日记里面还记有老舍和曹禺在美东的情况,如1946年老舍和曹禺在哈佛曾经有演讲,曹禺有英国风格,而老舍讲得清晰,但喉音太重,有些资料也许现代文学研究者还没有用到过。
最好玩儿的人,应该是何炳棣,杨联陞日记里面记了他好多事情,比如他曾为当选中研院院士紧张活动,比如他得到研究奖章后的炫耀,比如他邀请杨联陞去芝加哥大学任教时那段“煮酒论英雄”故事,读来都很有趣。
何先生做人,那倒真是豪气干云,绝不扭捏小气,日记里有这么一件小事情,1964年6月何炳棣到剑桥镇,住在一个老太太家,“房租每日三元,(何)自增为四元”,然后自豪地向杨联陞夸耀说,芝加哥大学为他特别“加薪四千五”,这真是个活脱脱的何炳棣!
另外,里面也有不少当年访问哈佛的朋友的轶事,如邢义田、葛剑雄等,在杨先生日记里,都有他们的名字,也有他们的议论,比如1976年邢义田兄与杨联陞关于罗马钱币和汉五铢钱的谈话,1986年葛剑雄与杨联陞谈陈寅恪诗和统一分裂问题等等,看日记就是这些特别好玩。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学术状况,特别是华裔学者在西方学界的活动和处境,日记里面提到好多人,前辈学者像胡适、萧公权等;同辈学者像刘子健、何炳棣等;到访哈佛的学者如李济、钱穆等;学生一辈如张光直、余英时等。记录了很多与东西方有关东亚和中国学术史,身在异国的华裔学者的家国情感,还有西方中国学界学术变化背后的思想背景等话题。
毕竟身在他乡,虽然也有“夫子”,但华裔学者心情可能多少还是有点儿压抑,这从杨联陞的诗里看得最清楚。
1963年7月他过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四十九岁初度》,里面有两句“负笈谁期留异国,执鞭聊用解嘲诽”,两年后的7月,他又有一首绝句《感时》,说到“书生海外终何补,未耀圆颅鬓已霜”。虽然生活安定,免于国内反右、饥荒、“四清”和“文革”的一波又一波折腾,但是总觉得有点儿寄人篱下。
不光是他,萧公权也一样,1976年2月杨联陞的日记里面,有年近八十的萧公权寄来的一首七律《兀坐》,最后两句是“结伴还乡天倘许,今生已矣卜他生”。杨联陞读后,不禁潸然泪下,日记里说,他拿起电话向余英时先生谈及此事,不禁再一次老泪纵横。
那个时代的美国学界,哪怕是东亚研究领域,华人学者其实多数也是很压抑的,像何炳棣那样的人毕竟少。后来刘子健、杨联陞精神出毛病,恐怕就和这种压抑的心境有一定关系。日记里面,杨联陞自己记录下来的病中困境,简直不忍卒读。
说起来,他还算是顺利的,但也不免受气和怄气,毕竟人在边缘。比如,他日记里有时写到费正清,说他用欺骗手段弄卢芳的书,“而卢芳不之信,虽五尺童子,亦不可欺也”,有时又写到费正清这个人很厉害,耍权威而且有手腕,为了抬高史华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称渠为佛教史专家,又称渠学力过于赖肖尔”。
其实,费正清虽然居高临下,但对杨联陞还算照顾和关爱,只是美国主流学者习惯性的傲慢,让习惯于谦退的华人学者,多少有些受不了,杨联陞曾经与哈燕社副社长白思达谈起费正清对《哈佛亚洲学报》有“甚不客气之讽刺”,不禁写道,“此人有时太尖刻,今已高高在上,而犹如此,虽本性难移,亦是气量不足”。相比起来,像黄仁宇那样,处处受压制,连教职都成问题,自然心里会更不舒畅。
当然话说回来,跟那个时代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在美国,教授生活还是很优越的。杨联陞的日记里面记载,1950年他作为助教授,薪水已经是5000美元;到1958年,杨联陞当了正教授,那年,哈佛的正教授是一万二到两万美元,副教授是八千到一万一美元,助教授是六千五到七千五美元,讲师也有五千五百美元。
日记里还记录了杨联陞和他周围学者的学术研究。其实,杨联陞不止是一个博学的汉学家,也是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家。何炳棣只是强调他“汉学家”的一面,其实并不完全对。
1966年他对何炳棣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上发表有关清代汉化文章的看法,其实就意识到了“过于强调清朝之重视儒教”的问题,也注意到何有关清帝崇儒的史料疏漏,毕竟他有关清史的立场,不像何那么有固执的民族立场。
其实,杨先生的学术研究相当被动。他要上课,上课还特别认真;他又是个自负博学的人,不得不每个领域发言。因为戴密微说他是“年轻汉学家第一人”,费正清也抬举他,要做“第一人”就得什么都懂,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定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个领域的专门学问。
所以,他在写完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做过特别完整的专题研究,总是今天写这个书评,明天写那个书评,今天为了一个人的问题查资料,明天为了另一个人的问题查文献,或者忙于种种杂务。
日记里曾提到很多书目,当他写《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那一段时间,他会集中阅读有关道教的文献,为了助力赵元任编字典,也会多看有关语文语法的著作,但相当多的时间里,他的阅读好像非常凌乱。
虽然,这是一个博学的学者的习惯,也为此赢得“通人”之称,但毕竟害得他专门著述较少。是幸或不幸?我也不知道。所以,晚年的杨联陞对自己一生学问有这样的评语,“说与邻翁浑不解,通人本职是沟通”,这“沟通”二字,与后来人称他为“中国文化的媒介”,和他自己所说“接触面广可备顾问”刚好吻合。
1965年,即将回哈佛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写了一首七绝给杨联陞,其中后两句说,“如来升座天花坠,迦叶当年解笑时”。虽然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客气和赞扬,不过作为老师,博学多识的杨联陞,确实常能给人很好的教诲和建议,即使在日记中,也常常能读到一些益人神智的见解。
1967年8月,杨联陞和余英时先生谈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都觉得王国维用功不过二十年,但“出手即高”,为什么?日记里面记载,余英时先生说了一句话,是“似高手下棋无废子”,杨联陞大为赞赏,说“此喻甚佳”,因为这点出了王国维学术上“用力得当”。这些话就好像度人金针,教你怎么做学问。
本文转自“历史研习社”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