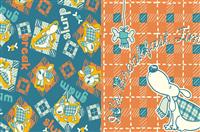
研究历史习惯上特别注重事件的开端,十六世纪利玛窦进入中国后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无论怎样深入地考察研究,都不为过。但是学术界对后续发展的关注显然缺位,到了乾隆年间,礼仪之争的冲撞,在交往上带来了寒冬。英俄美加入早期海洋帝国的竞争行列,大清对外多边关系变得复杂。商贸和传教关系的后面是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教派形成错综纠葛的网络。在北京俄罗斯东正教士与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耶稣会士之间的来往,成为大棋局中的卒子。 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更能显示做为文化中介的传教士如何迎头应对挑战,给学者提供线索来评价早期的对话模式是否有复制性 。
耶稣会士在早期中俄关系上扮演了一些重要的角色,张诚 (Jean-Francois Gerbillon)与徐日升(Tomas Pereira) 担任大清使团在尼布楚谈判时的拉丁文翻译,于康熙七年(1689)签订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国际条约,是外交史上的大事。进入十七世纪后,由于礼仪之争导致的天主教被禁,耶稣会士在北京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可是沙皇政府仍非常看重耶稣会士做为窥探清帝国的情报信源,同时加紧汲取耶稣会士的经验来建设驻北京的东正教传道团。
费奥多西. 斯莫尔哲夫斯基所著之《 在华耶稣会士记述》(1) 就是这段时间东正教士与耶稣会士频繁往来,留下的一份纪录,成为了解当时耶稣会士的处境 以及清帝国对国防外患警惕的重要参考文献。
欧洲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新教兴起,后来天主教以耶稣会带头自身改革,整顿纪律,向外四处传教,办学传播科学知识,是当时最先进的学府,吸引了不少贵族子弟,影响力渗入波兰及乌克兰, 对俄罗斯东正教造成压力。沙皇彼得大帝在1720年废除了原来的东正教的牧首制,直接由政府设立的“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来管辖教务,教会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早期俄罗斯来华商队就有所谓的“出使喇嘛”(2),后来派遣到外地的教士听命于宗教会议以及俄罗斯的外交部。有鉴于教士受过正规教育, 有相当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采集的信息比较可靠,彼得大帝早有设置常驻北京的东正教教士来搜集清帝国的情报的打算。雅克萨战役 之后,受降来京的俄罗斯人(统称阿尔巴津人)中有一名神甫,请愿要求有个崇拜祈祷的场所,康熙帝应允,赐 关帝庙一座来安置所携带的圣尼古拉圣像。这位神父过世后,俄方有意派遣继任人,不久后,中俄恰克图条约(1727年)签定,做了有关派遣教士的制度化安排:俄罗斯传道团由一名修士大司祭带领三名修士司祭以及六名学生组成,十年轮换,被安置在东江米巷的南馆,馆内有清政府为了接待俄罗斯教士仿天主教堂兴建的奉献节教堂,由理藩院管理,每月发放口粮及银两。此时原来的圣尼古拉教堂被并入南馆。
十八世纪中期,沙皇政府急于得到黑龙江航行权,来扩大与太平洋到美洲的贸易,分配俄罗斯传教团的任务是:与北京的耶稣会士交往,来了解清帝国的动态。还特别交代,避免谈宗教,尤其是涉及礼仪之争的话题。东正教传教团宗教服务范围限于俄罗斯馆内的商队及在京的阿尔巴津人。
费奥多西。斯莫尔哲夫斯基是东正教第四届传教团的修士司祭,他曾在波兰及乌克兰的耶稣会办的学校学习,通晓拉丁文,懂得和耶稣会士打交道。他于1745年来到北京,居京十年, 三十五岁时回国,三年后在乌克兰的一家修道院于过世。他留下的一份记载耶稣会士日常生活的观察报告手稿,被第十届传道团随行的商务专员吉姆科夫斯基(Egor Timkovskii)在伊尔库茨克获得,交给了“西伯利亚先驱 报”(Sibirskii Vestnik) 的发行人斯帕斯基 (Grigorii Spasskii) ,经过编辑处理,删去文中有关传教团内部行为不端的丑闻, 其余在1822年发表 。
斯莫尔哲夫斯基的叙述反映出他的观察能力和判断力,写实性很强,少有加油添酱的主观臆测,但是在雍正继位一节上,他还是记录了康熙原来要传位于十四子,雍正作为第四子,篡改遗诏而登基的传说。他到北京时,离康熙去世已有二十多年,耶稣会士还言之凿凿的延续了这个阴谋论。
从利玛窦明末年进京以来,几代耶稣会士,已经摸索出一套适应中土环境的套路,任职宫廷有画师、乐师、钟表师、天文数学等专业;穿着官服,出门顶戴、随从一项不缺。 他们修建教堂,组建文化班子,有翻译、聘用语言教师、还有宣传道理的宣道者,靠着《邸报》来了解朝廷政策。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不张扬,有尊严,有规律。相比之下,东正教还被视为“行教番僧”,形象不佳,物质生活不像耶稣会那么舒适。 东正教士们从耶稣会士那儿学到不少窍门,例如起个儒雅的中国名字,延聘私人的语文教师,整顿南馆外观,还有带来会修理钟表之类有一技之长的团员来受到尊重。这群人 在生活上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习惯时,如何保持外来宗教的特征,斯莫尔哲夫斯基做了些比较:耶稣会士入乡随俗相当灵活,东正教士却不能改变穿着黑僧袍,在北京当地人眼中还是把他们归类为喇嘛。东正教士也有随和的地方,例如,他们不在意接受原来的关帝庙做教堂,这在耶稣会士是无法接受的。 在不谈宗教的指令下,斯莫尔哲夫斯基的报告中只字不提宗教精神文化,反映出世俗政权如何引导文化交流。
耶稣会士在十八世纪中叶处于内外交困十分严峻的状态。从康熙朝的重用,经过雍正禁教,到乾隆年间被监视,耶稣会士的日子很不好过。同时压力来自耶稣会本身,多年树敌过多,西班牙、法国等国下了逐客令, 教廷在1771年干脆解散了这个修会。乾隆13年 (1747)清廷加大禁教的力度,处死了在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一名传教士,监禁另外四名。北京的耶稣会士,战战兢兢,随时准备大难临头。监视他们的有九门提督和海淀守备,在这些警卫武官之上,还有首席军机訥亲 (文中称“訥公“)。这位清朝开国元勋之孙领命为经略大臣出战金川,与云贵总督张廣泗不和,无功而返,被赐死,记载多与正史吻合。 耶稣会士和东正教士之间频繁往来,曾受到警告。乾隆帝对外界的兴趣虽远低于他的祖父康熙,但他对海疆的安宁有相当强的忧患意识。来自斯洛文尼亚, 任宫廷乐师的鲁国贤(Johnn Walter 1708-1759) 就曾对斯莫尔哲夫斯基说过,“他们(指清政府)对我们船舰的警惕比对传教更有过之,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俄罗斯。”
同行即是亲家也是冤家,东正教和耶稣会士往来的纪录,反映出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耶稣会士虽然帮过俄罗斯使节的忙,但是在尼布楚谈判条约时,一度因俄方不信任清方的耶稣会士翻译,转而要求使用蒙古人翻译,试行不通后,才勉强同意回到以拉丁文来交涉。俄罗斯最高宗教事务会议和枢密 院于1718年考虑把北京从伊尔库茨克分离,做为主教区, 推荐英诺肯提.库里奇斯基为第一任主教。俄方怀疑耶稣会士从中作梗,不愿见到级别高的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常驻北京,而未能进入中国。历届东正教传教团为首的是修士大司祭,一直到二十世纪辛丑条约后,才有主教出任。
斯莫尔哲夫斯基记载的译者是俄裔年轻学者Gregory Afinogenov。 英语译文不甚雅驯,好在书中提供原文对照,对谙悉俄文的研究者大有帮助。可惜译者对明清史认识不足,译文及注解张冠李戴,频添了些混乱。例如,斯莫尔哲夫斯基听说早期有位已懂中文、名叫“保禄”的耶稣会士来到广州,投身在一名佛僧门下当差,学到了佛经、仪式及法事,一日雄辩众僧,僧人们辨不过他,集体领洗皈依天主教,帮他传教。译者臆测这位“保禄”可能是明末西名为Paulus的徐光启 。只要稍有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徐光启不是耶稣会士,怎么可能在广东一座佛寺内卧底?斯莫尔哲夫斯基遇到一位名叫“保禄” (俄文原文 “павел Cy“)的中国人耶稣会士,听到他如何在福建买通了狱卒,获取到多明我会遇难传教士的遗骸。 这应该是死后葬于栅栏墓地的 “苏公” Paulus Su, 译者误译为 Paul Xu, 在索引内,又和徐光启同条并列。但总体来说,他根据其他学者提供的线索,找出《西伯利亚先驱报》中斯莫尔哲夫斯基的记载,翻译注释的贡献,值得称许。
这份史料受到学界的重视,堪比2010年在肇庆刘家族谱中发现刘承范著作的利玛窦传,同样印证及补充了早期耶稣会士在华的行迹。这类的史料可能还有很多有待发掘,将更丰富中西交流的研究。
后记
清朝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与东正教士的关系,常被美化为抱团取暖的兄弟情谊;事实上只能说是彼此利用, 各取所需. 耶稣会在欧洲全面被禁,俄罗斯与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之后,沙皇凯萨琳大帝顾虑教廷可能介入支持波兰境内的天主教徒反抗俄罗斯,为了保留一股可以抗衡教廷的力量,保护常与罗马做对的耶稣会。在俄帝国境内的耶稣会士尝试利用西伯利亚经过陆路打通来华之路,折腾了数年,徒劳无功。沙皇得知英国预备派通商特使来北京商讨贸易,急着想利用耶稣会教士挑拨离间散布谗言。 到了十九世纪初,在北京只剩下三位老弱病残的耶稣会士,不久相继去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目睹俄罗斯上层社会西欧化程度日深,以振兴东正教为国策,于是在1821年驱逐了耶稣会士,直到苏联解体后,耶稣会士才得以重返俄罗斯。而在耶稣会士于南京条约之后, 就回到了清帝国。
(1)Feodosii Smorzhevskii, Notes on the Jesuits in China,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regory Afinogenov,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Boston College, 2017.
(2)东正教传教团在清朝肩负了外交使命,其实葡萄牙也曾经考虑派遣教士作为过往信使,北上与清廷讨论驻广州贸易之事。“亦僧亦使”并非俄罗斯独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