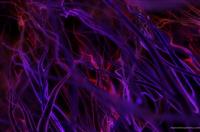【摘要】“5.12”四川汶川地震之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开始凸现。本文是对作为公民社会的内在属性的“公民性”进行简要地阐释。认为“公民性”是关怀社会整体福祉的态度,表现为共同体成员自身所拥有的“良好风尚”,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被集体性自我意识部分取代时的一种行为。
澄清“公民性”内涵,是阐释建构“公民社会”为什么应当成为我们值得追求之目标的理由。如学者所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一系列外在指标来观察,如相关的法制建设、社团的发展水平和生存环境、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个人对公益事业的参与等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检验它的内在属性,这就是civility,也可译为“公民品格”、“公民属性”或“公民精神”等等。这里将其直译为“公民性”。按美国学者希尔斯的说法,所谓“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就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行为体现公民性(civility)的社会”。根据希尔斯的论证,从三个方面对“公民性”做概括理解。①
“公民性”的关怀视域不是某一局部,它是超越阶级、党派、地域、血缘群族、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等等的界限,而关怀整体社会福祉的一种态度。所以,公民性是具有同时涵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地区或集团性(parochial)和“整体性”(holistic)三种要素的特质。它以实现整体性的福祉和较大的利益为依归。这种关怀的视域,不在于共同体规模的大小、人口数量以及内部种族的异质性,而在于强调对多样性包容的层次究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在一个固定的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群体或派别之间,产生不同和差别是必然的。面对这些差异如何行为?进一步深究,实施这些行为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它具有哪些特质和表现,就是“公民性”所涵盖的内容。
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精神和民族秉性,这是该共同体之所以可以区别于其它共同体的要害所在。现代社会学的鼻祖之一的涂尔干(Emile Durkheim)把它称之为“社会力”(Social force)。②并认为,虽然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属性是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但它本身却内含着极大的能量,有什么样性质的“社会力”,就会呈现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进而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在这其中以“孝道”为基础的家庭伦理是中国的“社会力”表现,于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就会倡导“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并此外推,从“修身”、“齐家”、“治国”,一直到“平天下”,建构出一整套价值准则。③而在西方社会,起码自罗马帝国以来,就逐渐地形成了一套以法律(特别是其民法体系)为治世基础的习惯,在其背后则受一套超越的信仰所支撑,是谓“高级法”。④因此,学术界把具有“精神”品性的东西,称之为“看不见的实在”(invisible reality),也有学者用“气质”(ethos)一词予以表征。⑤
这里所谈的“公民性”也同样具有这种“看不见之实在”的属性,它也必须借助于其它的载体才能得以展现,而“公民性”与其它各种类型的“社会力”不同的内在气质,就在于起码在自己生存的共同体范围内,实现公民之间的“充分尊重”。这样的“内在气质”要求任何一位公民,看待世界的眼界应当是多元的,不以某一固定的框架作为唯一准则去删改世界,也不仅仅强调一种局部意志和利益而强求其它局部跟随改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希尔斯才说:“公民性”之特质之所以一般地被解释为公民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意味着礼貌、谈吐优雅、谦逊、尊重他人、自我克制、绅士风度、文雅、高尚、良好的风尚、斯文”等等,就是因为在这些用词和行为的背后,其更深的含义是摒弃“非违法的自我放纵”,“顾及他人的感受,特别是顾及他们要求受到尊重的欲望”。这样,承认他人至少具有与自己同等的尊严,而决不贬低他人的尊严,就成为衡量“公民性”的基础原则和最后底线。
“公民性”表现为共同体成员自身所拥有的“良好风尚”
如上所述,内在气质之类的“看不见的实在”必须经由物质或行为载体才能得以展现,那么,公民行为中体现出来的那些“良好风尚”就成为“公民性”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与“公民性”的抽象属性不同,这些“良好风尚”则是实实在在可感可触可闻可见的,而且随时随地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高丙中把“公民性”所体现出来的“良好风尚”具体概括为7项内容:礼貌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避免和排斥强制性暴力;对他人的容忍和宽容的心态;对陌生人所持有的同情心;独立自治的自愿精神;平等地尊重共同体中任何成员;对超出熟人世界以外之共同体抽象符号的认同。⑥
高丙中对这7项内容已做过逐条阐述,此处不赘,这里所要稍加解释的是上述概括中出现的“陌生人”和“熟人世界”这样一种范畴。一般而言,尤其在中国文化环境之下,人们对待自己的所熟悉的亲属、朋友、师友等等,往往可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爱、理解、尊重和宽容,但对于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陌生人”则可能呈现另外的一种行为。上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美德要素,会伴随著陌生度加深而呈下降趋向。这种状态称之为“群族伦理”,而能称得上“公民性”的品质一定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就是说,无论对方是什么人,一方面,我们都以同样的一套原则相处;另一方面,别人也同样以这样的原则与你相处,于是在陌生人之间就达成了某种行为的共识,这种共识之下任何一方在接触对方之前,就可能判断出他将以怎样的方式与自己相处。显然,这种彼此行为的“可预期性”就将成为彼此信任的基础。所以有学者定义说:“‘公民性’的规范圈出一套行为准则的范围,以便于公民可以对陌生人产生正确的预期”。⑦而上述规定的7个方面,就是被划定的“公民性”的基本范围。假如在共同体之中人人都认同这样一套行为标准,那么就会由此形成一种相互默会的、毋庸论证的“共同感知”和“公共话语”系统。这是公民社会超越熟人世界的必要条件。
“公民性”是自我意识被集体性自我意识(collective self - consciousness)部分取代时的一种行为
“集体性自我意识是将自我视为集体之一部分的认知状态,它内涵着一种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或地区与集团利益之上的范围。”在这里,希尔斯的意思是说,当“公民性”被内化为每一个成员的自觉价值的时候,就会生成某种被共同体成员所普遍认同的“集体心性”。这样自我个体德性的规范,就变成普遍的行为准则,“公民社会”于是生成。当一群公民成员自觉遵从共同认可的良好风尚并平等相处时,他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把对方视为具有同等尊严的公民,这就意味着将其他人,包括属于不同党派、宗教团体和种族群体,都应被视为同一集体的成员,不因他们在“政见”、“信仰”或“习俗”的不同而加以排斥。特别重要的是,在这里,“公民性”是所有共同体成员,包含超出个人或社区以外的、以至于可囊括全体共同体成员的范围,包括那些并不相识、彼此陌生的(即“不在场的”),甚至永世未必相见的共同体成员,共同建立起来的一套大家分享其权力与义务的“价值符号的空间”。而有资格共同分享价值的对象应当“包括自己的敌人”。“公民性不仅是良好的风尚与和解的语调,它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模式。这种模式预设政敌亦是同一社会的成员、共享同样的集体自我意识。”把他们也“视为同一集体的成员,亦即同一社会的成员,即使他们属于不同的政党、宗教团体或种族群体。”“这一意义上的公民性包含了对政敌以及盟友福祉的关切”。
作为生活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政治认知传统中的中国人,理解“尊重敌人”无疑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公民意识”所强调的“集体性自我意识”并不等同于中国人常说的“集体主义”,因为在“公民意识”的本质中没有“阶级斗争”所释放出来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怨恨;其次,“公民意识”的本质中注重“集体性自我意识”,并不构成对个人意识的压抑和扼杀,而是通过预期到别人同样的感受而使自我行为自觉地受到克制,这种限制不是来自外力的约束,而是出于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理推演;再次、“公民意识”的本质中内生着“当社会之一部分可能从某一特定事件或政策中得到好处时,任何设想或试图减轻另一部分可能招致的损失的行动都是一种实质性公民品行的行动”,由此形成谦让、妥协、后退行为的可能性基础。通过上述三点,个人主义、地区或集团性和“整体性”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平衡就能实现。
综上所述,由于“公民性”不是“权力欲”,所以它是“非暴力”的;由于它的志趣不在于升值,因此它是“非营利”的;由于它的价值底蕴出于“使命”之中,因此它是“志愿性”的;由于它“视人如己”,所以才能对“异己”给与宽容。一个公民社会就是其成员都具备公民美德的社会;这样的美德包涵了诸如“良知”、“独立”、“志愿”、“慈善”、“互助”、“合作”、“责任”等等内容;而当这些公民美德内化为共同体成员志愿遵循的价值准则和日常行为时,这就标志着“公民社会”的成立;而“大爱无疆”和“彼此宽容”则又是其中最为抽象、也最为深刻的终极内涵。
在这里,引用徐永光在谈及慈善事业和慈善产品之性质时所给出的具体解说,在一定意义上,他的意思表达了“公民性”抽象理念的核心内涵:“做善事不光可以帮助别人,还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公益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能够拨亮人们心灵的明灯,推动人和人之间建立平等、互助、互信、互利的社会关系,这是和谐社会建设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发展慈善事业,就是让中国人更加接近‘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的,就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慈善心、公德心、公益心、博爱心。…… 参与公益事业,无论是捐款或是当志愿者都是助人自助,有私奉献;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施比受更有福。这是公益事业的市场需求。了解这种需求,以需求为导向来设计项目,推广营销,就找到了非营利组织的经营之道。”⑧虽然他针对的是慈善事业,但这其中韵律则留藏着“公民性”的久久芳香。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反思“现代性”(Modernity)就成为一个严峻的国际性课题。学者们注意到,自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中心主义意识日益增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良知,在人类整体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处于被关注的边缘,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明显地趋于淡化,物质利益的获取成为压倒一切的“第一主题”。个人被从家庭、社群中剥离出来,而以专业和利益为原则被非有机地重新组织化,以至于个人在社群中角色失去了自然本性和连续性,以至于道德贬值、信念消逝、价值危机、世风退败,其突出的表征就是占有欲望的无限扩张、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冷漠功利的人际关系等等。显然,这些征兆对完整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如韦伯曾以其少有的激烈方式予以诅咒的那样:“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人类所理解的“解放”,实际上是被再一次囚禁于“合理化铁笼”。⑨一句“德性能值几个钱?”的亢奋质疑,其实已全然揭示出了“现代性”狂躁的逻辑本性。
当然,“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否认物质进步对人类生命的积极意义显然是一种愚昧,但是“现代性”悖论的深刻性则在于: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另一方面,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困;一方面,人的界域的迅速扩张,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的急剧恶化;从而使“丰满的人”渐变为“逐利的躯壳”。用思想大师们的概括就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霸占,或者是“工程主义取向”对“道德主义取向”的吞噬。⑩在某种角度上说,所谓反思“现代性”其实也就是试图对人类“存在意义”(Being)的精神康复和灵魂拯救。
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反思‘现代性’”和“倡导公民社会的建构”这两股社会思潮,为什么会在时间维度上几乎是同时兴起?我们也就无法说清“5·12”四川汶川地震后的捐赠“井喷”究竟何以可能使我们感动?所以说,“5·12”的中国公民大行动,已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暗示:建构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或许是缓解“现代性”痹症的一剂良方,因为被公民性所激发的是一种人之为人的终极之善,
而公民性所提供的则是滋养精神生命的丰富美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Edward Shils, The Virtue of Civility: Selected Essays on Liberalism, Tradition, and Civil Society. Steven Grosby,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7. 引文见: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李强译,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6~305页。文中,李强把civil society 译为“市民社会”,把civility 译为“市民风范”,这一译法本身没有问题。为使本文的概念一致起来,这里统一将civil society 译为“公民社会”,而根据具体的上下文,把civility 译为“公民性”,但其概念的内涵不变。
②参阅: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参阅: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2年。
④参阅: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⑤所谓“精神”是不直接具有物质属性的,我们不能说出“精神”是圆的还是方的,是红的还是黑的,但正因如此,“精神”的展现必须通过物质或行为的途径来间接地实现。比如,见义勇为是一种行为,通过这种行为,我们才能看到所谓“大公无私”的“精神”。
⑥高丙中、袁瑞军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⑦Richard C. Sinopoli, Thick - Skinned Liberalism: Redefining Civil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5,89 (3) : 612.转引自:高丙中《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状态——基于“公民性”的评价》,《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⑧徐永光:“中国民间组织治理和发展五题”,《环球慈善》,2008年10月。
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3页。
⑩Benjamin I. Schwartz,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 208-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