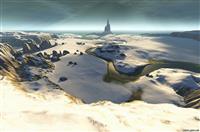灵魂如果缺乏丰富的形象
它就会饥渴而死
——千叶
中国美术学院是人才辈出的一座学府,能到这里来介绍自己的想法实是一种荣幸,为此我要感谢许江院长,吴美纯女士,高士明,高天民等朋友。
今天我想讲一个大题目:科学的思考方式和我们平常的所思所感是否相容?谁更基本?谁更正确?等等。当然我不指望三言两语把这个大题目的方方面面都讲清楚,我想的是提出一条多少有点新意的思路,作为交流的一个起点,希望诸位觉得还有一点意思,同时也希望听到诸位的批评。
近几百年来,科学已经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宇宙图景,我们的宇宙是从大爆炸产生的,后来有了星系,有了地球,地球上产生了生命,或者陨石从太空中为地球送来了生命,生物不断进化,基因越来越复杂,最后产生了人类。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再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怎么在几百万年间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从大爆炸到基因到人的心灵,虽然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澄清,但大致轮廓已经勾画出来。科学带来了很多益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有些是物质层面的威胁,原子弹、克隆人、臭氧层空洞,有些是思想层面的困惑:既然生命、人性等等都是从基本粒子发展来的,似乎从理论上就可以一步一步还原到起点,自由意志、道德要求、爱情和友谊,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可以而且应该用粒子的运动来解释,真实的世界是科学描述的那个样子,我们平常看到的世界和幻象差不多。我记得爱丁顿说过,我们看到的桌子只是幻象,真实存在的是很多个原子,看上去桌面光滑致密,但真实的桌子却凹凸不平,充满空隙。现在把这一类看法称作科学主义立场。
把努力向善还原为某种腺体的分泌,把爱情理解为一些亚原子粒子的运动,会让敏感的心灵感到不舒服。而且不止于此。即使乐于在理论上坚持这种还原,在实际生活中仍免不了要谈论意愿、善恶、爱恨,免不了这样看待人和事。为了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有人主张,科学并不是真理,科学的身份和希腊神话、圣经、阴阳五行、几内亚的传说的身份是一样的,只是一种看法,只是对世界的一种可能的解释。这样一说,我们似乎就可以逃脱科学主义的罗网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明显是错的。科学不是和神话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观念体系〕,在一种简单纯朴的意义上,科学是真理而神话不是真理,而这恰恰是因为,科学为真和假设立了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单单应用到非科学学说上的,科学体系内部的论断同样要接受这些标准的检测。据圣经文本推算,人类有七千年历史,现在我们都认为这是错的,科学证明人类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当然,具体的数字可能错,可能不是三百万年而是三百二十万年,但这与圣经的错法不一样:科学体系有办法提供更正确的回答而圣经体系没有办法提供更正确的回答。我觉得,把科学说成是和神话并列的某一种观念体系,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的本质,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对科学主义的迎战,科学主义提出的挑战要严厉得多。把问题轻描淡写一番无法让我们当真摆脱困境,甚至也可能使我们更容易陷入科学主义的罗网。
那么,也许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都错了,或至少都是片面的,我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官老爷可以这样说,哲学家是不可以这样说话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入手来考虑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想从视觉的生物学/心理学开头,当然,这个入手点是偶然的。科学家现在对视觉的生理机制已有相当了解,第一步是光子落在视网膜上,光子告知刺激野中的某个部分的亮度和某些波长信息,但不告知那是个物体、它如何运动,更不告知那是什么物体,具有何种意义。神经把视网膜接到的信息传到大脑,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电-化学反应实现的。从视网膜到脑皮层就是这样一些单调的信号,然而,我们却看到一幅幅图画,看到一个五光十色、生生不息的世界。这幅图画画在哪里呢?它不会是画在神经突触之间,然而大脑皮层上也并没有屏幕。
我就勾画这么一个大轮廓,不敢多说。你们的视觉比我敏锐、高雅,还可能有人钻研过感觉生理学、心理学,我说多了会露马脚,不如赶紧跳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和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
这个一般性的结论是:看是一个建构过程,我们看到的世界图画是建构起来的。我们有时说,我们的认识是对世界的反映,那么,那是一种建构性的反映,我们说一种理论反映了时代精神,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了一种生活理想,都是在有所建构的意义上说的。像镜子那样在同一个平面上镜映,是反映的一种极限情形,虽然可以用它作起步的例子,但不能限于用这个例子来理解“反映”这个概念。
我的一般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建构起来的,那么,实在本来是什么样子的?克里克――他是最早发现基因的著名生理学家之一-―正是在讨论了视觉的建构过程之后断言:“你看到的东西并不真正存在,而是你的大脑认为它存在。”那什么东西真正存在呢?我们看见西施走过来,翩若惊鸿,但那只是我们的大脑认为有个西施,有个美人,“真正存在”的是一堆电子,走过来的,不,也没有所谓走,移动过来的,是一堆电子,一堆夸克。这种说法有点别扭,但似乎也满有道理。在我们眼里,西施是个美人,但我们不能保证在猴子眼里她也是个美人,我甚至敢肯定在蝙蝠眼里她不是美人。那西施本身是什么样子?一种回答是:西施本身谈不上样子不样子,她只在观看者的眼睛里有样子。我们固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本来无一物,但至少可以说:实在本来无样子。一种眼睛有一种眼睛的建构方式,我看见西施是这个样子,蝙蝠眼中的西施却是另一个样子,X光照出来的西施又是一个样子。另一种回答是:实在本身就是物理学描画的那个样子,那是世界本质的样子,它决定蝙蝠会怎样看待实在,决定人怎样看待实在,但反过来,蝙蝠怎么看,人怎么看,都不影响实在本质的样子。在这个意义上,蝙蝠的看法,人的看法或意识,都只是些副现象。
对不熟悉“副现象”这个用语的朋友,我这里插一个简单的比喻作个说明。对于一台连着显示器的电脑来说,本质的东西是电脑里的那些电子活动,只要你在操作,即使显示器关着,电脑里面那些活动还在进行,这些活动决定屏幕上的影像,屏幕上的影像却丝毫不影响背后的电子活动,这些影像就是副现象。
我刚才说,西施在我们眼中是个美人,这话说得太草率了,很可能我认为她是美人你却认为她不是,你眼中的西施和我眼中的西施可能很不一样,甚至我此时所见和彼时所见也不一样。现在我的又一个问题是:既然建构会引起这么多纷争,我们为什么不就西施本来的样子来看待她,这么说吧,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她看作一堆原子?
我知道诸位都具有健全的理智和良好的教养,难免觉得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荒唐。但这些不是我本来要提的问题,这些是尝试解答我原本疑惑的辅助线,我把问题向各个方向延伸,想看看抻到哪里问题就变得荒唐不可解了,反过来也许可以借此看出原本那个问题是以哪些基本理解为条件的。有些初学哲学的人正好把哲学的旨趣领会反了,他们也向某个方向抻一个问题,然后把抻到最极端的那个问题及其不可解答性当作真正的哲学问题及其“哲学上的答案”。
哲学,以及从哲学发展出来的科学,本来是为了寻求真理,从看似来到真正是,来到事物的真相。但最后我们自以为获得真理的时候,无论我们信仰上帝的善意还是信仰进化论,都会有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不沿着真理的路线前进,而要钻进一片到处都是迷途的丛林?罗素找到了一种比日常语言清楚百倍的逻辑语言,乔姆斯基发现了普遍语法,这时他们都该自问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我要问的是,我们的感觉为什么不停留在更基本的层面上,为什么不直接对现实作出反应?却要通过这么复杂的程序去建构一个西施的形象?建构总是可能出错的,不同的建构之间又会发生好多争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抻得很远了。什么叫直接对现实作出反应?像蝙蝠那样,像草履虫那样,像一个碳原子那样?在某种意义上,碳原子从来不会作出错误的反应,和谁结合不和谁结合,从来不出错,我们挑一个爱人,费了好多心机,结果还是弄错了。有人会指出:错误总是对有认识能力的生物才谈得上。蝙蝠是一种生物,但我们仍然很难说它对西施作出了正确的反应还是错误的反应,我们大概得说,它眼里没有西施,它是在对另一个层次的事物作出反应。一种成象方式正确不正确,谈论起来相当困难,因为我们通常是在一种成象方式之中谈论正确不正确的。当然不妨说,蝙蝠的成象方式正好能应付它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它像碳原子一样不会错。但我绝不是要用“适者生存”这样简单的成功观来定义真理。事情几乎相反:越低级的东西越容易生存。在进化的阶梯上,熊猫比蟑螂的地位高多了,但老听说熊猫濒临灭绝,从来没听说有人担心蟑螂绝种。
但不管低级高级,每一层次的生物,都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成象,在这个特定的成象水平上和现实打交道。我们人,在语词的水平上成象。这不止涉及我们怎样认识世界,这同样是在谈论我们怎样在世界中活动。现实在我们眼中以西施、溪流、日月这样的方式成象,这无非是说,我们对西施、溪流、日月作出反应,而不是对电子、分子之类的东西作出反应。
这里也许有必要提到一个哲学上的成见。不少哲学家把事情表述成这个样子,好像我们每次都是先看到先看一个亮点,再推论说是那是一颗星星,那是启明星,等等。实际上却不是那样,我们不是从最不可错的地方开始看,〔说启明星最容易错,说星星其次,说亮点最不容易出错,〕而是尽可能从最富有意义的层次上开始。我们首先看到启明星或星星,不能看成星星才看成亮点。如果你认识西施,那你“第一眼”就看到西施,而不是看到一个影子,然后看到人,看到女人,看到西施。
我们人在人心成象的层次上和世界打交道。我们当然也在其他层次上对事情发生反应,突然用强光来照射,瞳孔会收缩,在脚趾上滴一滴盐酸,脚趾会抽缩,但那好像不是我在反应,是大脚趾头自己在反应。我不想立刻卷入关于本能、随意肌和不随意肌等等的讨论,因为这类讨论也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例如“本能”这个概念就相当复杂:我的某些情绪可能是非常本能的,但那仍然是我在人的层次上的反应,和瞳孔收缩这种本能不一样。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较低的成象水平,如果我们没有继承草履虫对利和害的区分,没有继承老鹰对移动物体及其运动速度的判断,我们就不可能在语言的水平上成象。没有生物发展上亿年的建构,我就不会看见西施。但这个建构不是我建构的。西施走过来,我就看见西施,我们人就是在心灵的层次上看的,直接在心灵的层次上看。我刚才问到,世界图画是画在哪里的?它不是画在神经突触之间,也不是画在大脑皮层上,它就画在心灵上,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定义心灵的:心灵就是成象的所在,象在哪里,心灵就在哪里。〔如果西施有那个样子,我就可以拿我的眼里的西施和它对,当然,即使如此怎么个对法也还是挺难的。拿照片来对。象不在照片上,不在镜子里。〕
可以说,西施的象在你心灵的眼睛里。但这不意味着,只在我们眼中或心中才有西施的象,所以那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象不在我之中。在我之中哪里?我恰恰是在说,我的大脑皮层上没有一块屏幕。心灵不是像心脏那样的东西,可以裹在一个身体里,心灵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你我这样的生物存在、交往的方式,在这个层次上交往,西施以西施的面貌成象。与其说西施的象在我眼中,不如说西施的象在西施那里,但她只对心灵交往这样显象。真正的西施就是那样。我们会想到关于变形、显象等等的无数传说、故事、神话。也可以这么想,说到头来,山是山,水是水。
我们通常总是以某个特定的层次为参照谈论建构的,所以,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我们不宜把直接看见西施这个层次以下的事情叫作“建构”,只有在这个层次以上才有建构,比如建构一个理论,用考古材料重构一段历史,用事实重构一个案情,等等。刚才说,反映一般是通过建构的反映,这就是说,我们通过营造某些上层建构,例如建构一个理论,使某些看不见或看不清的东西得到反映。
较高层次的成象固然以较低层次的成象为基础,但想要从较高层次上去清楚地设想较低层次上的成象却是相当困难的。实际上我这里是在用悖论的方式说话,因为我们本来只在最高层次上清楚地成象,或用语义上行的方式来说,我们本来只把最高层次上的成象称作清楚的象。诸位现在来设想一下狗眼中的世界或猴子眼中的世界,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你给你的爱犬一块牛肉,它吃得很开心,它是喜欢牛肉吗?
你怎么知道它能分清牛肉还是猪肉?它眼里出现的是肉吗?肉和鱼是一类东西还是两类东西?请再想一想嗅觉和视觉的区别。人格外注重视觉,〔“明晰”等概念都和光、和视觉有关,〕而且还制作了各种我们自己很容易开关的器具,我们打开垃圾筒的盖子,用眼睛一看,知道里面没有肉,视觉是一种更加非此即彼的官能,一块肉要就在那儿要就不在那儿,我看着你拿开它,那它一下子就没有了。嗅觉却不是这样认识世界的,垃圾筒里的肉味逐渐散去,就好像一块肉逐渐变小直到最后消失似的。狗偏偏非常依赖嗅觉,这就让我们很难设想狗“眼中”的世界。
我们自己在互相理解的时候就没有这层困难,你看见了什么?肉,牛肉。当然,你没有说它的颜色、新鲜程度、位置等等。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只要我问,你就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描述困难是存在的,到这不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一种。“牛肉”这个词指牛肉,而不是肉类和鱼类的集合,这一点在常识看来是清楚的。〔可以对此发生疑问,引向私有语言之类的讨论,但今天我们不谈这个。〕人心有它格外难解的一面,也有它格外好解的一面,这是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水平上成象,上面已经说到,在语词的水平上成象。语词若要有意义,我们就得有感觉,纵深地感觉,像狗一样,像水螅一样去感觉。感觉从深处一直连到处在最高层的语词平面那里,到了语词平面,我们看清了,不再说我觉得如何如何,它就是如何如何了。对于人来说,现实在语词平面上成象,在语词平面上是其所是,因此,我们首要地在语词平面上分辨真伪。
到了语词这个水平,我们就清楚了。你惊叫一声,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屋里有条蛇,于是我就清楚了,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变得更清楚,当然,我可以继续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蛇,是不是毒蛇,有多长,是什么颜色。但我不能在“你说屋里有条蛇这话是什么意思”的意义上变得更加清楚。但是有条蛇从草丛爬过来,一只猴子惊叫起来,你却无法在这个意义上弄得清清楚楚。猴子看见的是蛇吗?还是看见“从地面上过来的危险物”?它有地面的概念吗?他的危险概念和我们的危险概念重合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这些,不过,这项工作是在语言以上水平进行的,是一种外部知识,而不是亚语词水平的感知。〔我们对机械运动有最确切的外部知识,对人心有直接的感知。〕但只要可能,我们总是首先通过感知去理解,如果行不通才寻求外部手段。
也许有人会想,通过一系列实验、概念调整、计算,我们最后还是理解了猴子的心理。这里大概对“理解”有点误解。理解和知道不同,我们可以通过极为繁杂的程序最后知道一个结论,但“理解”这个词却天然带有某种直接性、自然性。绕的圈子太多了,哪怕最终获得了结论,我们也有几分茫然。如果我们必须对环境多少有点理解才能在人的水平上有所作为,那么单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就必须对完形的象作出反应而不是对建构象的那些因素作出反应,因为把一切解构之后再进行重构太迂回了,我们即使知道是对的,也体会不到。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象不可能是副现象。我们无法脱离“想要”、“不高兴”这样的语词来描述人的行为。用完全亚心理的方式来写小说,不是不好,是无法做到的。当然,基于同样的道理,有时候作家会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解构的方式,我们会觉得理解起来挺别扭,而这正是他有意要制造的间离的陌生化效果。我们关于太阳已经积累的大量的知识,但太阳首先是大地上光和热的源泉,是天空的父亲。不这样看到太阳,整个世界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我说,我们首先求助于直接的理解,通过感知去理解,如果行不通才寻求外部手段。这个提法又和不少哲学家的成说相反,他们以为我们总是先把相遇者看作一个机械物,然后逐步去查证它是否有生命、有意识、有心灵,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以及心理学人类学的各种研究成果〔儿童和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等等〕相悖,我们一上来就尽可能把相遇者视作自己的同类,在证据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才逐步不得已把它视作具有较低成象水平的或根本不具有成象能力的东西。这一条,就是我上面说到过的从富有意义处成象那条原则的一个内容。
谁和动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把它们当作无生命的物体?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设想它们的成象方式。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较高的关照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较低的关照,我们固然想不清楚狗眼中的世界,但我们还是可以去设想,狗却完全无法设想我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亚里士多德说,心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切。心灵通过想像进入万物的存在。
柏拉图说,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清晰的世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我们也许可以降低一个层次来领会这个说法:对于我们人来说,达不到语词,就不够清楚,我们设想狗或蝙蝠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好像是影影绰绰的,像是个影子世界,像是个梦中世界。顺便说一句,我差不多认为,我们做梦的时候,就是回到了较低层次的感觉,越深的梦境就回到越低的层次,只不过这些感受仍然只能和我们的理性对照着呈现,我们只能用通常的成象方式来再现和保持梦境。
索绪尔说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混乱和模糊的,这话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直觉,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神话讲到从混沌到清楚的转化。从较高层次的成象着眼,较低层次的成象自然是不清楚的。人类沙文主义会说,我们眼中的象是客观的象,狗眼中的简直不成其为象。在一个很特定的意义上,在人的眼睛里头世界变得清楚了。但这个说法显然不能是说,狗或蝙蝠眼中的世界对他们是不清晰的。清晰不清晰,本来是相对于各自层次的最高成象水平而言的。狗有狗的清楚,哪里有食物,哪些危险正在临近,它比咱们清楚。动物之间也广泛交流,这种交流在他们自己听来也没什么不清楚的。
但若从人的眼界反观,狗和蝙蝠生活在影影绰绰的世界里。那么从哲学家、科学家的眼界反观,普通人不就是生活在影子里吗?这的确就是柏拉图的意思:与一种更高的成象对照,较低层次的形象是影影绰绰的。柏拉图的说法很有深意,不过我在一个重要之点上不能同意,那就是,我认为物理学的世界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象,一种技术性的成象,不具有我所说的成象的直接意义。这一点我马上要说到。〔即两段之后谈到的“超自然形象的系统语言”。〕
真相是说:无论你怎么看它它都是那个样子。然而,没有看,就没有样子。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主观的世界,无论主观客观,都要有这一“观”,我们是在这一观的水平上,在人的成象水平上,区分主观客观的。客观看到事物之所是,主观看到事物之看似。然而,是与看似处在同一层面上,而不是处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因此,我们,或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是与看似分清楚,每一次我们都要重新辨识。想想我们实际上是怎么发现错觉纠正错觉的。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时候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有时候不再只依赖看,而是用手去摸一摸,有时候把事物重新排列组合。当然,有时候还会通过分析、还原,但所谓分析-还原,不是退回到较低的成象水平上完事:不可能在较低的成象水平上解决较高成象水平上为真为假的争议。分析-还原是说在一个更高的成象水平上,例如在更加精密的逻辑的水平上,重新组织我们原来那种认识所依赖的原材料。
通过科学工作的系统努力,我们在这个更高的水平上发展出一套超自然形象的系统语言,从这套语言反过来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自然语言是模糊的,而且在一些有限的场合,可以依据这套更高层次的语言来评判我们自然理解的真和假。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就像狗的世界对狗并不模糊并不错误一样,泛泛地说我们的自然理解是模糊的或不真的或不够真实,那是没意义的话。而且,如上所论,我们是通过继承草履虫对利和害的区分,继承老鹰对移动物体及其运动速度的判断,才形成了对我们是自然的理解。同样的道理,没有自然理解,就不可能形成现代科学的技术性理解。
诸位是不是会指责我陷入了相对主义?我觉得我和标准的相对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一个表面上的不同点,还有一个真正的不同点。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都认为,真理是有条件的,如果再次用语义上行的方式来说就是,“真”只在某种类型的句子中才有意义。我想这一点是明显的。我们表面上的不同点是,我认为有条件的真理是真理,相对主义者认为有条件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了。我一向觉得相对主义者是些有强烈绝对主义倾向的人,像普罗塔哥拉那样主张“没有是,只有看似”,这种非此即彼的口气,一听就是绝对主义那一流的。但我们在这一点上只有表面的不同,对着半杯水说“只剩半杯了”或者说“还有半杯呢”,也许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是不是真理,也许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然而,最后还有一点实质上的不同:相对主义者认为有条件的真理就不是真理,因此他就懒得去研究某一类真理实际上是根据什么条件成其为真理的,而变换了哪些条件就不再成其为真理了,而对我说来,真理是重要的,有条件的真理一点都不减少其为真理的重要性,因此,我愿下很大功夫去探索这个真理那个真理的条件究竟是哪些。我把这看作实质的差别。我一向认为,单纯的看法,无论多么相反的看法,多么激烈的看法,――如果并不和做法连着――都无所谓,只有怎么做才是重要的,哪怕在哲学思考这种高度抽象的领域也是一样。
关于真,我是这样理解的,关于美、善等等,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人们有时问:美是事物本来的属性抑或是我们附加到事物之上的?按照现在的思路,我们会这样问:在何种成象水平上才谈得上美?说水螅觉得一种东西美另一种东西不美没什么意义。但在我们的成象水平上,美却不是后来附加到事物之上的,仿佛我们先看到一个干巴巴的事物,然后再判断它美或不美。固然,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我们可以甚至必须把美或不美先放到一边,就像外科医生临床的时候需要把乳房、心脏、大脑只当作一些生理组织来处理。这当然不是说,大脑先是一块物质,然后附加了思维的属性。维特根斯坦年轻时说:“善的本质和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这只能是说,在赤裸裸的事实层面上,善恶这样的概念是无效的,然而我们却不是从赤裸裸的事实层面开始来理解世界的,我们是从生活世界开始理解的,如果我们在分解世界的时候失去了善恶,那只能说明分解是会失去某种东西的,虽然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我们有时必须失去一些什么。
我拉拉杂杂说了这些,最后我想作个简短总结,再就刚开始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个回答。每种生物都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成象,亦即在这个特定的成象水平上活动。音乐、绘画、建筑,这些都是我们的成象方式,但最为典型的是语言,因此不妨说,人在语词的水平上成象,在这个水平上和世界打交道。到了语词这一层,世界变得清晰了。但不能因此说狗眼里的世界不清晰,不真,或不正确。比较人眼中的世界和狗眼中的世界哪个更真实没什么意义。只有在同一层次上才谈论真假。你看见金星我只看见亮点我当然总不出错。这引出几个主要推论:一,在同一层次上可以谈论真假,真理不是因人而异的。二,正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谈论对错,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发明一种办法,一劳永逸地消除所有错误,我们永远达不到一个只对不错的层次。三,人的眼界并不更正确也不更有效,但人有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在心灵的交往中,世界以最为丰富、精微的形象显象,相形之下,草履虫的世界实在是非常单调。我说显象,不止是谈论认知,生活在丰富多彩的形象之间,是说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可惜,人类现在利用自己独一无二的禀赋,反过来在自然界和人类文化世界危害丰富多彩的生活。
最后,对我一开始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个简短评论。
物理学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我的评论是,不同层次上的观念体系哪个都不提供唯一的真实,唯一的真实这话只在同一个层次上才有意义,只有在同一成象水平上才谈得上真相,以及真相与看似的冲突。我看到世界的真相并不排斥猎豹也看到世界的真相,虽然它眼中的世界和我大不一样;同样,上帝看到世界的真相并不排斥我看到的也是真相。物理学不提供唯一的真实,恰恰不是因为物理学只是和希腊神话并列的观念体系之一而已。不同层次也是可以沟通的,办法就是建构一个新的平面,把纵向的差异投影为横向的差异。当我们在同一平面上考察物理学和希腊神话,就可以判定一个是真一个不真。
物理学的世界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我的评论是,比较物理学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哪个更真实没什么意义,就像比较蝙蝠的世界和水螅的世界哪个更真实没什么意义。我们的确可以根据物理学的发现来判断我们某个自然理解是对是错,就像我们根据我们的同一性标准判断一条狗认错了主人,但这个判断对这条狗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生活在一个不同的认同系统中。自然理解中出现的困惑要在自然理解层面上解决。这并不排斥我们就某一点局部进行更高的形式化,进行建构,但是这部分形式化的工作必须在自然理解的框架中具有意义,而不是单纯从自己的形式体系中获取意义。
意识、善恶、美丑、自由意志,这些都只是一些副现象。我的评论是,人需要水和氧气才能生存,水和氧气没有人照样存在,在这个最简单的意义上,是世界影响意识而意识却不影响世界。然而,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成象水平上,事物才作为这种水平上的事物得到对待。在人的水平上,事物是美的或丑的或无所谓美丑的,是善的或恶的,是自由的或受奴役的,而不只是看似善的或恶的。
我就讲到这里,感谢诸位的耐心,并希望得到诸位的指正。
(本文源自2001年春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一次演讲,后收入《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