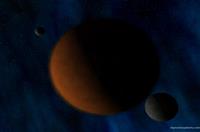孟子对于墨子、杨子深恶痛绝,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而当时的情况很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他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他立下决心与大志:“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
朱子解释说:“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
程子说:“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
孟子对于杨墨的痛恨,一是杨墨的学说与孔儒冲突,二是杨墨当时充塞天下,以至于孔子之道不著。
孟子认为,“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情况,要由杨墨负责。所谓“率兽食人”,是公明仪说的话,《孟子》里引用了两回。公明仪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如孟子所言,这指的是“行政”的情况,这样的“行政”是不配“为民父母”的。
杨墨学说如何与孔儒冲突?杨子的很明显,“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当然不合孔子之道,因为“礼”首尊者君,“仁”首爱者君,就连韩非子也知道“义”是讲“君臣上下之事”的,为臣的岂可以讲“为我”?而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既不爱君,又不爱天下,自私到极点,岂不与禽兽无异?骂得似有道理。
不过,我们能为杨子说一句的是,那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的现象,不是因为听了杨子的话才做出来的,是当时诸侯君王巨室权臣向来的自私与无道。所以,孟子在梁惠王面前引用公明仪这句话,目的是为了教育梁惠王这样的君王。如果说杨子在这情况上也有责任,是他不该面对诸侯君王巨室权臣的自私无道,就思想走极端,鼓吹“为我、贵己”,好像是赌气一样。殊不知,这样的理论,虽然也有启蒙普通人走向人格独立的作用,却也有使天下都自私更无望的作用,毕竟含有消极性。
另外,我们还能为杨子说一句的是,杨子不过是一个讲学者,日常所过的也许还是很贫苦的日子,这种贫苦,我们从颜回、庄子就可以想见。颜回是居陋巷一瓢饮,庄子是要向人借粮食。颜回是一介“逸民”,即没落贵族子孙,庄子的身分当与颜回差不多。所以,若从孟子的时代去看,那些“放恣”的诸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他们治下的国家里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孔孟这些人,还这样起劲叫人俯首贴耳,“庶人……不敢见诸侯,礼也。……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仁,急亲贤也”,“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虽然孟子总是提醒君王“为民父母”,但君王若是“放恣”而想不到“为民”,民也就没办法,更不用说“民”之下还有更等而下之的人群,像杨子这样会思考一点的,因为这情况,愤慨发出要“为我”的声音,那就是一种要求生存和解放的呐喊,又有何奇怪呢?朱熹说,“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这样的说教,其实只是做着“诸侯,巨室”的帮凶而已,而杨子偏不听他们的。
《列子》一书有《杨朱》篇,据研究,不全是杨朱原著,乃至认为是后人所托也就是某种发挥,发挥得似是好的,读来觉得与杨朱“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的“为我”思想是有机联系或辩证联系的,比如,杨朱针对世人往往“为寿,为名,为位,为货”而“不得休息”,提出主张说: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人人不损一毫(不损天下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不以天下自利),天下治矣。”
这样的社会,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杨朱还说:
“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之物者,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
这该算是杨朱思想的最终的结晶,放射出的决不是自私自利的光芒,他的“贵生、为我、爱生”等宣言的真正归宿或原有底蕴,其实竟然是“公天下”而反对“私天下”,这与墨子的“兼爱、尚同”不是相通么?所以,墨子杨朱其实是殊途同归,墨可通于杨,杨可通于墨,孟子看得很清楚: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孟子·尽心下》)。
但表面上,墨子正与杨子相对,一个讲“为我”,一个讲“兼爱”。墨子的“兼爱”,恰恰没有像孟子那样说要把“君”以及“君子”们至高无上地“急”爱,这犯了大忌,当时也是可以攻击的最薄弱环节。孟子从一个很刁的角度说,墨子“兼爱”则“无父”。既然如此,当然就更是“无君”了。其实墨子哪里“无父无君”?孟子扣人大帽子,也算是开了风气而至今未绝。
总起来说,杨墨是违背了孟子所阐释的“仁义”的宗旨。杨与墨就被孟子一锅煮,叫做“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刚烈威猛的卫道形象,真有其“浩然之气”,对此,我们虽不免“肃然而起敬”,却不能不加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了。
1,当今之主,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
2,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
孟子劝诫齐宣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劝诫梁惠王“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这些话里的所见所思,与墨子基本是一致的。如果说墨子的“兼爱”,含有劝诫这些“当今之主”们能“兼爱”到“民,百姓”,则与孟子的“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思想,也可算相去不远,然而孟子对墨子这些话似乎视而未见。
墨子说:
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
这番话中的“兼”字,不就是孟子的“同”字吗?然而孟子却不认可。
墨子说: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夫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
这些情况,孟子该是知道的,因为在“君子”内部,仍有其高低贵贱、贤与不肖,不应当一味的只凭“骨肉之亲”或“面目美好”这样的标准来举贤治国,他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就提到过“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别。
但墨子基于这一现象而提出的主张,孟子就未必同意了,孔子也不会同意的: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在农与工肆之人”,即普通平民“庶人”,或孔子所看不起的自耕农一类的“小人”,墨子竟然说他们也可以被“举贤”,可参与理国事、行政令、享爵禄,这种“理论”,怎么可以?实属违背了三代以来“礼”的大原则。
孟子认为,“庶人……不敢见诸侯,礼也”,如果“往见”了,就是“不义也”,但“召之役,往役”是可以的,是“义也”。这“庶人”只不过是没爵没禄的“民,百姓”,如果是更等而下之的人们,则更应如此规规矩矩遵“礼”守“义”了。
而墨子竟然要破这样铁的规矩,正是藐视那传统之“礼”,是要从下面来让“礼崩”,产生混乱、颠倒,岂能允许?墨子的这种平等观,这种“兼爱,尚同”,在孟子的感受中,如洪水猛兽,所以才那样深恶痛绝。但孟子没有从正面落笔,而是说墨子“兼爱”是“无父”,其实,真正的落笔处,是说墨子“无君”,是有大逆不道之罪的。其实,这时的孟子忘记了历史,《尚书》不是记载说,大舜出身贫贱、从乡野之上得到尧君提拔的吗?但尧舜有这样的故事是可以的,墨子式的理论则不可以。孟子所卫之道,也就十分明白,甚合君王巨室贵族权臣的心愿。所以,朱元璋曾要将孟子逐出孔庙,实属误会,终经劝谏而罢。
于是孟子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句话一面以圣人之徒自任,一面也是号召大家都来跟着他做圣人之徒。
墨子也称舜,禹,汤,武王这些人是“天下之仁义显人”,也说过“国君者,国之仁人也”,“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只是他认为,实行他的“兼爱,尚同”之说,就能真正到达治世。所以,儒墨分歧,从字面上,并不在于是不是赞成“仁,义,礼”,而是在“学术之争”底下,反映了当时贵与贱、专制与民主的对立。
墨子用他的“兼爱”观,全面改造传统“礼治”理论的系统:
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
墨子竟然这样用他的一个“兼”字来全面解释“仁学”,而且,墨学已经“盈天下”,怎能不引起孟子的极大恐惧?如让墨学得逞,就要“孔子之道不著”,但是,“孔子之道”才是正宗“仁学”啊,孟子是不能不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了,劈头就骂墨子一句“无父无君,人道灭绝,禽兽而已”,为此,孟子发出了“人将相食”的警报,也就是说,若依了墨子,平民就要起来参与以至主持天下,贵族就不免要失去好日子了。想当年,这一意识形态之争多么的不可调和。
但孟子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如他自己所说起了多大作用。秦始皇时代的《吕氏春秋·仲春纪》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说这话时上距孟子去世大约七八十年。汉文帝时代的贾谊《过秦论》有“陈涉……非有仲尼墨翟之贤”这样的句子,将孔墨并称贤人。汉武帝时代的《淮南子·道应训》篇说,“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时距离孟子去世已经一百七十多年。可以说,从春秋末年至西汉初期,墨学与孔学三百七十多年间并驾齐驱,都是天下“显学”。孔学是传统之学,墨学是新兴之学,而这新兴之学何以自春秋之末以来能行于天下数百年,又何以自西汉中期以后二千多年间几乎湮没,该都是能从天下政治和人的现实状况中得到说明的,无非反映着贵族与平民在权利方面的此消彼长罢了。
孟子的理论,却也是从社会须有分工这一合理基点出发的,在《滕文公章句上》里,他批评了“为神农之言”的许行,以及盲目崇拜许行的陈相,他由此进而上升到“天下之通义”上,说: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在这样的基础上: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君子对于小人:
“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孟子就这样从社会须有分工,而得出社会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结论,有混淆概念之嫌,而他却认为绝无问题,理直气壮批判杨子的“为我”与墨子的“兼爱”。
我们不可一看到孟子说“为天下得人难,以天下与人易”就失口叫“好”,而不问他这话的原意是什么。
尽管墨子与孟子言词相同之处还是不少的,比如都承认“仁义礼”,都反对战争(墨子“非攻”,孟子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但孟子认为他与墨子不可调和。墨子无差别的“兼爱,尚同”之说,平等观的“尚贤”之说,跟孟子主张的“君子治野人”,决无共同之处。所以,他们也仅仅是言词有相同而已,所阐扬的是各人自己的思想体系,甚至是严重对立的。
墨子还直接点名批判了儒与孔子:
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这怎不令孟子愤慨?
朱熹说,“孟子虽不得志于时,然杨墨之害自是灭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赖以不坠,是亦一治也。”赞扬孟子狠批杨墨十分有效并且立下万世之功。但“自是灭息”一语,夸张不实,因为直到数百年后,世人还是“孔墨”并称,当然,从朱子往前推许多年内,杨墨是“灭息”了,正反映着封建时代的没落。
有研究说,法家本出于子夏之儒,子夏传李悝、吴起,此二人一个变法于魏国而成功,一个变法于楚国虽成功而自身遭害。据郭沫若研究,李悝的历史贡献,“不仅是法家之祖,同时是可以看为封建制的奠定者的”,说明着当初子夏所传授,有儒有法,比较全面。李悝传商鞅,韩非则得力于这些前辈,包括他的老师荀子。子夏恰恰是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可见他根据时代不同,而从“礼学”分化发展出来,影响及于李悝、吴起、商鞅之辈。我们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看到吴起对魏武侯说的“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的话,也是很懂“德教”的,这正是从子夏学过传统“礼义之学”的一个证据。
韩非子之重要篇章《五蠹》,抨击儒,未及墨。韩非子另一重要篇章《显学》,虽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全篇重点仍在抨击儒,而对于墨子的“兼,尚”之说,则未有言及。他稍稍提到的儒墨分歧只有“墨者葬俭,儒者破家而葬”。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指出了大家都上承共同的历史思想文化资源。
几千年来,墨子的博大,不为“君子”所承认,而排斥得远远的,他的平民色彩的“兼,尚”之说,以及“非乐,节用”之说,注定不能为帝王、朝廷所用。至于其对科技的研究,更是“小道,小术”不值一说的了。
墨子“尚同”之说,表面看,亦与儒家无二,比如他说:
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只是这里面的“选贤”、“立天子”、“一同”,是何含义?墨子说:
今王公大人……政以为便譬,宗於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
原来是批评“王公大人”的为政与民不“一同”,认为这是天下不治的原因。这个不“一同”,与孟子对统治者要求的“民与同乐”,意思有区别,墨子是要求“王公大人”在任命左右上下官员时,不要仅仅在“便譬、父兄故旧”里面挑选,也要在这些人之外的人群里挑选,要不然,就会“上下不同义”,而民“莫肯尚同其上”。而这些人之外的人群,当然就包括了他在“尚贤”的观点里说到的“在农与工肆之人”。所以,墨子的“尚同”,也就是他的“尚贤”,总之是认为在“在农与工肆之人”亦有贤人,可以“一同”进入治理社会国家的行列,包括“立天子”,也要天下海选,“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来担当,以便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这些在儒家看来,其非礼与越轨确实简直是达于大逆不道了。墨子这类言论一出,其学说的命运也就被历史决定,他不受封建统治者欢迎并且要湮没它,是很自然的事。
郭沫若认为,“墨家节葬不非殉”(但我们从《墨子·节葬》篇看,墨子不主张“杀殉”。当时“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是加以谴责的。)郭沫若从《墨子·非命》篇找出了“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的墨家主张,并以齐国晏婴的话以印证,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墨子与晏婴一致,理论上仍不能与殉葬陋习根本断绝。他又从《吕氏春秋》的《上德》篇里找出了事实,证明墨家后来成为宗教性的严密组织,勇于以身殉其义,墨家首领孟胜就这样为义自殉,弟子继而自殉者一百八十五人,何等壮烈。这两方面相加,可就成了一个问题,所谓墨流为侠,虽然令人佩服,却成了少数人的行为,不为大多数人信仰追随。郭沫若还认为,“殷周时代的人格神除初期墨家还死死维持着之外,其他的学派都把它几乎完全唾弃了”,这些就是墨家的落后因素。所以,尽管墨家的“兼爱,尚贤,尚同,非乐,节用”这些主张里反映着平民的意识和要求,含有许多合理的以至光辉的成分,其得不到统治者欢迎,除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与时代局限使然,自身含有的此类落后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他关注科技,也是传统的以礼义治人者所不感兴趣的。
墨家之所以从与孔学并驾齐驱的显学学派,转而“灭息”,主要原因是受到东汉以来越来越浓厚的封建统治的歧视压迫,失去了春秋战国至汉初的那种大时代的生存空间,而它的复活,亦必有赖于这种大时代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