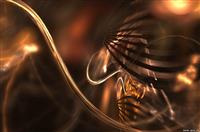本书收录的访谈和文章的几位作者我大都没见过面,仅仅是在网络上拜读过他们讨论墨家的文章或言论,却很为他们的努力和成就所感动。毕竟,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闲暇时间,积极发掘两千年前的墨家思想资源,深入揭示其中包含的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仍然具有深刻启迪意义的普世价值理念,个中的艰辛困苦、挫折磨难,不是我这号专门吃这碗饭的书斋爬格子者能够想象的。
不用细说,就像某些偏爱孔孟的专家曾经以历史上的“朝廷大正统”自居而嘲讽墨家这种“民间小宗教”那样,一些高雅而精英的人士或许也会对这几位墨者的“民间”身份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然而,撇开被捧成了“王”的“大成至圣”当年也一度干过“民间小私塾”的史实不谈,只要抛开儒家所青睐的官本位视角特别是王本位视角,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学说观念在思想史上的真正地位,根本不取决于它是不是得到过统治者的重用乃至“独尊”——当统治者属于“专制独裁”的范畴时,情况尤其如此。相反,扎根于民间、能够真正代表和维护普通民众正当权益的观念学说,不管曾经遭到过怎样的贬抑打压,只要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和深刻性,反倒更能够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焕发出足够持久的强大生命力,因而是那些一门心思只为权势者着想、一味琢磨着怎样才能为君主官长所“用”的显赫一时的学说观念全然没法比拟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本书提出的某些见解或许还没有得到充分学术性的论证(其中的个别提法我也不是完全赞同),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在挖掘问题的深刻程度、洞穿现实的敏锐程度、挑战质疑的尖锐程度上,却超出了许多虽然貌似在形式上恪守学术规范,但在内容上仅仅是响应号召、迎合局势、随波逐流、隔靴搔痒、应付差事、混点经费、评个职称而又毫无创见的所谓“课题成果”。说白了,后者虽然看起来冠冕堂皇、洋洋洒洒,就其实质而言仅仅属于时过境迁之后便立马沦为昙花一现的“学术垃圾”;相比之下,作为几位民间墨者刻苦钻研、认真思考、深入探索的理论结晶,本书更有可能在21世纪墨家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标志着历史悠久的墨家思潮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重新展开了自己的思想行程。
话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对于本书副标题的某种特定理解了:在我看来,它的意思并不是说墨家自从失去了先秦“显学”的身份后,就一直作为“千年绝学”处于完全“不在场”的缺失状态,要到今天才有资格正式进入中国思想史的场域;相反,倒不如说事情的本来面目其实是,汉代以后的墨家其实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依然维系着“在场”的存有,尽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它都不再具有先秦时期那样浩大的声势。就此而言,墨学当下的“登场”与其说是从无变有的“登堂入室”,毋宁说是由隐至显的“再创辉煌”。
的确,单从理论的角度看,在先秦之后的两千年中,墨家阵营里就没有再出现过足以彪炳青史的思想大师,因此在这方面不但不如长期作为朝廷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而且也赶不上与儒家保持着对立互补关系的道家和佛教。尽管这样——或者说恰恰因为这样,下面这个事实才会让人感到十分惊异:墨家思潮并没有像在春秋战国时期竞相争鸣的百家里的其他许多思潮那样,逐渐销声匿迹,变得悄无声息,沦为严格意义上的“绝学”,相反倒是一直维系着自己的顽强存有。更令人惊异的是,墨家思潮两千年来的这种持续绵延,还主要是通过它的头号论战对手儒家思潮实现的;换言之,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显赫一时、左右腾挪的儒家大师们,才无心插柳地让墨学总是处在了“后继有人”的在场状态。所以,这个带有反讽意味的历史事实,才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回味。
众所周知,在先秦时期还是“显学”的时候,墨家的一系列理念就已经受到了孟荀这两位著名儒者的激烈抨击。尤其是所谓“亚圣”给出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种带有咒骂色彩的无端指责,更是为后世“独尊儒术”的统治者从实践上打压墨家奠定了周密的理论基础:强调“忠孝至上”的专制朝廷,在通过孟子的指责察觉到了墨家主张君主“不仁”就“不可以为法”(《墨子·法仪》)的基本理念后,怎么还会给这种“民间小宗教”留下充分的发展空间呢?然而,墨家理念对于种种坑人害人的不义行为的严厉批判,对于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兼爱非攻原则的大力倡导,却毕竟具有如此深厚的生命力,就连它的儒家对手们都没法置之不理,相反还不得不以犹抱琵琶的偷运方式,从中汲取种种积极的思想资源,用来弥补自身先天生成的严重理论缺陷。
举例来说,整部《论语》就没有把“义”当成重要的概念来强调,而仅仅偏重于突显它在君臣关系中的狭隘意蕴,诸如“使民也义”、“务民之义”、“不仕无义……君臣之义”之类。相比之下,正是墨子第一次将“义”与“正”连接起来,作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不可突破的终极底线,明确指出任何偷窃抢劫、杀人越货的“恶人贼人”、“别相恶交相贼”举动都属于“不义”的范畴,甚至还清晰地给出了“杀一人谓之不义”(《墨子·非攻上》)的命题,从而不但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迹,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站在哲理高度上,不但提出了“贵义”的伦理主张,而且还具体揭示了“义”的规范性实质在于“不坑害人”的大思想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大贡献。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以不可抗拒的强大思想力量逼着大肆诋毁墨子的孟荀二人也不得不偷偷引进他在这方面的基本理念,以求堵住儒家理论中那个毛毛草草的大漏洞,甚至在言辞上都只能是不加掩饰地“山寨”墨子的原初命题:“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这种白纸黑字的文本证据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就算后世儒生拼命想将墨家思潮从中国思想史上一笔勾销,恐怕也只能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谓予不信,请看例证:两千年后的张岱年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曾经让儒生们十分扫兴地指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再比如说,墨子强调“兼爱交利”对于所有人的普遍适用性,主张“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墨子·小取》),同样克服了儒家“至圣”只是简单地将“仁”解释成“爱人”的抽象苍白、疲软乏力,不但直接影响到了儒家“亚圣”有关“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的见解,而且还像本书中具体指出的那样,进一步影响到了后来的唐代大儒韩愈、宋代大儒张载等,引导着他们或者以“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读墨》)的方式主张“博爱之谓仁”(《原道》)、“一视而同仁”(《原人》),或者干脆直接借用墨子的概念主张“爱必兼爱”(《正蒙·诚明》),甚至还因此让这些完全有资格进入儒家“亚道统”的候选人遭到了另外一些更富于原教旨倾向的儒生们的攻击,认为他们“语固多病”、“立言有过”云云。
试想,一种几乎已经在一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涌现出理论上的代表人物的学说,居然不仅能让它的头号论战对手毫不掩饰地从中汲取积极的思想资源以弥补自己的漏洞百出,而且还能在头号论战对手的庞大阵营里引发若干场足以在思想史上也留下清晰一笔的公开“内讧”,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比这一现象更充分地见证它自身的那种虽然隐而不显、却又是绕不过去的深刻在场性吗?
不好意思,思想史就是这样彪悍。
弄清楚了思想史的这种彪悍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期,在西风东渐的氛围下开启了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候,不仅许多国内的风云人物,而且许多国外的汉学研究者,都纷纷给予了墨家以超出儒家的极高评价,一方面将它的“兼爱”理念与基督宗教的“圣爱”理念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特别称颂了它在科学技术、逻辑思维方面为中华文明做出的出类拔萃的独特贡献——不幸的是,恰恰是由于儒家思潮的残酷打压,墨家思潮在这方面的积极贡献才变成了严格意义上后继无人的“绝学”,结果当中华文明终于面对着现代化的人类历史大潮的关键时刻,只能是哀叹自身在科学技术、逻辑思维方面的先天不足了——某种至今我们其实也没有完全摆脱其深刻积淀的文化劣势。
当然,在此同样有必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墨家遭受了种种打压而缺失自己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只能通过众多大牌儒者的“山寨”、抨击甚至内讧来维系自己的“后继有人”这一缘故,两千年来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在场性并不是它自身的本真在场性,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倒是一种被其头号论战对手儒家严重扭曲了的在场性。这种扭曲不仅体现在儒生们对于《墨子》文本的曲解乃至篡改之上(令人欣喜的是,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一批墨学研究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拨乱反正的积极努力,我真诚期待不久之后能够见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式问世),而且尤其体现在儒生们对于墨学理念的有意歪曲、肆意诋毁、恶意毁谤之上——所有这些甚至对于不少同情墨家的学者人士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此,不将这种被扭曲了的在场性纠正过来,中国墨学的当下登场还是有可能重蹈以往两千年历史的悲剧性覆辙。
本书作者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将“立墨”与“非儒”结合起来,坚持“不非儒就不足以立墨”的立场,乃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能言距孔孟者,圣人之徒也”的口号。这一点也是我十分赞赏的,理由很简单:两千年前的墨学原本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两千年后的墨学也只有这样做、必须这样做,才能找到自己本真在场的立足之地。有鉴于此,虽然本书作者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及了这个问题,我还是想借用这篇序言的有限空间,简单地谈谈我对墨学理念遭受扭曲的一些看法,以便澄清某些最严重的误读曲解——尤其需要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在此指出的是,我自己以前也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这些误读曲解,从而充分暴露了我在研读《墨子》文本方面的不严谨不扎实。
首先就是那种认为墨家“兼爱”理念的实质在于“爱无差等”的曲解。大家知道,按照《孟子·滕文公上》这部儒家书籍的记载,墨家弟子夷之据说曾经在与儒家亚圣的一场论战中提出过“爱无差等”的说法;后世儒家于是就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将其说成是整个墨家的基本立场,甚至还据此指责墨家“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父母的爱没有差别”,鼓吹“绝对平等”、“平均主义”,以致许多学者乃至墨者也不加辨析地认同了这一点,承认墨家确实含有“平等主义”的倾向。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说法不但在现存的《墨子》文本中找不到清晰的文本根据,同时也不符合墨子自己给出的大量难以否认的经典论述。事实上,稍微浏览一下就会发现,正像儒家“至圣”在倡导“仁爱”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墨子自己在倡导“兼爱”的时候,也总是对症下药地要求父子之间维系“慈孝”、君臣之间维系“惠忠”等等,所谓“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墨子·兼爱中》),既没有将这些特殊性人际情感之间的区别一笔勾销,也没有将它们与普遍性的兼爱情感混为一谈。所以,倘若我们确实尊重《墨子》文本对于墨家思潮的元典意义,显然很难断言墨子本人也认同“爱无差等”的说法。不管怎样,要是主张父慈子孝、君惠臣忠的儒家“至圣”不能说成是“爱无差等”的倡导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同样赞成父慈子孝、君惠臣忠的墨子说成是“爱无差等”的倡导者呢?
不错,《墨子·兼爱中》猛烈抨击道:“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但细究起来,墨子批判这类“别爱”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父母的爱没有差别”,而仅仅是要求人们不要基于对自己、家人、本国的封闭偏狭之爱,从事“损人利己”、“损人利亲”、“损人利国”这类不义的举动,相反应当凭借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兼爱”情感,努力防止一切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说穿了,正是从墨家思潮中汲取了这些不是抽象地倡导“爱无差等”、而是具体地反对“坑人害人”的积极思想资源,后来韩愈才提出了“一视而同仁”的流行说法,张载才也提出了“乾父坤母”、“民胞物与”(《正蒙·乾称》)的著名命题。至少,如果我们没有理由硬说儒家的“一视同仁”理念是“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父母的爱没有差别”,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硬说墨家的“兼爱”理念是“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父母的爱没有差别”吧。
当然,我们依据有关文本指出墨子没有提出“爱无差等”的说法,而是也承认了“君惠臣忠”、“父慈子孝”的差等情感,并不等于说墨子思想中就不包含主张“平等”的因素了。相反,正如刚才的分析足以表明的那样,他的“兼爱”理念特别彰显了人际关系中一种最重要的“平等”——“任何人都不应当受到他人坑害”意义上的“平等”;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墨子·兼爱中》的一正一反两个命题上:他一方面激烈抨击了“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邪恶现象,另一方面又积极倡导了“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正义原则。
无需“同情理解”、只要“尊重文本”,我们就能发现,墨子在这些命题中根本没有否认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贫富、贵贱、强弱、诈愚等诸多方面的等级差异,尤其是没有激情浪漫地高调号召人们一举抹平这些常常是令人不快的等级差异,而是仅仅提出了一条看似肤浅的底线要求:强者、众者、富者、贵者、诈者不应当凭借他们在权势、数量、财富、等级、智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在人际交往中欺凌、侮辱、压迫、残贼、坑害社会分层中的弱者、寡者、贫者、贱者、愚者。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墨子根本就没有否认“人有差等”的现实,而只是在承认这种差等现实的基础上,力图在具有种种等级差异的人们之间确立起一种符合“正义”底线的人际“平等”关系——“不坑害人”意义上的人际“平等”关系。
更重要的是,墨子的这种理念才真正抓住了“平等”问题的要害所在。众所周知,出于对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反感厌恶,古往今来的各种思潮曾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平等”观念,试图消除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财富、生活享受、社会身份、道德品格、政治地位、管治权威、才能机遇、具体权益等方面的等级差异,达成彼此间的平均一致。然而,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不管这些“平等”观念听起来怎样理想美妙,它们没有一个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到底,相反在付诸实施的时候还有可能引发坑人害人、侵犯人权的邪恶后果。理由很简单:首先,它们都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财富、生活享受、社会身份、道德品格、政治地位、管治权威、才能机遇、具体权益等方面的那些等级差异,在人类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上都不可能消解得一干二净;其次,它们更没有看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深恶痛绝的其实也不是这些等级差异本身,而是在这些等级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现象,亦即强势一方坑害弱势一方、侵犯后者正当权益的不义行为。
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在道德上属于“不可接受”范畴的邪恶,并不是各种不平等的等级差异现象本身,而是某些人凭借这些等级差异坑害他人、侵犯人权的不义举动。考虑到这一点,对症下药的基本原则当然也就不应当是幻想着实现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乌托邦,而是像墨子那样一方面反对“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恶人贼人”,另一方面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爱人助人”,最终努力达成人与人在“谁都不可受到坑害”这一关键点上的终极平等。就此而言,要是夷之作为墨家弟子也真诚认同了墨子坚持的“平等”理念,我们就应当在强调“关爱任何个人或团体的行为都不应当凭借人际之间的任何等级差异导致坑害其他人的邪恶后果”这种限定的意义上,亦即在墨子反对凭借“别爱”损人利己、损人利亲、损人利国的严格意义上,去理解他提出的“爱无差等”说法,否则他自己就有可能背离了墨家思潮倡导“兼爱”的基本宗旨。
值得指出的是,就连当代西方推崇“平等”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潮也迷失了这个关键的要害,结果同样落入了所谓“平等主义”的陷阱。例如,威尔·金里卡就宣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与辩护者共享着一种观念:正当原则是对我们应当给与每个人的善以同等考虑这个要求的清晰阐发。……德沃金已经论证,罗尔斯与批评者分享着同一块‘平等主义高地’:他们都同意‘社团成员的利益是重要的,并且同等重要’。”(金里卡:《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应奇、葛水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但很不幸,这种“给与每个人的善以同等考虑”的“平等主义”高调虽然在理论上十分美妙动听,在实践中却完全不切实际,特别是遗忘了至关紧要的一点:尊重人权的终极目的根本不在于实现人际之间在物质财富、经济地位、政治权力、乃至具体权益等方面的形式性均等,而是仅仅在于实现那种唯一应当达成的实质性平等:每个人的应得权益都不可受到侵犯。就此而言,墨子充分彰显了“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底线意义,一方面强调任何等级差异都无法构成坑人害人的正当理据,另一方面又主张只要不会导致坑人害人的邪恶后果,包括贫富、贵贱、强弱、智愚在内的任何等级差异都是可以允许的,甚至要比当今西方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潮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人际平等的实质所在,对于我们今天站在尊重人权的普世价值立场上,解开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悖论这个长期困扰着西方学界的理论死结,克服左翼平等主义的消极弊端,具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启迪意义。
极度反讽的是,恰恰是拼命想给墨家扣上“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帽子的儒家,才一方面真诚真挚地维护周公姬旦开创的权贵礼制主义的森严等级规范,认同和鼓励强势者特别是统治者凭借“别爱”从事那些损人利亲、损人利国的邪恶行为,另一方面又假仁假义地提出了一系列“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口号,结果让自己沦为了不但自相矛盾、而且精神分裂的典范案例。口说无凭,文本为证:首先,儒家“至圣”就公开鼓吹“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其次,儒家“亚圣”不但声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试图以乌托邦的伪善方式达成人与人在道德品格上的平等划一,构成了后来儒生们大搞“道德绑架”的精神资源,而且极其偏激地主张“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为了标榜自己的“亲民”态度,不惜宣扬老百姓与统治者在“好货好色”的物质享受方面也应当维系绝对同等的虚幻理想,从而严重扭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的“大同”理念。更严重的是,他甚至还打着儒家式“义利之辨”的堂皇招牌,宣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以不但极端、而且荒诞的一刀切方式,无中生有地在“富”与“仁”之间设置了某种不共戴天的对立框架,站在儒家伦理的虚伪“制高点”上,指责一切有财富者都属于不仁不义的道德恶人。
正是在两位儒家圣贤的这些“绝对平均主义”观念的误导引诱下,像“均贫富、等贵贱”这一类的激进口号后来才得以在中国历史上广泛流行,以致连“不配姓赵”的阿Q居然也会形成“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革命”动机,一有机会就想到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打个滚,实现“好货好色”方面的“同之”诉求;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儒家的这些观念更是成为某些人特别是权贵集团打着“公有”、“平等”的华丽旗号大肆剥夺普通人正当拥有的私有财产,用来满足自己的奢侈享受的思想资源,造成了两千年来绝不罕见的只“劫富”、不“济贫”的恶劣后果。相比之下,墨子除了正面鼓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墨子·尚贤上》)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出过类似的激进主张,相反还在强调“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同时,又特别彰显了“众不劫寡”的重要意义,明确反对贫穷者利用自己的人数优势劫夺少数富有者的正当财产的侵权做法。两相对照,谁才是鼓吹“绝对平均主义”的急先锋,谁才真正流露出不正当的偏激“平等”倾向,不就一目了然了么?
其次则是那种认为墨家“尚同”理念旨在鼓吹“专制极权”的曲解。19世纪末叶以来,不但许多儒生这样拼命抹黑墨家,而且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曾对墨家持有赞许态度的学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曲解,认为墨子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是试图反对“多元化”、拒绝“和而不同”,由于强调整齐划一会导致“专制独裁”乃至“极权主义”。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孤立地看待这句文本,而是将其置于墨家“尚同”理念的整体语境之中,很容易发现这种曲解其实属于望文生义的不着调以及一拍脑袋的想当然。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墨子主张的“上之所是所非”属于统治者个人或小团体持有的偏狭专断的是非标准、礼制规范,那他强调全社会都必须“尚”这样一种“同”而不允许出现任何不同看法,当然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制极权”了;同时,由于这样一种“尚同”势必导致现实生活中坑人害人的后果,它即便在古代也会被许多人视为道德上“邪恶”的。事实上,今天人们在尊重人权的普世价值意义上试图拒斥的所谓“专制极权”,恰恰具有这种侵犯人权的典型特征:统治者个人或小团体为了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凭借自己在政治领域内拥有的强势权威特别是暴力机器,强制性地推行自己持有的是非标准、礼制规范,迫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和恭顺服从,如果谁竟敢从事反抗的行为、甚至提出反驳的言论,就会对其施加残酷的惩罚,亦即哪怕造成坑人害人的严重后果也要确保自己的是非标准、礼制规范得以贯彻。一旦澄清了这个关键点,事情就变得足够清晰了:难道从《墨子》的全部文本中,我们能够找到任何支持这种理解的清晰证据么?不但答案明显是否定的,而且我们同时还会发现:墨子恰恰坚决反对这种坑人害人的专制极权,尤其是严厉驳斥了为这种专制极权提供思想资源的儒家理念。
本来,从上下文的关联看,墨子是在下面的特定语境中提出“尚同”理念的:“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墨子·尚同下》)换言之,由于现实生活中不同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种种差异(也包括刚才讨论的等级差异),他们站在自己的规范性立场上认同的“正义”标准也各有不同,像有些人以“损人利己”为“义”, 有些人以“损人利亲”为“义”, 有些人以“损人利国”为“义”,等等。倘若听凭这种“各自为义”的现象任意发展,势必造成“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邪恶后果,甚至导致社会整体的分崩离析,尤其是弱势者备受坑害而几无立足之地。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墨子才明确提出了“尚同”的主张,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严格遵守同一条“正义”的底线——换言之,墨子的“尚同”理念实质上只是为了克服“各自为义”的乱象丛生,
才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崇尚同一条正义的底线”,所谓“欲同一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下》)。
话说到这份上,事情就清楚了:墨子要求全社会都必须“尚同”的那条“正义”底线的具体规范性内容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他反复强调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也正是从这种特定的规范性立场出发,他才极力提倡“爱人利人”、“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恶人贼人”、“别相恶交相贼”,所谓“别非而兼是”(《墨子·兼爱下》)。换言之,按照墨子主张的“是非”标准,只有不坑害人、兼爱非攻的“义”才是唯一应当成为社会共同底线的“正义”,而任何基于偏狭之爱(“别爱”)坑人害人的“义”都属于不正当(“非”)之“义”, 应该否定。事实上,他曾通过一段清晰的文本,细致描述了坑人害人的“不义”实质: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杀一人谓之不义。(《墨子·非攻上》)
换言之,所有那些今天被认为是侵犯人们的正当财产权和生命权的偷鸡摸狗、杀人越货行为,在墨子看来都属于“不义”的范畴;与之对应,显然只有“不坑害人、尊重人权”的举动,才有资格符合墨子指认的“正义”底线了。如前所述,儒家孟荀二人在讨论“仁义”概念时所阐发的那种“义”,正是不动声色地悄悄汲取了墨子的上述核心理念,从而在这个方面不自觉地维系了墨家思潮在后来中国思想史上的隐身性在场,让我们今天还能从中发现这位两千年前的大思想家是如何运用古代汉语积极提倡“尊重人权”这条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念的。
进一步看,墨子也是在上述“正义”底线的意义上,才提出了“万事莫贵于义”的命题,反复指出:“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上》);“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他的理由很简单:只有在人际互动中严格遵守“不坑害人”这条唯一不可逾越的共同正义底线,人们才不仅能够维系各自的生存发展,而且还能达成社会的良好秩序,实现繁荣富强;相反,一旦违反了这条底线,人际之间就会出现尔虞我诈、相互坑害的乱象,不仅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物质生活陷入贫瘠匮乏,而且人们自己也会走向毁灭死亡。有意思的是,比墨子晚了两千年的康德也曾以类似的方式指出:“如果正义沦丧,人们便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了。”(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4页) 于是问题来了:难道我们也有理由因此指责这位德国哲学家主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他指认的那条唯一的正义底线,就是旨在倡导“专制独裁”、鼓吹“极权主义”吗?荒唐。
从这个角度看,胡适虽然号称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并且也确实在传播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方面做出了难以抹杀的积极贡献,但严格说来他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正义理念的实质精髓,反倒流露出一丝把它简化成“为所欲为”、“怎样都行”的幼稚肤浅——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单凭墨子强调“尚同”、主张全体社会成员遵守唯一的共同“正义”底线这一点,就指责这位古代思想家是在倡导“专制极权”呢?
无论如何,恐怕不需要从哈佛学到多么高深的知识,我们也足以明白这样一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没能在理论上加以突出、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即便在一个自由宪政的社会里,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社会管理者(墨子所谓的“上”)肯定也要无条件地站在自己的规范性立场上贯彻“尚同”的理念,坚持把“不坑害人、尊重人权”的正义原则设定为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共同恪守的唯一行为底线,并且通过宪法以及各种具体的法律条文将其付诸实施,不允许任何坑人害人、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一旦出现了就要采取种种手段给予严厉的惩罚,以求维系自由宪政社会的“良序”——这正是墨子主张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哪怕对于那些不会当下实际产生坑人害人的严重后果、因此基于“言论自由”可以允许发表的鼓吹损人利己、损人利亲、损人利国的观点,身为自觉的自由主义者也应该在理论上予以批驳和揭露,让其他社会成员充分了解这些观点的不正义特征,而不能按照胡适有关“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糊涂见解,以放任自流、怎样都行的和稀泥态度对待这些不符合“正义”底线、违反了“尚同”理念的错误观点。不管怎样,难道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极权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空泛苍白的“和而不同”而不惜放弃“尊重人权”这条唯一的正义底线,以致允许人们维系“各自为义”的“多元化”状态,乃至怂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任意偷别人家羊,随便杀害无辜者,或是协助犯下这些坑人害人罪行的亲属潜逃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两千年前的墨子其实远比同时也是一位“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更深刻地洞穿了当今自由主义坚持的“尊重人权”的正义原则的精神实质。
倘若再考虑到胡适早年曾经这样说过:“那反对墨家最利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5页),我们实在是很难理解他在解读墨子思想时所遵循的内在逻辑:一个鼓吹“专制极权”的人,怎么可能脚踏实地地做到“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呢?反过来看,一个脚踏实地地做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又会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鼓吹“专制极权”呀?更有反讽意味的是,要是墨子的“尚同”理念真的构成了支撑“专制极权”的思想资源,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朝廷君主为什么没有一个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墨术”,明确将《墨子》文本指定为科举考试的国家级教科书,反倒让它几乎变成了隐而不显的“千年绝学”呢?难道我们能用后面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来“证明”这些朝廷君主没有一个具有“专制极权”的意向,而是统统实施了具有所谓“自由主义”倾向的“特色宪政”,所以才会专门到儒家思潮那里去寻找文化基因的“活水源头”么?无语。
从这个角度看,许多儒生居然也指责墨子的“尚同”理念倡导“专制极权”,明显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不怕让人笑掉大牙了。理由很简单:无论孔孟荀等人曾经吟唱出了听起来如何罗曼蒂克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高调,他们实际上也是明确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尚同”理念的,只不过与墨家截然有别的是,他们要“尚”的“同”并不是“不坑害人”这条墨家指认的唯一“正义”底线,甚至也不是他们或许带点真诚地倡导的“仁义”理念,而恰恰是深深地浸润在他们的血液和骨髓里、被他们视为儒家唯一命根子的“忠君孝父”的“礼义”底线,从而必然导致我称之为“权贵礼制主义”的专制极权统治。也正是基于这条唯一的“礼义”底线,他们才异口同声地公然主张“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孟荀二人甚至还敏锐地察觉到了墨子倡导的“平等”和“尚同”理念对于君主专制极权构成的严重威胁,所以才指责墨子是“无父无君”的“禽兽”, “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荀子·天论》)。弱弱地问一声:一个“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家,所鼓吹的会是怎样一种“专制极权”呢?
相比之下,倒是墨子才针对儒家认同的“权贵礼制主义”的专制极权统治,清晰地主张“君不仁莫可以为治法”,强调只有“天之行广而无私……;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所以“莫若法天”(《墨子·法仪》)。以此为基础,他还进一步提倡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宣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甚至流露出了在“天子”层面也应当实行“尚贤”原则的倾向,主张“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中》)。试问,世界上有哪个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不但会“尚同”这样一种“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的“天志”,不但会宣布如果君主“不仁”就“不可以为法”,而且还明确肯定了有能力的“农与工肆之人”也有担任重要政治职位的平等资格呢?难道“专制极权”的实质不恰恰在于:即便君主极端“不仁”,他不还是可以凭借血缘世袭和暴力机器强迫全体臣民以他“为法”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岂不是赞成“大人‘世及’以为礼”(《礼记·礼运》)、鼓吹“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才是“专制极权”的真正吹鼓手吗?
所以,虽然人们既能发现“客观”的辩证法,也能玩弄“主观”的变戏法,但在究竟谁才是“专制极权”的倡导者这个问题上,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黑变不成白,白也变不成黑,因为白纸黑字的文本证据就在那里,不动如山。
在两千多年的隐形在场过程中,墨家在思想上遭受的无意误解和有意扭曲绝不限于“平等”和“尚同”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在这两个理念上遭受的误解和扭曲却是影响最广泛、性质最严重、后果最恶劣的。因此,墨家要想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舞台上再次以“显学”的面貌登场,自然就应该以重新阐发这两个理念作为突破口,尤其是大力彰显它们共同肯定的“不坑害人、尊重人权”的“正义”底线,向世人展现出其中包含的不但儒家思潮望尘莫及、而且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略逊一筹的深刻内涵,由此揭示两千年前的墨家思潮就已经十分清晰地确立起来的适用于古今中外的那些普世价值理念。
令人高兴的是,本书作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他们的对话和文章中反复论及了墨家理念过去曾经和当下还在遭受的种种误解和扭曲,其中也包括了“平等”和“尚同”这两个关键的要点。事实上,就像当初墨子自己所做的那样,他们主张的“非儒”以“立墨”也不是要根本否定儒家思潮;毋宁说,他们所“非”的首先是儒生们自孟荀起便强加在墨家身上的种种污蔑和抹黑,因为他们深知,不将这些缺乏根据、毫无道理的东西“非”掉,墨家就无从“立”。就此而言,本书的确可以说是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为墨家在21世纪的重新登场铺下了一块奠基石。期待着今后在民间和学界有更多的人士投身到积极弘扬墨家传统的努力之中,期待着今后在这个方向上能有更多更优秀的墨学论著不断问世,期待着拥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墨家思潮能够凭借它那些深刻隽永的普世价值理念,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重新焕发出无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