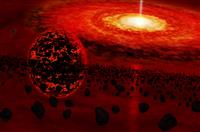
俗话说“近墨者黑”,还真没说错。这不,先秦那位长得本来就比较黑的墨姓老头,两千多年了,便被人泼了差不多一太平洋的脏水,你就是把全地球的排水机都拉来用上,恐怕也没辙。前几天刚刚对付了“兼爱即绝对平均”和“尚同即专制极权”的陈词滥调,又想起了另外还有一拨污蔑墨家是“极左”的奇谈怪论,打算在此澄清一下。
各位都知道,自己也主张“仁者无不爱”的孟贤人,曾经因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指责他是“禽兽”;一帮现代儒生大概觉得不好意思再宣布“禽兽”的本质在于“利天下”了,于是就顺带着抓起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帽子,声称墨家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也想实现“财产公有、均贫富等贵贱”的乌托邦,流露出了“极左”的激进倾向。某些自由主义者可能没怎么读过《墨子》,听到这样的说法后却立马不仅信以为真,而且“义”愤填膺,同样把墨家当成了“洪水猛兽”避而远之,反倒纷纷向两千年来朝廷的正统意识形态抛去了像秋波一样风靡的媚眼,努力到儒家那里寻求自由人权的思想资源,尤其热衷于从孟夫子“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的命题里采掘“中产阶级”的文化基因,乃至以倾向于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自居并自豪,一时间波涛汹涌蔚为大观。
可惜的是,这种道听途说的想当然、望文生义的拍脑瓜十分离谱,因为只要撇开了那些二三手的先入之见,回到第一手的《墨子》文本那里,我们恰恰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护私有财产权和个体生命权的哲理宣言。大话说多了没用,还是直接面对原典本身,看看这位墨姓老头到底是怎样讲的吧: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杀一人谓之不义。(《墨子·非攻上》)
这段话比较长,听起来也有点古奥,但意思却不难懂,因为它讲的实在是一条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谁要是偷了抢了别人家的东西,不管是小不点的桃子李子,还是有些分量的鸡犬猪羊,或者是大块头的马匹耕牛,统统属于“亏人自利”的“不仁不义”;假如他看中了某人的衣服刀剑想据为己有,居然把那人给杀了,性质就更严重了(“罪益厚”),不但大家伙会谴责他(“非之”),而且社会的管理者(“上为政者”)也会按照“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的“尚同”原则,对他施加惩罚(“罚之”)。
对于上面的文本解读,想必除了那个偷了东西抢了财物杀了人的“谁”及其同道外,各位不会有啥异议吧。于是结论就来了:尽管找不到“私有财产”和“权益”这样的严谨概念,其中彰显的不正是每个人在私有财产和个体生命方面不容侵犯的正当权益吗?不错,与墨子同时代的杨朱曾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也从一个角度肯定了个体的正当权益;可要是较起真来,这毕竟还是某种人生意向的消极陈述,并没有明确否定侵犯个体权益的“不义”罪行,不是?
有人会说了:墨子在此反对的只是大白话叫做“坑人害人”的“亏人自利”行为啊,怎么能理解成高大上的“捍卫个体权益”呀?至少也得拉出个“自然法”什么滴当大旗吧。不过,撇开墨子“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的出发点不谈,保守文化的自由主义不是一直都强调自己扎根在悠久历史经验的深厚土壤里,却不太喜欢文绉绉的时髦“理性”话语么?无论如何,“捍卫个体权益”的口号要是不能落脚到“反对坑人害人”的生活实际中去,对于那么多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老百姓来说,还有啥意义呀?至于将生硬拗口的学术概念和法律术语转换成了普通人也能懂的日常语言,又有什么不好呢。
更重要的是,墨子也没有到此就打住了。出于对种种“别相恶交相贼”的“不义”罪行的深恶痛绝,他还进一步强调了“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一方面主张,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压倒“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了,另一方面又指出,只要遵守了这条“正义”的底线,人类社会就可以维持可欲的“良序”,所谓“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考虑到这里的语境关联如此清晰,要是这位长得比较黑的老先生不能算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主张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哲理宣言的发布者,鄙人就真不知道谁还有资格了。要不,你举出一段更早的话让大家瞅瞅?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
再把眼光投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两千年后的英国人洛克,今天还能受到自由主义者们的高度推崇,头号原因不也就是他明白指认了人们的财产权和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嘛。既然如此,墨子认为无论是谁剥夺了人们的私有财产和个体生命,都构成了“不义”的罪行,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思想实质上与他比起来又逊色了几分呢?不管怎样,美国当代法律人艾伦·德肖维茨最近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这本书中,不也试图从人们有关“不正义”的日常经验里寻找“权益”的来源,结果从一个角度见证了两千年前中国墨姓老头的深刻原创吗?
更有意思的是,墨者们虽然很少“学而优则仕”,荣升“大司寇”,一看见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异议分子就把他当成“一夫”给“诛”了,因此也没什么机会将上面的哲理宣言转型为现实中的法律,他们却的确在自己的团队中将这条“正义”的底线贯彻到底了。大家都知道《吕氏春秋·去私》里的那个故事,有位墨家巨子的独生子杀害了一个无辜者,虽然君主赦免了他,巨子本人却遵守“杀人者死”的墨家规定将儿子处死了。不难想象,要是有哪位墨者或其亲属偷了别人家的羊,肯定也会因为犯下“不义”罪行的缘故受到惩罚吧。
无需废话,儒生们当然会含情脉脉地指责这种做法“六亲不认”(尽管从周公姬旦起,他们也常常奉行为了忠君“大义”不惜斩杀亲人的残忍信条);另一些人则可能依据《吕氏春秋》的篇名觉得墨者们太“无私”了,甚至还会抨击墨家内部的等级森严,巨子居然能握有生杀大权。但要是你自己的亲人被杀了或财产被盗了,因此没有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先决条件,难道你还会更“无私”地认为,墨家巨子履行“有罪必罚”的正义要求以维护人们的财产权和生命权属于“不近人情”,反倒基于不正当的私利亲情包庇犯下了不义罪行的亲戚才有资格成为“圣贤模范”吗?你没病吧。
话说到这份上,就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据说是支持“中产阶级”的咱儒家了。撇开“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命题在语境里只是强调了君主让百姓拥有“恒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并没有彰显百姓对“恒产”的正当权益这一点不谈,更重要的是孟贤人紧接着还宣布:“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本来,事情可以说是明摆在那里:在“为富”者中既有人“不仁”也有人“仁”,在“为仁”者中既有人“富”也有人“不富”;可亚圣却纯粹基于财产数目的“阶级分析”,非此即彼泾渭分明地硬性宣布:“凡是有钱的都缺德,凡是有德的都缺钱”……话说就算你当年快接近了穷矮矬的“吊丝”级别,同时据说还顶着“大儒”的道德光环,也用不着“嫉富如仇”地把一刀切的大棍子这样抡过去吧。
别拿这话是他人说的搪塞过去,因为不但孟夫子对于这副仇富的对联没有提出丝毫异议,而且它的精神实质也完全符合咱儒家一贯的“义利之辨”。孔圣人不是早就说过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贤人则将这种凭空设置的反差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地主张“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所以才有了“富”与“仁”的不共戴天:既然逐利的行为属于“禽兽”,发财致富的那伙人肯定就没资格算“人(仁)”了。
于是问题就来了:你说这样子你积累起来的那点“产”还怎么个“恒”法?可能还没达到“中”的档次呢,皇上看不顺眼就当成“不稳定的因素”一把给夺走了。咋啦,你有不满情绪?明摆着是“为富不仁”的敌对势力嘛,给朕拿下!不妨从这个角度对那些自以为“儒商”的“中产阶级”的内心纠结来上点精神分析,说不定能找到某些特色跑路现象在副交感神经末端的浅表动力。
更荒唐的是,老有人以为“均贫富等贵贱”的“绝对平均主义”来自墨家,却忘了孔圣人的警世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也忘了孟贤人的愤青主张“王如好货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更忘了孟贤人的革命口号“闻诛一夫纣矣”(《孟子·梁惠王下》)。再加上刚才提到的“为富不仁”,这些后来被收进了《四书》这本国家级教科书的命题可是普及得很,远远超过当红歌星的流行程度,要说它们既没有给“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打上多少印迹,也不会影响到阿Q那种“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造反激情,你觉得靠谱吗?再说了,历史上打着“革命”旗号的许多改朝换代,不都喜欢顺着咱贤人的腔调,宣布自己是在讨伐“独夫民贼”么?
于是乎不用细说了:要是有人在孔圣孟贤的热忱感召下,这样子通过“患不均”“诛一夫”的途径,去实现自己“好货好色”的“同之”诉求,私有财产和个体生命的不可侵犯还有可能维系吗?毕竟,那些先是被“仇”了一回、然后又被“均”掉了的“富”,不会像馅饼那样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吧。至于同“‘劫’富”和“革‘命’”捆绑在一起的残酷杀戮血流漂杵,不但连当年亚圣的玻璃心都看不下去,以致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劲头曲为解说,而且后来也受到了20世纪头号大儒熊十力的痛斥:“武王最劣。殷帝纣已自杀,而犹亲斩其首。纣妾已自杀,而亦亲斩其首。何不仁已甚乎。”(《乾坤衍·辨伪》)考虑到咱儒家的顶级“道统中人”都能下狠心将斩草除根的活儿做到这种地步,要是我们还找不出那些激进的极端倾向在传统文化里的活水源头,大概真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智商层级了。
火上再浇它一盆油吧:不管是孔圣人赞美的“其父攘羊,子为父隐”,还是孟贤人讴歌的“瞽瞍杀人,窃负而逃”,也同样显摆了咱儒家对于私有财产和个体生命的不在意:就算我老爸偷了别人的羊,杀了个无辜者,就算我也承认这些勾当属于“不义”,但倘若与俺俩之间的血缘亲情比起来,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桩罢了;所以,你要想因此惩罚我那再亲爱不过的爹地,可是连一点门儿都没有滴,我不但会竭尽全力帮他隐瞒,而且还会偷偷背起他远走高飞,奔赴那法律管不着的海外他乡——咦,这话今天听起来怎么还这样子耳熟尼……
七八年前,在海外他乡的一本AHCI级别的英文学术杂志上,曾围绕“亲亲相隐”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讨论;有位从美帝某所顶尖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的洋教授,便这样子振振有词地当上了孔孟的卫道士:那地主家里有那么多羊,顺手牵走一只多大个事儿啊?如何比得上神圣庄严的父子亲情哟。参与讨论的在下于是隐隐约约闻到了颇为熟悉的“劫富”气息,心里十分惊讶咱儒家的“普世价值”怎么这么快就“全球化”啦……
文化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或许又说了:侵犯了财产权和生命权当然不合“天理”,但严重伤害了父子之间的血亲情感,不也同样违反了“自然法”吗?所以咱儒家的立场自有它的道理,也有资格构成自由主义的文化基因……
和稀泥的好处就是全方位辩证,面面俱到啥都拉不下。但很不幸,要是两条“天理”之间居然也打起了架来,你作为自由主义者,又觉得哪一条“自然法”才有优先性呢?说白了,这正是人生在世一切麻烦的终极根源:就像鄙人有关“诸善冲突”的研究可以表明的那样,要是各种好东西本来能够和平共处没有矛盾,人们根本没必要劳心费神,因为它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做到其乐融融美美与共;倒霉的只是它们之间出现了张力冲突,就像鱼和熊掌那样不可得兼,没法一块儿红烧或清蒸,你该咋办呀?
说得明白点就是:要是你像咱儒家那样把血缘亲情凌驾于人们的财产权和生命权之上,恪守“尊重人权”的“正义”底线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很难再标榜自己是捍卫私权的自由主义;要是你像他墨家那样主张“尚同”,坚持对亲属犯下的“坑人害人”罪行实施惩罚,又会丢掉咱儒家当成了命根子来维护的“父慈子孝”的高尚“德性”,因此也没法再成为朝廷意识形态的亲密同道。于是乎,一旦自由主义的脑瓜里灌进了咱儒家的水,你的“通两统”就只能是在稀里糊涂的一锅粥里早早泄了气。不是你实力不济顶不住,而是你无可奈何花落去。
再扩展来看,道理也是一样滴:不管你把什么东西置于了人们的财产权和生命权之上,一己私利也好,忠君之情也好,朋友之谊也好,均富动机也好,集体利益也好,国富兵强也好,高尚德性也好,你的自由主义立场都会像被蛀空了的大坝一样,让水冲上一下就土崩瓦解了,沦为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却唯独不再是本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相比之下,只有像被抹黑成“极左”的墨家那样,始终坚持“万事莫贵于义”的底线原则,根本否定一切坑人害人、侵犯人权的“不义”罪行,我们才能沿着自由主义维护财产权和生命权的人间正道走下去。
说破了,在这个国度里,私有财产权和个体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主义理念之所以到了21世纪的今天都很难确立,精神文化层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主张“血亲至上”和“移孝作忠”的儒家思潮,凭借自己作为朝廷意识形态长达两千年的“独尊”优势,残酷打压了坚持“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的墨家学说的发展空间,结果严重扭曲了人们的“正义感”,以致某些西化了的自由主义者居然也认为:像“子为父隐”“窃负而逃”这类为了血缘亲情包庇侵权行为的“不义”举动,属于什么更神圣更高尚的“天理人情之至”。
说穿了,先秦那位长得本来就比较黑的墨姓老头“摩顶放踵利天下”,仅仅是他本人基于自愿的自由选择,并且真正体现了正义底线之上的高尚德性;咱们自己或许做不到,可难道因此就能污蔑他是鼓吹“大公无私”“财产公有”的“极左”分子么?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嘛——也许咱儒家“损人利亲”“为富不仁”的歪门邪道是个例外?存疑。不管怎样,要是尊重文本的话,你能从《墨子》那里找出诸如此类的乌托邦语句,强行命令每个人都必须“摩顶放踵利天下”吗?相反,我们看到的只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墨子·尚贤上》)的慈善鼓励,甚至还有与“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并排摆出来的“众不劫寡”命题(《墨子·兼爱中》),否定性的矛头明白指向了那些打着“为富不仁”的“革命”旗号,公然抢夺他人财产的“劫富”勾当。与“患不均”“诛一夫”之类的圣贤激进论调比起来,要是如此言说的老实人反倒被抹黑成了“极左”,你说你的“正义感”被咱儒家带进了哪条沟里了哟。
斗胆叫嚣一回:正是经过这样的反思研读,鄙人现在觉得,自己坚持的“正当主义”或“自由人权主义(liberal rightism)”(早先叫做“批判人本主义”),尤其是它主张从“正当(right)”衍生而来的“权益(rights)”旨在防止人际冲突中的“不义”之“恶”的基本理念,其实更接近于墨家“贵义”的规范性立场,反倒既有别于右翼的自由至上主义,也有别于左翼的自由平等主义。至于它与“亲亲相隐”“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他老人家亲”的儒家理念的互动关系呢,明显属于水火不容的势不两立——不好意思哦,这边厢先有礼啦,“亲”。
友情提示一句:先秦那位长得本来就比较黑的墨姓老头,由于后来一直遭到抹黑打压的缘故,连生卒年份都不太清楚,估摸在公元前479年到381年之间吧。照这样推算,上面那份捍卫私权的哲理宣言,大约已经有了两千四百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