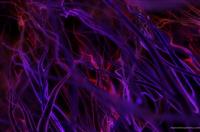
摘要:哈特的法律语言分析方法源于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观、罗素的日常语言哲学观、维持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哈特从法律语言的简洁性、法律语言的中性化、法律中抽象术语的释义法等三个方面继承了边沁、奥斯丁的法律语言观。哈特的法律语言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坚持法律语言使用的具体性和日常性;第二,反对法律范畴的定义,主张采用描述的方法;第三,注重法律语言的精准性、反对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人们通常认为,语言是受心智的控制。的确,在常态下情形确实如此。但有的情况并非仅仅如此,所以有人曾坦言:有些情况下是语言控制心智。语言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心灵活动,它还是一种常规的社会表象。所以说,人类自身的存在与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如此,古希腊才有将人类比喻成会说话的动物这一个说法。在大多数人看来,语言作为人们交流的一种工具,是表达人们内心世界的一种手段,只有符号、象征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现实,即语言属于逻辑推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而逻辑推理在结构严谨的法律规范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要求表述精确、明晰、用法合宜,切忌产生歧义,以免导致法律规范与其他制度、规范混同以及法条之间产生相互抵触。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法律规范是明确的、具体的、确定的,它往往通过成文法典以规则的形式确立下来,而道德规范是抽象的、原则的、相对模糊的,一般不以规则的形式外显出来,而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舆论的力量、传统的习惯促成。因此,坚持将道德与法律划界,选择语言分析的方式进行,这本身就是哈特等分析法学家们的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们为法治所作的巨大贡献之一。
哈特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哲学家之一、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区分“实然的法”和“应然的法”,坚持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主张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但法律有效性的标准包含道德因素等等。他以实证主义的姿态、自由主义的立场、分析哲学的旗帜和道德哲学家的情怀,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方学术界对哈特的法哲学思想评价甚高,认为哈特奠定了当代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法哲学的基础。当代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指出:“在法哲学的几乎任何一处,建设性的思想必须从考虑他的观点开始。”[1]也就是说,哈特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独辟蹊径的解读使其成为法伦理学理论阵营中的重要人物。学界对哈特法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法律规则”理论的确立以及他与自然法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富勒、德沃金的学术论战方面,对他的法律语言哲学虽有涉猎,但尚不深入,预留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笔者认为,分析法学赖以存在并发展的活力就在于“分析”,其中分析的方法又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对分析法学家哈特的法律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论渊源及内涵的阐释,其意义不言而喻。
语言分析的方法并非哈特在确立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中首创的方法。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方法也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语言分析方法与语言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密不可分,因此,要探讨哈特的法律语言观,必须从语言哲学这个元问题开始。
关于语言哲学,在西方学术界的看法各异,从总体来看基本可分为两种释义:其中一种为Linguistic Philosophy——语言哲学,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语词的含义与语词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另一种为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的哲学,它主要从哲学视角来看语言中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语言的研究意义、语言的基本特征、语言的逻辑性以及言语的行为等方面。[2]正因如此,语言哲学又称为语言分析哲学。语言分析哲学的创始人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雷格,其后的罗素、胡塞乐、摩尔、维特根斯坦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将语言分析哲学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使语言分析哲学重新回到鲜活的现实生活中,下面择其要者论述之。
(一)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观
在西方多数国家,通常将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创始人的头衔加戴于19世纪的德国人弗雷格头上。弗雷格本来是研究数学的,他在早期也一直在为数学提供可靠的逻辑基础而努力。弗雷格在研究数理逻辑中时常碰到部分哲学问题,如何处理这些哲学问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其集中在技术层面进行探索,另一种则是直面这些哲学问题,并探究这些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路径,夯实自己所进行的研究的基础,弗雷格选择的就是后者。弗雷格所关心的哲学问题主要是语言哲学传统,特别是对早期的语言哲学展开逻辑研究。他的《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一书旨在完成语言构造的纯形式化,从而为算术及可以划归算术的数学分支提供严格的逻辑基础。他认为,所有算术的基本概念都可以用逻辑概念来重新定义,同时证明逻辑推理的规则适用于所有合格的算术推理。弗雷格对数的基本概念尝试从纯逻辑的方式推出来。这项工作意义是巨大的,既为算术提供了精确细致的逻辑概念,同时也扩大了逻辑的范围。这项工作内容还包含设计一套新的人工符号系统,它要求在排除自然语言修辞的同时专注于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因此,它要比自然语言更严格地遵守逻辑规则,清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一规则要求:我们在面对算术的基本概念和推理规则时要用这套新的符号系统来表达;明确所有推理的前提,从而使一个证明过程中各个命题间的所有推理规则得到保证,使推理没有跳跃和脱节的同时也不再依赖于直觉。这些设想一旦实现,任何人都在遵循规则前提下无歧义地达到同一结论,同时也能够检验每一推理的前提和步骤。弗雷格在1982年发表了《意义和指称》一文,该文对后来的语言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被视为弗雷格“意义”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胡塞尔甚至认为,“意义”(meaning;siginficance)与“指称”(referent;reference)的区别是弗雷格对语言哲学所作的唯一重要的贡献。在该文中,弗雷格列举了许多概念,对“意义”和“指称”进行了论说,其目的就是表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在自然语言中同一个符号往往可能存有几个意义,这些情况甚至在一些理论著作存在。在他看来,每一个符号只能表现出它仅有的一个意义,如果已表现了其中一个意义就不能再表现出其他事宜,否则将使得这些含义混乱,这也是造成混乱的根源。诚然,弗雷格在对于语词的意义与分析的研究方面,并没有按照其他语言哲学家的问题。所惯用的逻辑思维来表示,他也并没有从哲学的视角去探寻语词的意义以及语词的真或必须性等方面,然而,我们必须明确,弗雷格是一位数学家,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逻辑上为算术和数学奠定基础。尽管他的初衷是为数学建立逻辑基础,但基本上不成功。然而,他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对以后100多年的语言哲学的发展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后世语言哲学所关心的众多问题都能从弗雷格这里寻找到源头和启示。
(二)罗素的日常语言哲学观
伯特兰·罗素也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受惠于弗雷格。罗素被称为是仔细研读了弗雷格著作的人,而且也是使学术界重视弗雷格思想的“引领者”,他和怀特海合著了《数学原理》。在该书的序言里罗素坦诚指出: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主要应当感谢弗雷格。但和弗雷格不同,罗素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上从理性主义转向了经验主义,也就是说从早期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向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正如D·皮尔士所指出的:“在本世纪头20年间,罗素逐步发展了他的逻辑原子论的基本思想,后来,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抛弃了某些论点,但这并不是全部抛弃。”[3]早期的罗素语言哲学主要集中于逻辑原子论,在1918年至1919年间,他撰写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一书,把哲学的本质还原为逻辑,他以逻辑作为分析工具,语言作为分析思想,相信语言分析可能揭示隐含的逻辑结构,籍此分析过程,期盼分析哲学有助于解决哲学的千年难题。罗素相信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组成的,并且可以建立一种理想语言,这种理想语言是与世界同构的。罗素主张的逻辑是原子主义的,是原子式的,认为有许多独立的事物与我们的常识和信念一样。它与那些追随黑格尔的人们的一元论逻辑相对立。他并不认为世界的明显复杂性只是在于对一个单一可分的实在的各种状态和各种不真实的划分,而是在于通过逻辑分析得到分析中的最终剩余物——逻辑原子(并非物理原子)。逻辑原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罗素称其为“殊相”,(比如很小的颜色片、声音、瞬间的事物),二是谓词或者关系等。罗素原子论的提出与罗素的外在关系说有密切的关系,罗素外在关系说的基本含义是:关系具有一种不以它的关系项为转移的实在性,关系并没有进入关系项的定义之中。例如X大于Y这种关系,并没有表明X和Y有任何共同性质,甚至跟X和Y各自的性质也无关,这种关系具有它的终极性、实在性。罗素的外在关系说导致他得出多元论,这种多元论的哲学也就是他的逻辑原子论。罗素对语言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摹状理论(有的又称为“摹述理论”)。[4]“摹状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句子进行正确的逻辑分析来解决哲学上的难题。摹状词就是通过揭示某一个体的独有属性来指称该个体的语词,[5]或者说,“它们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某个特征的描述而唯一指称这个事物。”[6]在罗素看来,存在着两种摹状词,一种是“不定的摹状词”,另一种是“限定摹状词”。当我们谈及“一个如此这般的东西”时,我们用的是不定摹状词,不定摹状词指的是不含定冠词“The”的指谓词组,比如one person(一个人)、one philosophy(一个哲学家)等等;当我们谈及“那个如此这般的东西”时,我们可以用“限定摹状词”。限定摹状词指的是含有定冠词“The”的指谓词组。如“当今的法国国王”,“《威弗利》的作者”等等。从形式上讲,不定摹状词是具有“一个某某”(a so-and-so)形式的短语,例如:“一个人”、“一头猪”、“一条蛇”、“一个苹果”等。而限定摹状词是具有“那个如此这般的某某”(The so-and-so)形式的短语,例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走进房间的这个人”等等。罗素并将摹状词置于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进行分析和探讨,进行真假命题方面的确证。使语言哲学脱离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形而上的分析,实现了语言哲学的形而下的转向,这种转向对以后的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板,并使概念更加明确化、具体化、日常化。
(三)维持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观念以及他对哲学发展的历程在某些方面与罗素有着无可替代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从早期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向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转变更为彻底。正如D·皮尔士所指出的:“维特根斯坦在本世纪20年代成了罗素的学生,接受了罗素的这些思想,而最后,又比罗素所做得更彻底,更全面地批评和抛弃了这些思想。”[7]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的观点,也是他认为一切实际“事态”(The state of affairs)的存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就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结合。但在他看来,对于思想的表述有语言与命题两种说法:第一种,语言就是人们说讲述的语句的总和,或说是社会上所有命题的总和,并且语言与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一种实在的逻辑,而实在又是各种事物的外在表现。所以,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它独特的意义,不仅能够描绘出事物的简单事态,还能描绘出事物逻辑性的复杂事态。因此,逻辑的形态与实在的形式是密不可分的。[8]这些思想在其前期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有精心的阐述。到了后期,
维特根斯坦在研究中发现自己在前期所构建的某些逻辑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他在后期改变了自我的研究风格,致力于语言的日常用法研究,并撰写出了《哲学研究》一书,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说:“我也把语言和行动——两者交织在一起——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9]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语句或命题的意义“不在于它是表现事实的逻辑图画,而在于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Gebrauch)、“使用”(Verwendung)、“应用”(Anwendung),换言之,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与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被表达的具体情况(场合)下的“用途”,一个语句的意义与它所应用的具体境况是紧密相关的。语句的用途也就是它本身在被使用的境况中所充当的角色。[10]所以他解释说:“这里的‘语言游戏’一词是需要突显出一个这样的事实——语言不仅是一种人们的生活活动而且还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11]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与使用语言(“说”)的特殊活动、目的、生活方式等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了,因而也由逻辑原子论走向了日常语言哲学的归途。任何游戏都具有各自的规则,但对于这些规则我们为什么要去遵守?对于这个问题,生活形式为我们给出了富有力量的回答。因为在每个游戏中都有属于他们自我的生活形态与形式,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游戏都具有共性,既然我们生活的充满了游戏,所以我们就必须生活在每个游戏规则当中。我们只有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才能很好地生活,不然就会被社会所淘汰。面对上述情形,维特根斯坦认为:“当我遵守规则时,肯定是我别无选择了。所以需要我去盲目地遵守这些规则,才能让我不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生活形式”也为我们遵守规则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哈特正是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启发,提出了他的“法律规则说”命题。
语言分析方法不仅在其他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法学领域同样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在这方面,边沁、奥斯丁作出了卓越的努力,并为哈特所继受。
从对哲学与伦理学有着重大影响方面而言,边沁所提出的功利性主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也正因如此,边沁在法律学说上的重要贡献受到的遮蔽,[12]掩盖了边沁在法学领域的光芒。实际上,笔者认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思想一直是边沁研究法律问题和社会改革(包括司法改革)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尽管边沁不可能接受其后的弗雷格、罗素或维特根斯坦等的语言哲学或语言分析哲学的影响,但作为一位务实和严谨的法理学家,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法律科学化的追求,并借助“语言”这一工具,紧密结合法律的实践,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确立作了不懈的努力,并使功利主义的理论言说和法律知识的技术化实践达到了真正的统一。综合起来看,边沁对法律语言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使法律语言尽量简洁和清晰
边沁首先追求法律用语的精确性。边沁认为,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思维本身依靠语言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拥有语言这个工具使人类优于兽类,同时语言具有模棱两可性,它包含了混乱和欺骗的可能性,这些混乱和欺骗同样为反叛者和革命者有意无意地利用。所以,边沁决心把模棱两可、游离不定或者含糊不清的措辞用简洁清晰的而且具有区分异同关键之处的明确的术语来表达。[13]
(二)要求法律语言的中性化
边沁认为如果将道德评价语词使用到法律用语中将会产生混乱,法律语词要尽可能避免具有褒贬情感意义的内容,在立法方面要取得进步,就必须舍弃那些“激发情感”的名称,使客观的、明晰的、中性的表达方式进入语言。他提倡在讨论法律和政治时要使用一种精确的、在道德上中性的词汇,通过这种语言和概念上的“中性”把握,使人们在面对法律问题时避免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缺乏清晰的判断,陷入一种混沌状态,边沁对法律中性化语言的关注体现在把行为的好坏判断标准从“善”、“恶”等道德标准的词语替换为明白了当的功利原则上。他认为,从一开始就必须严格区分可能是罪过的行动和应当是罪过的行动,真正应该被定义为罪过的行动应当是社会利益所要求的。由此可见,边沁的这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法律用语的中性化而确立道德与法律的边界,坚持的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路。
(三)注重对法律中抽象术语的释义
除此之外,边沁在对于语词的划分方面有具体的论述,他将语词分为抽象术语与具体术语。[14]具体而言,我们经常在法律术语中见到一些诸如权利、义务、责任等抽象术语时,往往无法给其准确的定义,也不能使用简单的术语(simple terms)来进行替换时,可以用“释义法”(paraphrases)来解决,即将这些包含了某些抽象术语的句子转化为另外的一个句子,并且转化后的这个句子使用的语词都是易于表达、容易理解的简单概念。笔者认为,这种释义的方法秉承的是古罗马法以来的注释法学的风格,而且这种风格在边沁以后的实证主义法学家如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的分析法学中均可以找到明证,尤其是哈特使用的对法律的“描述法”可以说与此一脉相承。
奥斯丁则是将语言哲学与法律实践紧密结合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强调法律用语的精确性,另一方面钟情于法律语言的世俗性、日常性。[15]他的法律观和边沁的一样,对其继承者和捍卫者的哈特有着同样重要的启迪。
正如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的序言中所述:“因为探究文辞的深意并非总在于了解文字本身。各类型的社会情境或社会关系之间,有许多重要的差别并非昭然若揭。唯有透过对相关语言之标准用法的考察,以及推敲这些语言所处的社会语境,始能将这些差别呈现出来。特别是因为使用语言的社会语境,往往不会被表明出来,更显出此研究方式的优越处。在此研究领域之中,诚如奥斯汀所言,我们确实可以借由‘深化对语词的认识,来加深我们对现象的认识’。”[16]关于这一点,他在《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的“导言”中也有提及。自从1953年发表第一篇法学论文《法理学中的定义与理论》起,哈特就自觉地运用了言语的含义与力量之区别的理论以及有关“言语行动”(Speech Acts)理论来分析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归纳起来说,哈特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是语言哲学(又称语言分析哲学),承继的是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日常语言分析方法、边沁的“释义法”及他们对语言的精确化要求,追求的是法律与道德分界的价值目标,捍卫的是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笔者认为,他的语言分析法的具体运用及主要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法律语言使用的具体性和日常性
在哈特看来,客观世界是一种现实存在,并且是一种复杂的客观存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和多样性使得法律制度同样具有多样性和具体性的特征,这也使得语言的阐述往往与标准的情形存在差异,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应该考虑到具体的语境情形,并采用日常化的语言方式进行说明,以使其不模糊。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哈特认为的客观存在的复杂性与日常语言的分析是同质的东西,在阐述法律问题时要采用日常语言的方法。在言及义务、法人等法律范畴时,他觉得如果只是仅仅给出一些示例,而缺乏明确的说明,是不能使人明白的,因为困惑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虽然这些词汇的一般用法已经被熟知,但与绝大部分日常用语相比,法律词汇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变异性。[17]在他看来,这些法律词汇与其现实中的对应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日常用语就不一样了,绝大部分在现实中都直接联系的对应物,而且在定义日常用语时,也会指涉到它们。因此,在哈特看来,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不管什么语言,都应该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这样才会具有价值。相反,如果偏离了标准情形,就会使人不能理解而引发无休止的争论。而法律规则与其他规范相比,要求词句更加准确、具体而容易看懂,不能模糊不清,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加入个体的价值考量标准。所以,词语在法律规则的使用过程中更加要求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
(二)反对对法律范畴的定义法,主张描述法
边沁的“释义法”对于哈特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对“释义法”的探讨,哈特认为在法律领域我们需要一定的描述,不能只靠简单的定义。而描述方法是指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哲学来对法律中一些特有名词以及某些法律现象进行一定量的描述和释义的方法。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法理学中的定义与理论》中。在该书中,他认为法律这种社会现象涉及的论题很多,譬如说国家、法律、权利、占有等等,分析法学的主要任务和使命就是要通过精致的语言分析将这些长期困扰法律人的论题表征出来。如何精准地界定这些范畴?很多法学家或者法哲学家通常是采用定义的方法进行,哈特另辟蹊径,他认为采用定义的模式会使得人们对法律的阐释更加复杂、更加使法律不可捉摸,甚至会导致法理学和现行法律研究的离异。[18]他在回忆起自己写作《法律的概念》提出:“对于本书的轮廓,我的脑子一片模糊,太模糊了。我的最大的野心是永远清除那种或那些‘定义欲’,即追求对法律的‘各种定义’。”他认为,唯有通过对构建标准法律制度的主要因素及要素的结构进行确认识别来描绘法律的“概念”,这才是分析法学家应该秉持的学术气质和正确方法。对法律制度描述使得法律人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通过对法律的描述,使得我们能够处理那些充满怀疑和不确定性的不标准情形(如国际法),因为唯有通过描述性的方式,才能使枯燥、隐形和过于专业的法律用语在抽丝剥茧的分析下重获生命力;其次,使得人们进一步深化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更加全面的解读。”[19]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的“后记”中也对此作了深入说明,他说:“在这本书中,我的目标是要提供一个一般性及描述性的关于法是什么(what law is)的理论。这个理论在以下的意义上是一般性的、即它并不关联于任何特定的法体系或法文化,而是要对‘法律’,作为一种复杂的,包含着以规则进行规制(rule-governed)[且在此意义上是规范的(normative)之面向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做出阐释和厘清。”[20]为了更好实施描述法,哈特选择了两种说法来为其铺垫:第一,由于受到边沁对于法律语言思想的影响,哈特选择了中立的表述方法,认为法理学就一个价值中立的理论架构。哈特在《法律的的概念》认为:“我的说明之所以是描述性的,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不以任何证立为目标;它并不寻求通过道德或其他的理由,去证立或推荐我在一般性说明中的描述法律制度的形式和结构。”[21]这也是哈特在评价德沃金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武器,因为在他看来,德沃金所设想的法理论是部分的评价性和证立性的,并且“指向特定的法文化”。[22]第二,哈特对于法律规则提出了内部与外部之分。哈特认为法律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仅只表达了人们对第一法律规则的接受程度,更多是表现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取向问题,并且还认为使用法律语言与我们平常玩的游戏如板球比赛相类似,“板球选手已出局”,这类似话语的表述是有效的,其所以有效,是指该说话人以及参与人或观看者都已接受了这种表述与规则。与此相适应,法院或其他司法人员在鉴别法体系的特定规则时,使用没有经过明确表述的承认规则表明这是一种内部观点的证明是同样有效的。如“法律规定如何……”的“内部陈述”,这是持内部观点的人最常用的表达语句。和比赛裁判一样,“内部陈述”是没有必要说明理由的,因为这种“内部陈述”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即其将自己角色定位为参与者,从内心已经理解并接受认可了规则,从而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在英国人们认为凡是女王议会通过的就是法律……”这是外部观察者进行的常用表述的外部陈述,显然这位旁观者只是陈述他人接受法律规则的事实,
而这位观察者自己内心接受或者不接受该规则没有表明。
在边沁的立法科学化和奥斯丁法律语言精确化思想的影响下,哈特在构建法的体系过程中,对于法律用语的准确性、清晰化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有学者认为这与哈特二战期间从事过情报部门的工作有关。这个因素固然应该考虑,但更主要的是他对于边沁和奥斯丁的法律语言精确性要求的推崇有关,他曾在《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一书中强调:“然而,在第三篇文章中我主要的关注在于捍卫如边沁和奥斯丁那样的一种明智的主张,也即实然法(law as it is)与道德上的应然法(law as morally it ought to be)之间的区分;反对形形色色的认为法与道德之间存在着许多概念上的、必然性的而非偶然性的联系的主张。”[23]在《法律的概念》的“前言”中也说:“诚如奥斯丁教授所言,我们确实可以借由‘深化对语词的认识,来加深我们对现象的认识’并举例说,比如‘被强制的’(being obliged)与‘有义务的’(have an obligation)之间、‘一项有效的法律规则’与‘对于官员行为的预测’之间有何区别等”,哈特认为“倘若不能鉴别出它们之间关键性差别,就不能理解法律,亦不能理解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结构。只有精确的分析才能够令人吃惊地阐明事物并激起我的兴趣。”[24]
为了使法律清晰明了,哈特对分析法学的实证主义传统进行了超越。首先,用“法律规则”说替代了之前实证主义法学创始人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的观点。其次,为了避免“法律命令”说中用词不准、模棱两可的问题,哈特对“法律规则”又作了更加细化的分类,他将法律规则分为“第一性规则”(又称为初级规则或者义务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又称为次级规则或者授权性规则)。第三,他还将第二性规则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承认规则,第二类是变更规则,第三类是裁判规则。如此一来,所有的法律制度均以规则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第四,法律规则解释虽然以规则的形式外化出来,但是有可能在操作层面上遇到执行上的障碍。为了解决规则和执行“两张皮”的问题,哈特基于“承认规则”中间存在的不确定性和“规则怀疑论”提出了“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和不谬性”的观点,并主张以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化解,从而使法律规则中的“阴影地带”和“模糊性”降到最低限度,使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和整体统一性提升到最高程度。
参考文献:
[1]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6.
[2]参见王路:《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
[3][英]艾耶尔等:《哲学中的革命》,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页。
[4]参见李金辉:《罗素分析哲学的逻辑表达式》,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5]参见李志才等:《逻辑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3页。
[6]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7]前注[3],[英]艾耶尔等书,第23页。
[8]参见[奥]L·维特根斯坦著:《逻辑哲学论》,张申府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27页。
[9][奥]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7页。
[10]参见万俊人: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11]前注[9],[奥]L·维特根斯坦书,第23页。
[12]参见[英]边沁著:《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0页。
[13]See H·L·A. Hart,“Introduction”, in Essays on Bentham: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82,p. 8.
[14]See Timothy A·O·Endicot,“Law and language“in Jules 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c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ce and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 41.
[15]参见杨玉成:《奥斯丁: 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5页。
[16][英]H·L·A 哈特著:《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2页。
[17]参见[英]H·L·A 哈特著:《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8]参见前注[17],[英]H·L·A 哈特书,第23页。
[19][英]妮古拉·莱西著:《哈特的一生: 噩梦与美梦》,谌洪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20]前注[16],[英]H·L·A 哈特书,第22页。
[21]前注[16],[英]H·L·A 哈特书,第22页。
[22]参见前注[16],[英]H·L·A 哈特书,第22页。
[23]前注[17],[英]H·L·A 哈特书,第9页。
[24]前注[19],[英]尼古拉·莱西书,第130页。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基建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