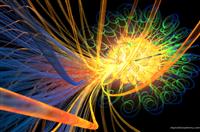【摘要】清末洋务工业化运动,由于落后生产关系与相对先进生产力的悖离,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折腾后最终归于沉寂,被世界誉为“亚洲第一雄厂”且为大清帝国第一家股份制改制企业的汉冶萍钢铁煤联营公司仍然难逃倒闭破产的厄运。缘何自近代洋务始的国有企业均易短祚而亡,一直为学术界所重。清末政治精英与商务精英们共同创设了汉冶萍公司,但由于其晚清帝国近代化先天准备不足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政缺失,在西方列强武力与资本裹挟的双重夹击中崩俎。本文意欲以汉冶萍为范例,寻绎晚清民族自强求富与变法救国宪政缺失的内在原因。
引论
近代洋务工业本是本着工业救国初衷而破题的,可是缘何又不能扛起实业兴国的大旗,甚至只能堰旗息鼓短祚而亡,多年来一直是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的一个难解之题。洋务初期的系列富国强兵之实业,在论到为何失败关键处,清廷总是托言“事实秘密,未能详知”而最后不了了之。民族企业生存的民主科学土壤与社会制度环境氛围不足、法律章制规范不足、人才培养储备不足、本土资本金准备不足,都是曾经的答案,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社会法律制度规范支持的缺失上寻找根由。
研究汉冶萍公司及其主要人物,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历久不衰的课题。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费惟凯在其《19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汉冶萍案例》一书中提出,汉冶萍公司“是中国为工业化所作努力的缩影,也是后来民国官僚资本的前身。”它的兴衰源自于它那个时代法治规范的缺失,那个国家整体宪政制度的全无。换句话说,晚清的工业化努力没有配上国家法制建设和宪政努力的套。经济上变革乘坐的是火车,而政治上变法革新则是赶着驴车。一个完全不匹配的路数。他认为,这个“本来可以为国库生财、为民生舒缓、成为财富源泉的特大企业”之所以被断送,是因为它“自闭自封、不容许外人经营管理这个企业”,加上无最基准的公司法规,导致长官意志统驭企业而滥经营,最终为日人所控制{1}。日本学者中村义在谈论盛宣怀主持汉冶萍时说,在清末的政治史上,盛宣怀“仅仅是靠着一点与列强的联系来维系着个人气息奄奄的政治生命”和企业生命,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浮在大清国表面上的巨大泡沫而已。”{2}由于这些学者置身域外,不免受到种种研究条件的限制。依笔者愚见,发轫于19世纪70 - 80年代的洋务自强运动,他们所作的近代工业化努力,包括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张之洞辈曹,有几个不是像盛宣怀一样,是依附在晚清帝国虚华泡沫上的繁荣,因为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或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那种最根本的宪政制度设计和相应的法律规范近代化管理,致使国企的投入甚至股东的资本变成官员升迁的资本和官员的花翎。
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创建炼铁厂,继而在大冶兴办铁矿。三年之后,这座标志着近代中国最具现代化特征的钢铁企业诞生,铁厂竣工投产。此后,受任接办汉阳铁厂的盛宣怀,在江西萍乡开设煤矿。1908年,经清廷农工商部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自此,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用世界一流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兼集采矿、冶炼、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1]“大冶之铁,既为世界不可多之产,而萍矿又可与地球上著名煤矿等量齐观,是汉冶萍不独为中国大观,实世界之巨擘也。”[2]其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它的兴衰,基本上反映了近代中国钢铁工业近代化的历史,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单纯从公司的联营体制和公司章程关照汉冶萍公司可谓是中国最早的复合型股份制企业,包含的国有、商有和民间资本股份,并且在不同时期所占股份都呈动态状,始终变化着。诸如官办时期、官督商办时期、官商合办与商办时期股份变更和比例占有是大不一样的。而所持这种股份发展动态的背后却始终没有最基本的公司法进行规制和管理,往往依靠的是个人的官品权威或是传统把头式职权来管理联合企业,显然与国外的大企业相较,就差了一截。
汉冶萍企业的催生孵化是与中国早期近代化洋务工业同步的,他们几乎怀着同样的富国求强的政治愿景和民生诉求,肩负着同样的发展民族工业近代化的使命感,诚如马建忠所言“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其公使傲睨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3]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出一批带有某些激进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官绅代表人物,形成了一个标榜“自强求富”,要兴办“洋务事业”的封建官僚集团,在工业技术上摒弃将西方的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井蛙之见,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法治思想和政治理念上,大胆吸收和移植西法,从国家法(宪法)到经济法,鹜赴云集般地兴办了江南制造局、汉阳枪械厂等10余家军事工业和上海轮船招商局等20多所民用工业企业。由于钢铁工业的落后,这些企业所需的钢铁原料全部依赖进口,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使得腐朽不堪的晚清王朝,更显得国力竭蹶。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洋务最具影响力的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铁器之器。”[4]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开办河北磁州铁矿,但因运道艰远,加之购买英国的机器设备不全,只得作罢。1875年,接受李鸿章密谕饬查中国地面产煤铁之区的盛宣怀,在湖北发现大量铁矿之后,遂在广济盘塘成立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光绪十一年(1885年),贵州巡抚潘开办清溪铁厂,经过5年多的建设,投人试产。终因运输不便,资金不足,燃料缺乏,加之经营管理不善,进展一个半月就被迫停产。连续两次的铁煤之开发均告失败,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原因是显见的,但政治制度的深层原因,晚清政府却总是不愿涉及。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痛感“凡武备所资,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需,无一不取资于铁,开办铁厂可以塞漏、开利源”(不论海防、塞防和民生均需铁产),遂有意开办铁厂。在此期间,清廷就修筑铁路发生了争论。醇亲王及张之洞等人提出修筑卢汉铁路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清廷的支持。随着铁路的兴修,自办煤铁便成为当务之急,“开发此等矿山,为不可或缓之图。”张之洞提出,“欲修铁路,必先制轨,制轨必先设铁厂,否则事倍功半”。清廷深以为然,嘱其委托驻外公使,购买比利时科克里尔厂日生产铁100吨的高炉两座和其他配套机器设备,准备在珠江南岸的凤凰岗择地设厂。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南段。
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广东铁矿贫乏,且营建厂房及购置机器的费用庞大,绝不是广东财政所能负担”为由,奏请将尚未运到的机炉,径运湖北或直隶。李瀚章上奏后的第13天,(1889年12月),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三天后便致电海军衙门及李鸿章,要求将铁厂移建到湖北,很快就得到清廷的批准,并由户部拨款200万两库平银,作为建厂经费。踌躇满志的张之洞,将在广东所定购之熔铁炉移到武汉,立排众议,将厂址定在楱莽丛生的汉阳大别山(今龟山)脚下。“汉阳铁厂之创设,此为取法欧美钢铁冶炼工程之嚆矢。”{3}也是晚清政府最大投资近代民生工程落户武汉的标志。
笔者曾经翻阅汉阳铁厂的厂志档案,其于光绪十七年八月(1891年9月)破土动工,经过两年又十个月的施工,于光绪十九年十年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竣工,这一年也是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为湖广近代工业化培养人才。经过半年的试车投产,一些问题接踵冒出,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焦炭不足。当时,国内能炼焦炭的煤矿,仅开平一处。在湖北境内开办的王三石煤矿,因水势过大而停闭;马鞍山煤矿虽然出煤,但含磺过重,须参用开平焦。“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及杂费水脚,需银十六七两。道远价昂,又不能随时接济。”[5]不得不购买英国、比利时等国的“洋焦”。因此,高炉时开时停,基本上不能正常生产,看来这一问题同样困扰了中国钢铁工业整整一个世纪。汉阳铁厂的总投资在588万两库平银以上,投产后两年间开支达160万两,而销售额只有24825两,仅占开支的1.6%。偌大的汉阳铁厂进退维谷。恰在此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既付出了巨额费用,又须交付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费,库空如洗,无力顾及入不敷出的汉阳铁厂。甲午战争的影响对近代中国而言不仅仅只是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政治层面和转型的变法要求的刺激。面对这个沉重的打击,张之洞顿感“心力交瘁”,便下决心实施其早已拟定的“经久之计:将铁厂招商承办。”[6]然而,鉴于当时国内资金技术现状,更主要是懂得企业管理的本土人才凋零,使得他不得不反复冒出“华商力薄,不能任事”、“中华绅商,类多巧滑”的念头,同时致电清廷铁政局总办蔡锡勇:“铁厂仍以外洋包办为宜”。消息传出,遭到众人反对。湖南巡抚陈宝箴致电张之洞:
衡州、湘潭均有佳煤可炼焦炭,正议开采供铁厂之用,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用怅然。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危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公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宜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想公必早见及。或其中尚有屈折,或合办定有年限仍可归还,外不及知?然究不如请借洋款为得。如公苦衷难可共白,箴虽人微言轻,当力陈之。乞示复。[7]
陈氏认为铁厂包与洋人,与公初意不大符合,而正是民族发展用铁之际,为张之洞,也为清廷王朝“甚为中国惜之”。至此,张之洞便驰电李鸿章说,包与洋人之议,“已作罢论矣”。这个时候的张之洞一方面考虑到与洋人合作,充分利用洋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一方面有迫于时下同僚的牵制和清廷的压力,从张之洞写给欧洲四国公使刘瑞芬使节的信函中可以窥到其在万马齐暗人才匮乏国情时局下对科技人才队伍渴求的心迹:
请代觅铜矿师一名,须精矿学、化学、善测矿苗,兼晓煎熔,曾著成效。确有把握者,即与订合同,饬速来粤。应用探矿钻具及考验矿质各器随合同带来。费,电示即汇。又恳代查开铜矿并兼熔机器全副价若干,并赐复,此系琼州用。洞。养。[8]
常言道,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命脉。任何时候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古今中外无例外者。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经理。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他对盛宣怀大加赞誉:“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而被称为“合肥相国左右臂”的盛宣怀,一方面向李鸿章表示,“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以示不应张之洞之招而一心追随李鸿章之心迹(其时李鸿章手握北洋海军重权,盛宣怀对权力同样充满热切的期待);另一方面,对张之洞抛出的绣球,他又很难不为所动,便积极地向张之洞出谋献议。后终因在厂址厘定问题上,与张之洞发生分歧而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暗结。不过,盛宣怀仍时时关心铁厂的情况,并酝酿相机接办。在得到耳目通报的消息之后,盛宣怀就向张之洞表示愿意赴鄂,“通筹决策”。张之洞则立即上奏清廷,说:“盛道才宏达,综合精详。”并明确表示,接办汉阳铁厂之人,“非盛莫属。”张之洞此时完全表现出一位能臣的干练与胸襟,为了清帝国的钢铁煤一体化近代企业雄厂大厦不倒,为了洋务大臣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荣誉和尊严,在湖北,汉冶萍,已经从程序和实体上解除了晚清帝国封建落后章制规定的诸多旧弊,在地方经济发展平台上率先讲求行政效率和民生经济的增长指标。
可好景不长,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5),汉阳铁厂作为国有全资的近代化企业率先作了公司发展进路上的重大改革,
虽然当时缺失公司法,也无系统化的公司章程,完全听凭长官意志,但此次公司改制是划时代的。由过去的官方包办一切而变为“官督商办”,即官方不再行经营管理事宜而交由市场化的商人主办铁厂事宜,政府唯行“督导”之能,从而给这个濒临衰竭的企业注入了些许的活力。从这则清廷《上谕》中,或能够寻绎晚清工业近代化在经营方式和利益分配为何变革的端倪,其实,此乃为中国最早仿效西方国家将官府企业与官府(政府)脱钩分离。
上谕:前因给事中褚成博奏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当经谕令户部议奏。兹据奏称:“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赡军火;平日工作不勤,所制不精,已可概见。福建船厂岁需银六十万,铁甲兵舰仍未能自制;湖北枪炮、炼铁各局厂经营数载,糜币已多,未见明效。如能仿照西例,改归商办,弊少利多”。
制造船械实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南洋各岛暨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富商在彼侨寄者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著边宝泉、谭钟麟、马丕瑶遴派廉干妥实之员,迅赴各该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徕,该商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赀认充,或予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宫款维持。其办理章程应如何斟酌尽善以杜流弊之处,即著该督抚等细心妥筹,详晰具奏。[9]
此后,其经营与生产较之以往,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生机。过去一直无法摆脱的两大难题,即缺乏煤焦和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随着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和铁厂机炉的新技术改造,都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在张之洞、盛宣怀的一再要求下,清廷也采取了某些法律规范上变更措施,诸如任命盛宣怀督办铁路;规定铁路所需铁轨均购之于汉厂;批准其产品减免税厘,等等。这些,对汉冶萍联合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起了一定的推动和刺激作用。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勉强维持了10余年,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许可及经济根源深层的弊端还是未能完全克服。正如严复在翻译《国富论》按语中所说,官督商办只不过“盗西法之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无一实效之可指”。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取得民族资本家的信任,或缺社会民众的真正参与,生产经营上缺乏一定的民主意识表达和科学管理,无疑民间本土资本很难集中,人股者寥寥无几也是自然的,从而导致庞大企业资金链的绷断,扩大再生产规模无望。国人的投资意向绝对取决于对现行官府的信赖和信心。因此,盛宣怀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奏请清廷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成立汉冶萍煤铁厂股份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汉冶萍公司是为亚洲第一雄厂,也是中华封建帝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我们从汉冶萍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决议中便不难发现其时代烙下的近代化特征和法律章制规范运行的缺失。
汉冶萍公司作为民族工业近代化的标志,在初期的改革上还是成效大显:招附新股1300多万元,部分地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三大厂矿的生产规模,逐年扩大。到宣统三年(1911年),以年产量计,汉厂产钢38640吨,萍矿产煤1115614吨,冶矿产矿石4441812吨。民国三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钢铁市场价格暴涨。列国工厂停顿,制造航轨器械,纷向汉冶萍定购,该公司供不应求。这种局势极大地刺激了公司的生产,使公司获利甚丰。上海的《万国商业月报》登载译自德国报端文章说:
铁厂烟囱凸起,插入云霄,屋脊纵横,盖于平野。化铁炉之雄杰,辗轨床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股者,是为二十世纪亚洲之雄厂耶!公司还不失时机地购置开办了一些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外合资企业以备民生之需,并由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10]
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急剧下降,致使公司产品严重滞销。盛宣怀早在接办时就曾指出的“总办不得人,洋匠不用命,百弊丛集,散漫杂乱”的问题,意即公司高管层面不法不智,延聘的外籍工程师又不用命履职,公司职员之间没有统一的企业文化理念和经营管理制度规范,龃龉不断,厂矿一级高层官员间的相互攻讦怨尤。更不可恕的是员司匿请舞弊,“侵款自肥”成为汉冶萍公司的家常便饭。总之,在今天所看到的国有企业诸多腐败现象和舞弊手段,在当时的汉冶萍均能看到。这也说明我们国企的贪腐,国有资产的流失由来有自,大有渊源。被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称为“办事亦有血性”的汉阳铁厂洋总工程师吕柏也说,铁厂的大小官员们“只想着如何去满足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工厂的兴衰对他们来说,就像宇宙中最遥远的恒星距地球那样远。”由于管理缺失章法规制,加之官方行政化替代技术化而最终导致事故迭出。斥巨资引进的大冶铁厂的1号高炉开炼仅10余日就因事故停炼。2号高炉投产2年,又因煤焦不足而停产。当时国内仅有的两座日产量为450吨的高炉,总共只生产了26个月,生命之短祚为世界所罕见。民国十四年(1925年),大冶铁厂的高炉全部停产。从民国十年(1921年)起,汉阳铁厂停止炼钢,三年后,3号、4号高炉停产。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萍乡煤矿被江西省政府接管。至此,公司开煤、炼铁两大端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大冶铁矿一处仍然在继续生产,中国唯一的钢铁企业,变成了供给日本重工业原料的基地。“本应该位列亚洲前茅的近代钢铁煤一体化巨型联营企业,为何短祚而亡,其国家应该担当的责任或是法治缺失,是今之官与商不得不认真思考的。
汉冶萍公司在命舛运赛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维系了58年。当它崛起在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上时,国人无不为之振奋:”阳夏一厂,冶萍两山,为全国富强命脉所系。“[11]然而,它却始终步履蹒跚,最终不可避免地还是走向晚清洋务工业化失败的同一归宿。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汉冶萍钢铁煤联合企业,从它的高调催生到黯然出局,其本身亦克服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人类近代工业文明的过程本是痛苦的,而像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的工业化发展更是要付出或承担更多的痛苦和代价。小而言之它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的担当,大而言之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担当。汉冶萍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总共生产铁矿石1400多万吨,生铁240多万吨,钢60多万吨,煤1500多万吨,焦400多万吨(煤统计到民国十七年,焦统计到民国十三年),藉此在中国钢铁煤工业史上铸下沉重而悲怆的辉煌。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根本不可能产生世界一流的企业,换句话说,没有先进的国家民主宪政文明与法制基础建设,也根本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化成长与出路,这就是国家与民族的悲情。
近一个世纪来,学者们对汉冶萍公司破产的原因和经验的总结,在心理上一直感到十分纠结:国家或政府的体制之误招致企业从诞生之时在成长的进路上就沟壑丛生,处处受制。人们往往会从一个企业自身内部管理寻找原因,很少从更宏观的视野寻医企业的病根。笔者以为李维格在《汉冶萍公司历史说略》一文中将其原因归纳为5点是比较中道客观的:
东亚创局,事非素习,自张盛二公以及二公前后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暗中摸索,何能人室登堂?官款不继,后招商承办,……又以张公铸成大错,……指摘之不遑,何来附股?及至三十四年新厂告成,铁路渐兴,始有大批股份投入。然迄今仍债多股少,不但付利,兼须拨还债本;事未办成,何来余利?而华商股款附入,官利即起,岂有难如制铁事业,方在购机建厂,而即须付利;汉厂之大希望在路轨,及各路开工而洋厂竞争,各国保其本国钢铁事业,加重进口税,使外铁不能侵入。中国不但不能加重,并且值百抽五之轻税亦豁免,且铁路洋工程司于汉厂之轨种种留难,以达其外购目的;萍矿之大希望在合兴公司之粤汉铁路,而当时赎路风潮剧烈,卒至废约,停顿十余年,萍矿间接直接之损失不知凡几。
当然,李维格作为局中之人,且著文于民国初年,所以备受研究者所重。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司长胡庶华也认为:”吾国钢铁事业,首推汉冶萍公司,其失败原因,皆由于办理之未善,兼之连年军阀斗争,颇受影响,复因欠日债关系,处处都受日人之操纵与牵制“。[12]同时,也有人认为,由于地方大员张之洞的好大喜功,在湖广急于建树政绩的心理,在既无煤又无铁的汉阳建厂,其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稍后,民国时期隶属于湖北省政府的清理汉冶萍公司债捐委员会(相当于现代的公司破产后的资产清算委员会),则在公司经营实体上给予了全盘否定,称其之为一个”废官黯侩之集团“。《辞海》”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条,归结为经营腐败、连年亏折以及举措外债,导致大权旁落。其实,时人作上述归结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从更全面的视域以观,或可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值得指出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起,洋务派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无一获得持久的成功,原因何在?从清廷总理衙门到地方封疆大吏,很少有人去理性地反思和检讨真正的原因。后人也就一般地机械地持取历史教科书中的肤浅观点:他们引进、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企妄在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统治下来改善民生,发展生产力,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而对一个国家政体国体之最基本的政治体制制度及其相关的宪政法律价值是否与国家的近代工业化发展愿景相称不愿作任何检讨和思考,更不愿反思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等这些洋务派官僚,”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在实际上悖离了这一规律。他们丝毫也不想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甚至连某些环节的改变也不愿意。“{4}这就人为地造成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含生产工具厂房)同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巨大矛盾。这种情形,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其结果,只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着的。
晚清社会本是天崩地解的转型社会,民主宪政法治思想如晨曦般地朦胧而至国民心,纯粹儒家学说和道德信念已经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击得摇摇欲坠,而朝廷和地方精英所主张和追求的宪政图景或模式却又遥远而飘忽不定,清廷的宪政之旅或者说《钦定宪法大纲》所关涉的近代工业化及民生发展条款极为空泛,由是,从清末到民初,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企业)很少有规范健全的法律章制,这不能不说与其国家没有统一上位法(宪法),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一个国家的宪法统一着全体国民的根本意志,也统御着林林种种的法律法规精神及司法层面的价值取向。而宪政则是动态的宪法,实施中的宪法。遗憾的是汉冶萍作为晚清洋务工业化运动的代表,还是未能赶上宪政发展的趟:是汉冶萍公司联营产业基地孵化的不是时候,还是中国宪政发展和努力实在太迟缓?
其实,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肇起之初就曾引起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不满。著名的洋务政论家王韬,曾公开批评洋务运动是”末者徒袭其皮毛,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指出,它”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13]像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盛宣怀等人,当然清楚这个”本“所指什么。但历史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价值趋向—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头来只能是对其皮毛的徒袭。因为根本的制度设计与国家体制革新改造,本质上就不再是洋务官员和地方大吏检讨和思考之事了。
汉冶萍公司同洋务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她既是洋务的一部分,又是清廷晚期洋务运动命运的终结者,亦可称”洋务运动之绝唱“。它同洋务运动初期创办的一系列官办企业如出一辙,不是先天营养不足,就是后天或缺统一的民商私法观念和管理规范。企业间或是员工间或是企业部门间的商业行为仅仅仰赖于某种交易习惯和拍胸誓言表达,
而却没有西方国家视为贸易准绳的民法通则或公司部门法则。汉阳铁厂投产后不久,就爆发了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中日甲午战争。这就在客观上使汉阳铁厂成为洋务运动的谢幕剧。汉阳铁厂的一号高炉也随黄海海战北洋水师的最后一声哑炮闷响而轰然倒下。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站在了走向必然倒闭的起跑线,几乎可以这样认为,汉冶萍公司带着摆脱不掉的近代洋务工业化的烙印,沿着自己生产出来的铁轨,一步步地驶向破产,有如清廷在仿行宪政改良保皇道路上自己设置的路障一样,阻死一条路,另一条却为其徐徐打开。
对汉冶萍为何短祚而亡的理性反思,应该放在民族早期近代化的历史变革大背景中审视。如果从纯粹的近代化实业救国论或是洋务运动的利益得失上关照,那也会有所偏颇。在客观上,汉冶萍联合企业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化的追求和努力实践中,无疑起到了开启中国官方资本、民间资本合和协同办大事的先河,从公司及公司法意的历史借鉴意义上言,它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傲然人世以及选择悄然离世无不与它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国家民主法治运行状态息息相关。例如,它揭开了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市场的垄断等等。所有这些历史特点和贡献,在汉阳铁厂身上也有着明显的反映。汉阳铁厂在官督商办以后,部分地吸收了私人的投资;经营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其产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企业的劳动力,也都是处在劳资关系下的雇佣工人;厂方任意地延长劳动时间,酷热季节仍要作满12小时;在大冶铁矿,还雇佣童工,”工人中多童子,年仅十龄者,肩土一担,得钱二文。“[14]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生产关系及其特点十分明显。不管是主动的抑或是被动的,汉冶萍在清末民族工业近代化过程中也曾对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过力所能及地改善,且重点讲求了一个”实“字。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没有像其他洋务企业那样,并以那样的悲情模式夭亡。这里从总理衙门与张之洞的电文中往来可察其一番秋色:
总理衙门电张之洞:奉旨,近闻湖北铁厂采煤合用,大炉业已烧通,每年可出快枪七八千支,铁轨尤易铸造。张之洞经理此事,历有年所。著将现办情形,切实复奏。如经费不足,亦应确切直陈。现在时事多艰,中外大臣,宜讲求”实“字。总之,毋妄费,毋受欺蒙,方有实绩。该督其深体此意。钦此。铣。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1895. 11. 2)
三天后,张之洞回复总理衙门电,表达悉心遵办汉铁及其枪炮厂的心志和筹集经费,感悚莫名,又不得不克服困难的个人努力恭读十六日电旨,感悚莫名。铁厂、枪炮厂现办情形,并筹计经费,洞于八月二十八日谨分三拆、两片具奏,计已上达。洞才庸智浅,惟有矢此愚诚尚堪自信,敬当懔遵圣谕,事事求实,不敢妄费,不容欺蒙。窃思此两厂,事多相连,招商总不甚便,似仍以寿款官办为宜,请代奏。之洞肃。效。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1895. 11. 5)
很多人在研究汉冶萍公司从兴建到发展继而衰亡的过程中,轻易便下这样的结论:汉冶萍的夭亡主要源自晚清民初政府体制原因、官僚管理混乱、人才匮乏、经费困难四大原因,更有甚者对晚清洋务官员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横加指责,认为主办者个人敬业精神不够、玩忽职守、对市场经营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导致了民族资本市场及近代洋务企业短祚而亡,汉冶萍也不例外。对历史的结论和法律意见的给出,必须依据理性证据。现有的事实和证据还真不能证明汉冶萍主要倡办人张之洞,包括盛宣怀有多少职务懈怠,经世平庸。从而或能促使后人其他原因上去检讨和思考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化发展缓慢受制的深层因素。
首先,是晚清没有形成培育民族近代工业化的土壤,或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制度的基本氛围,也就是说晚清社会本质上只有宪政表层的丝丝努力,决然还没有实现宪政基本政治制度和国民行宪法治的强烈诉求,国民缺乏最基要的法律思想、法律道德、法律伦理和法律精神。自始便会招致来自清廷皇权和中央上层封建官僚的抵制与反对,因为他们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宪政制度,有自己的认识,盲目以为中国近代化游戏规则应该任由清廷制定。如李鸿章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土之上,无须变革。所不及者,独火器而已“。[15]再如盛宣怀,在戊戌变法中,他主张”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到清廷朝野搞立宪运动的时候,还企望”但求宪法顾得住君权“。因此,他们创办的企业,经费多由皇室府库拨充,劳动力多以地方官吏以劳役形式征用。在管理上沿用封建作坊的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上一个工厂就像一个衙门,等级森严,劳苦工人处处受把头和官吏的压迫剥削,对外国技师工程师,缺乏起码的尊重和科学态度,在心底深处抵制西人的”奇技淫巧“;在市场经营上,毫无自由可言,企业尚无自主经营权,项目研发权,只能依据清廷旨意统驭计划经营。而近代工业化强调的是西方科学技术普世应用和市场自由化,企业管理的民主法治建设恰恰是实现之的唯一路径和保障。因为宪政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国民民主自由权的充分享有,国民私权对政府公权的限制,即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是也。在汉冶萍公司经营管理链条上,最为缺失的就是企业自主经营权,企业民主的决策权和公司股东权利对官方行政权力必要监督和限制权。即使到了商办时期的《汉冶萍公司章程》也是形同虚设,毫无公司规制之法定效力,哪怕是基本的公司人事任免还须看清廷脸色行事,”伏乞圣鉴“。
其次,为外国列强武力裹挟资本的入侵与对我民族资本的侵占掠夺。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外国列强以武力裹挟资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转契和历史拐点。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各国,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商品输出,他们无意使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壮大起来而成为商品竞争的对手,而是日益注重资本输出。其目的,就是要瓜分中国市场,更多地攫取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得到了一时的缓解,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出现了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汉冶萍公司也不例外,其生产和经营有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好局面。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势力便卷土重来,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泡沫迅速地走向消解。这一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人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5}以汉冶萍为例,在1915年,仅日本人就从该公司掠走钢铁煤焦价值白银近二百万两。而查是年收入厂矿营业:”于汉冶项下,共收各路轨价、矿石售价、各户钢铁料价等一切,计银三百十六万七千四百余两;萍矿项下共收生煤、焦炭共计二百八十六万七千一百两“。[16]日人通过资本投资、人力技术等项下收益几占三分之一。
再次,中国本土资本力量孱弱,无法与强大国外资本主义抗衡。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本土资本主义萌芽或启蒙时期,”中国所成立之矿业公司颇多,……然其财力,大半薄弱,不足称霸一方。而其产业权利,大抵属诸外人。“汉阳铁厂曾宣称”拒收洋股“,但在萍矿开办之初,就不得不向德国借了400万马克,向日人借6000万日元。此后,尽管汉冶萍公司向以”纯粹之中国公司“自诩,但它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资本侵蚀。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后,日本便加紧了对该公司的资本输出,明确要求公司以厂矿作为抵押。单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就迫使公司向其借债达17次之多,最终将公司牢牢掌控。”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与异族。“{6}即使有不借外债的中小企业,也难能摆脱外国列强欺压。他们若打算将工厂办下去,则”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难成或必败。“最终,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本土资本与外国列强帝国主义较量的结果,”停厂者有之,杀生破家者有之“{7}。真正能够像美国日本那样近代化之长青藤企业几无一家,这对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很难做出自圆其说的解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情。
汉冶萍公司的破产倒闭,是对中国本土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创。它早期高调入市与最终悄然退市是由多种原因导致而成。但是,公司管理的法治残缺与体制腐败,同当时整个晚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及政治腐败是紧紧依偎的。试想,汉冶萍公司的运输船只,往来于汉口九江间,还须挂上日本、俄国、或者德国的”洋旗“,才能在本国的内河上往来通行,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在这样的一个弱势政府的治理下,能够有何作为?反观当下之中国,年钢铁产量已达亿万吨,也就是说,汉冶萍公司虽然号称亚洲第一雄厂,但其58年的总产量仅为当今一年产量的百分之一。因此,我们在研究公司的失败原因时,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的宪政与政治体制维度中,通过它来了解和认识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法治状况。归根结底,就是要有助于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转型和复兴时期,更加觉醒起来,振奋起来,聪明起来。这才是笔者撰述本文的根本出发点。
三、赘言
宪政研究,当然难离人物。论道近代人物的贡献,诚如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讲的不能忘记的四个人,此四人与汉冶萍公司有直接关系的就占其三,一是张之洞,二是张骞,三是盛宣怀。对张之洞的研究,历来为政治法律学界所重。他在督鄂期间,尤其是创办汉阳铁厂时期如何实业救国重要思想主张和举措,无不与中国早期的宪政民主法治思想萌芽相关乎,他也呼请清廷适宜改良政治和用人体制,与引入西方先进的大机器生产相匹配。张骞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只有一年时间,并实质性到职任事。因为他在政治上属”立宪派“,也有相当鲜明的政治个性和宪政主张,与盛宣怀之”保皇派“的伪宪保守立场素来不合。他主张过于闭关保守的国家治理理念,必然会阻滞国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便是引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生产线,仍然还是不能生产一流的产品,因为它或缺了最根本的生产氛围,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反之,从这里也可看出,晚清的宪政努力之所以难有大成,这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滞后,无不存有直接因果关系。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是盛宣怀,对他的研究一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有关专家认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不研究盛宣怀是不可思议的。“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与张之洞共同搭建的早期工业化平台并以此作为二人政治合作的政治与经济改良实验基地,拉着晚清衰败的马车在实业救国与宪政改良救国的双轨上艰难前行。盛宣怀虽在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坐拥相当大的资本势力和尊崇的地位,但是他在接手汉冶萍后,几乎要以公司为家并为之付出了个人全部智、识、力,直至湖北武昌辛亥首义成功后五年,带着满腔的政治期许和遗憾而悲情辞世。
曾哲,单位系西南政法大学。
【注释】
[1]《张文襄公奏稿》第28卷。
[2]《汉冶萍公司过去及将来》,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
[3]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
[4]《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
[5]汪胡桢:《中国煤矿业小史》,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
[6]1892年6月11日张在致李鸿章的信说:汉阳铁厂的“经久之计,终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持久。”
[7]陈宝箴(1831—1900):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字右铭。时任湖南巡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896.1.30)陈发给张之洞电文。
[8]刘瑞芬(1827-1892):字艺田,安徽贵池人,时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张之洞致刘瑞芬电的时间为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1889.3.23)。
[9]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95.8. 2)的上谕中,或可发现为何近代国有钢铁企业必须改制的原因,国有企业的问题和弊端,间或反映的也正是我们政治体制的问题弊端。
[10]参见:《东方杂志》第7期。
[11]参见:《忠告为汉冶萍事人告者》,刊载于《中华实业从刊》第10、11合刊。
[12]参见:1925年5月16日《新闻报》,第1版。
[13]王韬:《上当路论实务书》。
[14]参见:1910年10月5日《时报》。
[1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