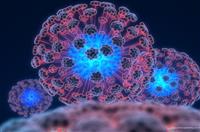在2001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有100多人大代表建议增加“见死不救罪”。在这之前,上海市一些政协委员已经提出设立“见危不救罪”,并同时设立“见义勇为奖”。然而,这项建议的合理性在学术界和网络论坛上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设立“见危不救罪”是否对个人权利构成侵害。笔者从这些争论中受到不少启发,但觉得要想把问题谈清楚,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这个新的视角就是对公德和私德的区分。
“公德”和“私德”这一对概念在我国是由梁启超先生首先提出的。梁启超的公德-私德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18-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和密尔的影响。边沁在其著作《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引入“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用以澄清道德与法律之关系。其后继者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著名的“不伤害原则”,其大意是: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利益,那么社会没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这个范围属于“个人道德”;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那么社会有权利对他进行法律的或道德的干预,这个范围属于“社会道德”。“不伤害原则”的重大意义在于指出个人和社会的权利界限,严守界限是维护正常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关键所在。
设立“见义勇为奖”和“见危不救罪”就涉及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亦即私德和公德之界限的问题。如果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行为属于私德,那就主要地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不必为之设奖或定罪,否则是必要的。然而,对这一问题,密尔本人并未说清楚。
一方面,密尔认为见义勇为的行为属于个人美德,而不属于社会道德,因而不可用法律惩罚等社会强制的方法来推行。他说道:“若说有谁低估个人道德,我是倒数第一名;个人道德在重要性上仅仅次于,假如还能说是次于,社会道德。教育的任务也是要对二者作同等的培养。但是即便是教育,其运用也有借辩服和劝服以及借强制办法之区别,而对于已过教育时期的人,个人道德的教诲是只应以前一种办法来进行的。”[1]密尔并不轻视个人道德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他主张,促进个人道德只能用“辩服或劝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道德,适合于它们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二者不容混淆。
另一方面,密尔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所主张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他认为在有些情况下见义勇为属于公德,违背它应当受到处罚。他说:“一个人做了祸害他人的事,要责成他为此负责,这是规则;至于他不去防止祸害,要责成他为此负责,那比较说来就是例外了。尽管是例外,在许多足够明显和足够重大的情事上却足以明其为正当。”[2]那么,这种例外情形是怎样的呢?他说:“例如出力去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挺身保护一个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等等。”[3]不过,密尔有时又说“无私的慈善尽能够找到其他工具劝使人们得到好处,而不必使用鞭子或板子”。[4]可见,密尔对于见危不救的行为是否要追究其责任并诉诸强制手段,也是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因此,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笔者认为,边沁的“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密尔的“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以及梁启超的“公德”和“私德”,这些概念虽然大致相当,但却存在岐义和含混之处,因而有必要加以澄清。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契约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签约者;当然,在社会契约之外还有人们的私人生活。所谓公德就是与社会契约直接相关或比较接近的道德规范,因而对它的遵守具有义务性;所谓私德就是远离社会契约的道德规范,因而对它的遵守具有非义务性或超义务性。例如,‘要信守诺言’与‘要谦虚谨慎’相比,前者属于公德而后者属于私德,既然前者比后者对于社会契约的实施更为重要。不难看出,由于公德具有义务性,所以一个人必须遵守公德准则,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甚至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与之不同,由于私德不具有义务性,所以一个人遵守私德准则更好,但不遵守私德准则也无可厚非。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应当以公德为主而以私德为辅。
具体到“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行为,我们首先从公德方面来看。对于某些特殊职业如警察、消防员和医生等,“见义勇为”和“救死扶伤”属于其职业范围内的义务或职责,因而是可以作为社会契约明文规定的。如果这类人员违反了,轻者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重者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如果遵守了,一般作为称职来看待,对于表现突出者给以表扬或奖励。这类社会契约可以在不同行业内分别制定,也可在国家法律中给出一般性的规定。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特殊职业以外的普通人而言,“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行为属于公德还是私德?这涉及一个更为一般的道德问题,即“舍己为人”属于公德还是私德?根据密尔的“不伤害原则”和“最大幸福原则”以及上面关于公德和私德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价标准:
如果舍弃自己较小的利益便可换得较大的社会利益,那么这种舍己为人行为属于公德,因而对它的遵守应当给以公开的表扬或奖励,反之应当给以公开的批评或惩罚。
如果必须舍弃自己较大利益(甚至生命)才能换取较小的社会利益,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也属于公德范围,不过不是公德上提倡的,而是公德上禁止的。
如果必须舍弃自己较大利益甚至生命才能换取较大社会利益,那么这种舍己为人行为的道德价值在公德上是无解的,因而属于私德;在私德范围内,遵守其准则更好,不遵守也无可厚非。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最为宝贵的,用康德的话说,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别人的手段。
例如,一个人发现有人进行偷盗或杀人等犯罪活动,根据上述标准1,他应当打电话通报警察;如果他这样做了,应当受到表扬甚至奖励,否则就应当受到批评甚至惩罚(当然要能确定他是知情者并有条件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通报警察)。然而,根据上述标准3,这个人是否应当冲上前去与歹徒进行搏斗,则是一个私德问题;他这样做更好,但若没有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因为他这样做是有生命危险的。
更为复杂的是,见义勇为的行为有没有生命危险事先并不确定,这就涉及概率问题。一般而言,如果危及生命的概率很高,如与劫机犯搏斗,那么这种见义勇为行为往往与上述标准2相关,因而不仅不应提倡,反而应当阻止,甚至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加以阻止;如果危及生命的概率较低(如打电话报警),那么对这种见义勇为行为就与上述标准1相关,因而要提倡,甚至用社会契约的方式加以确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把见义勇为作为公德问题来处理的。然而,还有一些场合,危及生命的概率是完全不确定的,如一个人捉拿盗贼时他对盗贼是否有凶器、是否凶狠等一般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奉行宽容原则,即从对当事人有利的方面去处理:如果一个人没有见义勇为,就把它作为一个私德问题,不予追究或过问;如果一个人见义勇为了,就把它作为一个公德问题,给予表扬或奖励。
由此可见,对于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行为的道德评价和法律裁定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警察、消防员、医生等特殊职业的人,设立“见危不救罪”是合适的,但对普通人设立这项罪名则需要严加限定,比如限定为: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面对他人危急完全无所作为者应当给予一定的处罚。至于如何处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设立“见义勇为奖”和“见危不救罪”不是完全不可以的,但一定要有明确的界定。特别对设立“见危不救罪”要格外小心,否则,不但不能起到抑恶扬善的社会作用,反而会使国家或社会过分地干预甚至侵犯普通人的生存权利,亦即违反密尔的“不伤害原则”。
[1]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2页。
[2]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页。
[3]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
[4]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