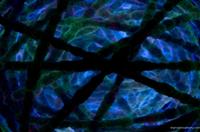2014年诺奖评审结果渐次出炉,被汤森路透“高估”的四位华人科学家一一落榜,接下来的和平奖、经济学奖、文学奖等更是无缘。长期以来,国际性评奖一直牵动着国人敏感而脆弱的民族自尊,一方面举国体制打造“种子”选手,一方面嬉笑怒骂“贬谈”洋人偏见。在“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式的集体无意识的“醒狮”自觉中,国人追求“承认”的斗争与获胜意识日益凸显。如今,“体能奥运”早已登峰造极,但有着“精神奥运”内涵的诺奖比拼却一直徘徊低迷,成为国人心头隐痛。
历数华人诺奖得主,从早期的李政道、杨振宁到近来的高锟、莫言等,真正具有本土教育和成长印记的似乎只有莫言一人。2012年莫言获奖引发国人躁动,但自然科学领域缺乏积极突破,仍然是无法掩盖的忧伤。此次入围的华人科学家即有着本土教育成长背景,且科研与国内环境相关,故所受期待更大,所带来的失望也更重,“诺将焦虑症”不减反增。
在评比结果不利和国人愈发焦躁的背景下,《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姜泓冰近日撰文提出了“道路自信论”,认为民族自信比诺奖结果更重要,诺奖评审有着文化偏向与偶然性,国人不必一味渴望“与国际接轨”,而是懂得对比、反思,走自己的路。作为一种精神安慰策略,这些观点或许可商,但这里存在诸多需要明确分辨的关系和范畴,不能笼统对待,否则容易重新落入“自卑式自负”的精神怪圈,负气退出游戏。
诺奖是人类精神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世界级奖项,是“精神奥运”,所代表和凝聚的是西方科学与人文的主导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在此意义上,姜先生所言的“文化偏向”自然是存在的。这里涉及到西方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在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文明”时代,世界几大文明并驾齐驱,在各自地理与文化边界内作为“文明标准”而存在,中国文化亦曾领先世界,或者至少是东亚标准。彼时,诺奖之类的事物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工业化、殖民化和全球化,西方文明日益超出其地域和民族边界,成为人类文明在工业时代与全球化时代的“代表”,成为世界历史的阶段性“立法者”,亦为不争之事实。中国之系统感受文化压抑和被动现代化,恰恰是整个近代史的真切体验,而中国之现代奋斗与崛起,又恰恰是不断学习并扬弃西方文明的结果。因此,若论“道路自信”,当更加发扬中国现代化经验中主动学习与适应西方的特定经验,以提升中国现代化的“现代性精神”品质。
如今国人的诺奖比拼意识,渐渐显露出一种“种族主义”倾向。国人的“诺奖假想敌”有二:其一是欧美阵营,这是诺奖的本家,尽管意欲挑战,但更是一场关乎“文明”的持久战,需从长计议;其二是东邻日本,这个曾经的华夏文明辐射地,自“脱亚入欧”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竟然迭获诺奖,而且涉及核心技术领域,实在令国人不快。以民族或种族为单位的竞争意识固然本真自然,但却隐藏着极大的狭隘与偏见,而且可能根本妨碍思想的多元汲取和丰富创造。在竞争挫折之下,按照姜先生的“道路自信论”,似乎要更加强化“种族主义”倾向,实在是精神后退之表现。只有适度悬隔“种族主义”想象和固执,使得中国的知识创造群体能够“自由”地面向人类,以人类共同的苦难为苦难,共同的理想为理想,才有可能在精神上首先站立在诺奖的世界级高度,也才能最终为本国赢得精神荣誉。真诚面向人类不是放弃自我,而是以更整体化与更符合知识自由品质的精神气质面对当代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严格限定的现代世界,一个由西方文明充当“阶段性代表”的世界,无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有多大,诺奖的科学与人文评价结果仍然构成对我国现代化品质的有效检验。如我们以“道路自信”为由对自身道路做出过分狭隘的解释与守护,很可能延误中华民族经由“深度现代化”而重新领导世界的历史前途。
“道路自信论”背后还隐含着一种关于文明和技术的区分,即诺奖的技术型奖项(生物医学、物理、化学、经济)与文明无关,而其文化型奖项(和平、文学)则带有文化偏见。按照这一解释逻辑,中国的诺奖挫折竟然就可以不是挫折,而恰恰是自身“独特”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证明。沿此逻辑推导,则中国道路论、中国模式论甚至中国例外论均可鱼贯而入。这是一种批判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思维模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主义以及中国文明内在的天下主义均存在严重的精神冲突。当代中国的一个悖论性的精神特征是:一方面标榜政治自主和精神独立,另一方面竭力促进“与国际接轨”,显示出战略自信与战术自卑的奇特组合。姜先生的“道路自信论”代表的是战略,而国人的“诺奖焦虑症”代表的则是战术,战略高亢掩盖不了战术窘迫。
这里混杂了不同范畴和概念。首先是文明与技术的区分需要相对化。面对一个严格的“技术主权”时代,如果中国的科学研究与文明改造不能在“技术”层面解决自身及人类共同难题,就不可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也就不构成“文明”增量。因此,诺奖的技术型奖项无疑也是一种文明成果的评价指标。人类的新文明已经与“技术”无法脱钩。再回到传统的人文文明层次,近来国人的文明连续论、主体性及复古情怀高涨,这是一个民族“精神寻根”的本真动向,但若论及对人类的精神贡献,则必须面向当代世界与当代处境,对人类在西方文化主导下遭遇的和平、环保、伦理、秩序、社群团结等方面的道德困境提供更优越的解释与解决,使得经历“创造性转化”后的中华文明具备对人类的实质贡献、解释权与代表权。因此,这里需要提出信仰性文明与技术性文明的合理区分,二者都是严格的现代文明形态。中国在技术性文明领域需要更严格的“与国际接轨”,建立更自由和更具竞争创造氛围的学术科研体制,而不是以所谓的“道路自信”阻碍中国教育科研体制的标准化与国际化。中国在信仰性文明领域则需要遵循不同的战略,这里的“道路自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道路”应作大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理解,不宜仅仅局限于现实体制和当代传统。更重要的是,在信仰性文明领域,中国需要有会通传统、包容西方的综合与创造意识,扩展而不是缩减现代文明范畴内的思想关键词与理论通感。如果一个民族以“道路自信”为借口阻碍“思想关键词”的民族化和日常运用,就相当于堵塞了该民族全面总结提升自身“道路”、扩展优化思想竞争力与文明前景的“泉眼”,贻害无穷。
事实上,中国本身包含着“诺奖化”的丰富潜能,中国丰厚的古典文明资源和复杂多样的现代化经验,尚未在学术理论上有真正科学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我们的“与国际接轨”大多限于纯粹的技术模仿领域,而对中国自身经验的总结又局限于一种严格而一致的“政治理解”。当然,西方人的“文化偏见”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西方学术对中国古典资源与现代经验真正科学的解释与认知。因此,“中国经验”尚成为诺奖成果的一大空白,从而也是中国有可能贡献于诺奖及人类的最大“富矿”。近十年来,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挖掘日益成为国内一流学者乃至于国际领先学者的“学术共识”。连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都在深度挖掘中国的“国家能力”要素在世界政治秩序起源上的典范意义。诺奖成果迟迟未能反映此种动向,既是诺奖“文化偏见”的某种折射,也是国内“本土学术”自由度与理论创造力不足的现实体现。
总之,诺奖仍然是评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现代化精神成果的权威标尺,中国应积极参与竞争,同时努力改革自身学术科研体制,增强自由度和创造力,深度挖掘“中国经验”的普遍主义价值与理论化潜能,以实际的参与和竞争行为改变诺奖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分享现代世界的文化解释权、代表权与领导权。只有“通向人类的道路”才可能是真正“自信”的道路,而泛泛的“道路自信”终究难解“诺奖焦虑症”。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4年10月13日,发表时标题改为“诺奖焦虑症该如何破解”,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