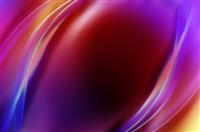
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外国人难以明白此话的含义,毛的老朋友美国人斯诺将此话翻译成“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如此谬译,让人哭笑不得。
无法无天也就是为所欲为,藐视规则,无限制、无约束、无底线。治国而无法无天,其结果可想而知。权力不受制约,最后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被中共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曾经的亲密同志和国家主席,转眼便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国家主席尚且得不到法律保护,遑论他人。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有了依法治国的口号。不久前,中共召开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仅仅只是一个依法的问题。在中国,一直以来总有人要么从古代法家的理念上去理解法治,以为法治就是统治者威临天下,法外无情;要么从联共(布)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上去理解法治,认为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专政。
这两种观念都隐含了一种前现代的政治理念,即不是从约法,而是从征服的意义上去理解法治。按这种理念,法律和法治,都是用来管制被统治者的,在这之上,有一个作为社会征服者的超级实体,它是法律或法治的制定者、施加者,而它自身是不受法律或法治制约的。这种前现代的政治理念固然符合人类早期,甚至至今一些后进国家族群间或阶级间的政治征服历史,但却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认为,法律是一种公共的约定。其正义性就在于这种约定。法律或法治固然有其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不是基于征服,而是基于约定。它的强制性只是为了维护这种约定。这种强制性本身,并不构成法律体系合法性和公正性的来源。在这种现代法治体系中,不存在位于法律之上的超级实体。即便是这一系统的操作者,本身也要受约法制约。这就是权力制衡和有限权力的现代政治理念。
在中国,千百年来,“依法”之所以仅仅只是一种景愿,而非一种常态,以至铁面包公的戏唱了几百年,就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在法律之上的超级实体,法律因其意志而随意弯曲。这就是俗称的权大于法。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种体制下,即便执法者个个都是包青天,都能严格执法,是否就实现了社会公正和法律正义呢?执法的严格,这本身并不能证明被执行的法律的公正性。早在两千多年,孔子就说过“苛政猛于虎”,认为严刑苛政对百姓的伤害,犹甚于虎。当然,孔子并没有去否定这种权法关系先天性的结构缺陷,而是试图以德治仁政去弥补其不足。
对于今日中国来说,要改变原有的权法关系,一步跨入到现代法治社会,尚无可能。究其原因,既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六十多年体制惯性的历史包袱,也有执政利益的纠结和马列原教旨主义教条的束缚。以今日中国党与法的关系来说,要执政党自我否定,自我放弃“党的领导”,按西方模式来重构权法关系,显然不切实际。
在近现代一些国家中,曾经历从开明专制或威权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演变。在这些社会中,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不是革命式地打碎重构或推倒重来,而是从确定王权或党权的法律边界,约束无限权力开始的。借鉴这种渐进模式,在今日中国,撇开现有党法关系不谈,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去约束公权,限制其对社会生活的任意干预。
首先,依法治国,意味着以法治替代人治,即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喜好去治国,意味着执政者不应越过法律去干预一切。改革开放前,无限权力干预一切,农民怎么种地,艺术家怎么写剧本,事无巨细,都被统管起来,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既然谈法治社会,至少要做到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不应任意干预。
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的非政治性的事务,譬如,文学作品要怎么创作,教材要怎么编写、建筑风格的美丑评价等等,这属于文学家、教师和建筑师等的事务范围,而并非国家事务。执政者纵然全知全能,亦应明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依法治国,不仅仅只是指限制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营造透明有序、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应包括限制公权介入其他非政治性的社会生活领域。
其次,在不涉及顶层党法关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基层和地方层面,去约束基层和地方权力对法律的干扰。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被称为“块块专政”的体制,每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在本地区都是一言九鼎,拥有无限权力,可以干预地方立法、执法、纪检、媒体舆论、经济民生等任何事务,如同土皇帝。
在地方层面上将某些权力,如司法、廉政监督、舆论管理等,分离出来,形成地方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限制公权的滥用,至少可以在大范围内有效减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和官场腐败的弊端,在地方层面上的发生,增进社会和谐,减少民怨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尽管当局讲依法治国,并非要否定现有党法关系,但与无法无天相比,提出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限制公权滥用,无疑是一个进步。人们希望,未来的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