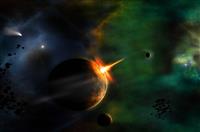东方与西方,原本是一种地域上的差别。古代社会,以地中海为中心,希腊和罗马是西方,波斯和印度是东方。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双重影响,东方与西方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上的概念。法律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具有文化的属性,这样便有东方社会的法律与西方社会的法律。
在发生利益冲突之前,东西方社会各相安无事。西方人曾羡慕过东方式的富庶与礼仪,东方人也惊叹过西方式的文明与繁荣。当东方与西方相互渗透融合,此方利用武力掠夺彼方的时候,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就显现出来。古代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罗马帝国时代的武力征伐,十字军的东征,蒙古人的西进,近代西方列强的海外扩张,都引发过东西方的冲突。武力之后便是殖民,殖民也需要秩序,维护秩序的方法之一便是法律。由此,东方传统法律与西方传统法律的优劣争议,甚嚣尘上,延续至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东方法律传统与西方法律传统并无优劣之分,西方人享受着个人的平等自由,东方安逸于等级有序的社会和谐。但是,19世纪后半叶以降西胜东败格局形成,东方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胜利者的西方人自信于自己的法律制度,于征服地推行自己的法律,希望被征服者按照自己的法律来生活。受挫的东方人会反思自己的法律,提出疑问: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的法律来自救?东方人的“西方法治的心结”由此产生,这种心结普遍地存在于东方各国,典型地,日本、中国和伊朗。简单的结论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中国的戊戌变法是失败的,伊朗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则是反动的。
日本法律的西化演进模式
日本法律发达史,展现了东方法治心结的全貌。日本法律史一般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儒家精神的封建法,二是继受德法的近代法,三是美国掌控下的现代法。对于日本封建制度的描述,政治史家与法律学家评论并不一致。在历史学家看来,日本的封建制度不同于中国大唐以来的专制封建帝国,而是更接近于欧洲大陆宗主和封臣的制度。公元7世纪日本孝德天皇采隋唐中央集权政制,移植大唐“令”制,虽然表面上实现了权力的统一,但是,天皇的势力范围只局限于京畿周围,京效之外仍然由强有力的家族封建主割据把持。封建之下有武士,武士勇敢强悍、忠君守义和重名轻身。武士的最高义务是护卫主君和雪耻报仇。幕府政治兴起后,天皇虚权与大名实权的二元权力格局并没有改观,家族血缘关系和封建附庸关系仍是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法律史家则另有解释,认定日本封建法律就是中国法律的一个翻版,日本法律的精神实质则是儒家的忠孝之道。孝德天皇的法律是隋唐式的,幕府时代的法律则是大明式的。穗积陈重的总结是:“日本法律属于中国法族者盖一千六百年矣。虽自大化改革以后经历极多巨大之变化,而日本法制之基础仍属于中国之道德哲学与崇拜祖宗之习惯及封建制度”。幕府时代,日本刑法既有中国明清律的普通制度,又有大名藩主的地方限制。但是,立法精神仍为儒家的道德主义:仆对藩主须尽忠忱,子对父母须尽孝道,妻对丈夫须绝对服从。
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将蒸汽动力的黑船舰队驶入东京湾,叩开了日本的大门。美国的治外法权惊醒了日本人。为了获得别国的承认和平等的国际地位,他们喊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增强自己的国力,日本现代化运动开启,其中移植西方法律成为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分。1871年,天皇废除了整个封建制度,首相伊藤博文出访欧洲各国,希望找到合适于日本的西方宪政模式。在英法个人主义的模式和德意志团体主义模式之间,伊藤博文焦燥不安,最后在普鲁士宪法学者斯坦恩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决定仿效德意志宪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现代法治国模式。1889年,日本天皇颁布的宪法,多多少少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复制品。日本宪法规定的两院制、国会立法和权利法案,是西方的舶来品,同时,东方文化的基本观念依然保留:人类天生不平等、劣等人服从优等人、社会比个人更重要、人治比法治更好、父权制家庭是理想的模式。大名和武士依然控制着政治,只是名称改成了元老或议员。在刑法方面,1870年日本颁布的《新律纲领》依然是《大明律》的模式,而1873年的《改定律例》,则基本采取了欧洲的立法模式。穗积陈重的评论是:“此两部法律典者皆代表日本法律史之过渡时代者也。前者为中国法系最后之结束,次者为加入欧洲法系之开端。日本法律自始由中国法族急转而加入欧洲法族”。中国法史学者则称,日本1880年采用法国《旧刑法》,为日本脱离“中国法系”转入“大陆法系”之起始。
1945年,美国占领了日本。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和平宪法”草案试图以美国宪法的精神来改造德国模式的明治宪法。麦克阿瑟提出了新宪法的三原则:国民主义、和平主义和人权保障。国民主义是要降低天皇的法律地位,反对家族式的政治统治,宣称主权在民,天皇只保留名义上的权力。和平主义是反对日本的武士道军国主义,放弃战争。人权保障是扩大选举权、提高劳动者的主体意思、引进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天皇于1946年11月在国会正式颁布。理想的法学家们称,战后日本宪法的转化,是德国模式向美国模式的变化,从法治国到法治的变化,从限制君权到扩大民权的变化。历史学家则说,新宪法带有乌托邦的味道,因为如果此宪法能够实现,日本就是比美国还要先进的民主国家了。但在实践上,日本的保守势力依然存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说,法治的实质还是“整体的人应当服从法律”,是“法律对人们的支配,人们应当服从法律”,“法治的最重要目的不是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人们服从法律”。悲观的学者们则称,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还是乐于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比如调节、调停与和解,“基于条文的诉讼仍然只是社会控制或争端解决的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从民族本性上看,“日本是一个敌视法律的社会”,“法律需要尽量避而远之”,“它不但不受欢迎甚至是可恶的”。“被传唤到法院也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日本人不喜欢法律”。
伊斯兰复兴与法律传统的回归
伊斯兰人在人类历史上也留下过深深的印记。在那样的文化传统里,一个自由的穆斯林男性,只要能够供养且能平等对待,他就可以娶四个妻子。财产人所有人可以依遗嘱处理他的财产,但是,前提条件必须是将财产的三分之一留给他的亲属。在公共事务上,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一切权利属于“安拉”,《古兰经》是法律的最高渊源。伊斯兰教徒不得脱教,叛教者会被处以死刑。在非洲的伊斯兰国家,通奸、诬告通奸、酗酒要受鞭刑。
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了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法律现代化启动。奥斯曼帝国的《御园敕令》,宣布了西方式的法律原则:保障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安全,所有人不分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876年,奥斯曼帝国宪法以比利时的宪法为基础,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确立了两院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908年的宪法又废除了奴隶制。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阿拉伯众多的国家取得了独立,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宪法的原则和理念在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等宪法中都有类似的表达: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两院制、法律平等、主权在民、代议制、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在私法部分,传统顽强地抵制着西方,但西方的影响依然可见。多妻制和离婚方面,1917年奥斯曼帝国家庭法规定:如果妻子在婚约中约定丈夫婚后不能娶第二个妻子,那么若丈夫再娶,第一个妻子有权请求离婚。通常讲,埃及1948年的民法典参照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法典,它既保留有伊斯兰传统,又增加了符合现代商贸规则的内容。这部法典被视为伊斯兰传统与现代法律相结合的典范,直接影响了伊斯兰各国。1949年叙利亚民法典、1953年伊拉克民法典、1954年利比亚民法典都以埃及的这部民法典作为参考。在刑法方面,1858年奥斯曼帝国刑法典照搬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1926年土耳其刑法典和1937年埃及刑法典则模仿了意大利的刑法典。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伊斯兰地区局势动荡。意在回复到传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萌动,而伊斯兰法的传统复归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伊斯兰复兴主义者认为,西方法律只代表西方的经验,而伊斯兰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价值观,与西方国家有质的差别。法律全盘西化搅乱了伊斯兰原有的社会秩序。他们主张恢复伊斯兰法的意识形态,回复法律中的伊斯兰传统。“伊斯兰法是最重要的渊源”、“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惯例是最主要渊源”、“在缺少可适用的制定法时,法院应使用《古兰经》和圣训”,重新回到了伊斯兰诸国的宪法之中。伊朗霍梅尼政府在1979年宪法中规定,“立法不得与官方宗教原则和命令相抵触,一切与伊斯兰原则抵触的法律都无效”。设立最高司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前者负责修改先前的法律、按照伊斯兰原则重新制定法律,后者有权监督议会通过的法案、对违反伊斯兰原则的法律予以否决。伊朗和苏丹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对盗窃者的断手刑,利比亚、伊朗、巴基斯坦和苏丹恢复了对未婚通奸及诬陷通奸的鞭刑、已婚通奸者的乱石刑。婚姻家庭法方面,伊朗恢复了传统的多妻制度及休妻制度,男性有绝对离婚权而女性只享有有限的离婚权。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美国911事件之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西方人称伊斯兰为恐怖主义,伊斯兰则自称为了信仰的自由战士。法律的博弈最后转化为赤裸裸的战争。西方人指责伊斯兰教义中“圣战”(Jihad)的暴力主义和报复主义,而伊斯兰人则称西方人误解Jihad,它并非“圣战”,而是“精神和非暴力”的“坚定信仰和牺牲”,是穆斯林的自我完善、节制欲望、战胜无知和努力拼搏。在历史学家们看来,宗教战争掩盖着政治经济的冲突。擅长以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讨论东西冲突的学者们宁愿相信,是经济与政治的因素而非宗教的因素导致了冲突与战争。
法治的西式形式与东式的实质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通过行为规范达到和谐的生活秩序、以法律的手段实现社会的控制,这些命题通行于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东方法律与西方法律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家族亲情观念、贵族平民等级观念、个人服从团体的义务观念、宗教道德居先于法律的观念,既出现在中国、日本这样的东方传统法律之中,也出现在希腊罗马的西方传统法律之中。19世纪的法律史学家的一般描述是,人类早期的法律,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在历史上的某个点上,静态的东方社会法律发展停滞了,而动态的西方社会法律则不断发展。这个点就是社会的“现代化”。现代社会之前,法律的出发点是家族的身份,现代化之后,法律出发点是个人的自由。按照此逻辑,东方社会一直保持着古代法律团体本位的传统,而西方社会则不断更新,由一个基于“家族身份”的法律过渡到了基于“个人自由”的法律。20世纪的学者则进一步细化,称西方社会的法律也非单一的固定模式。英法个人主义法律强调了个人的自治与独立,政府的作用是消极地保障个人权利;德国团体主义的法律则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来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政府的作用是积极地促进个人的权利。前者称为“法治”的模式,后者称为“法治国”的模式。这样,法律的模式就出现了两组对立统一:东方/西方和法治/法治国。西方人学习东方人的法律,存在于古代社会,比如,罗马共和国的法律来自东边的古希腊,现代罗马法来自东罗马帝国的法律。近代社会后,则常见东方社会对西方社会的法律移植或继受。学习的对象,有的偏重“法治”,有的偏重“法治国”。从日本的情形看,它先学德国的“法治国”,后学美国的“法治”。
但如果从逻辑转向经验,那么明显地,西方人永远变不成东方人,东方人也永远成不了西方人。东西方法律的移植或继受,与其说是机械的嫁接,还不如说是双方的融合。罗马法起源于西方,成熟于东方,开花在西方。其中,哪些来自西方的希腊城邦、罗马城、波伦亚,以及法兰西和德意志?哪些来自东方的巴比伦、古埃及、闪米特和耶路撒冷?这是历史的悬案。现代东方人对西方法治的心结,其实不过是西方法治形式与东方传统实质之间的冲突与焦虑。东方国家对西方国家法律的移植也好,继受也罢,那都只是接受西方法律的外在形式。西方法律内在精神是西方的,东方人在这样法律形式下生活,内心的冲突必不可避免。西方法律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同义词,东方国家要进入现代化,那么东方与西方法律的趋同则不可避免,这也加剧了东方人的内心挣扎。要了结此心结,我们就需要确信,所谓东方法律的现代化,只不过是将西方要素纳进东方的法律世界。我们生活的结构不变,内心就不会再有纠结。人类社会本身就应该是多元的,东方人也没有必要变成西方人,孔子也说过要“和而不同”嘛。
【作者简介】
徐爱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