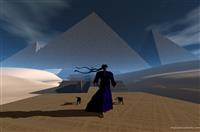不知从何时起,乞讨权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首先是法律家们在法律上大谈特谈所谓的“乞讨权”究竟是不是乞丐的一项权利?如果是,那么这项权利究竟是道德权利还是法定权利?虽然关于“乞讨权”问题,目前还在争论,不过根据已发表的“权威”观点,笔者解读出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含义:(1)乞讨权是一种法外权利,法外权利是不为国家所保护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义务作它实现的条件或保障;(2)乞讨权是穷人的道德权利;(3)乞讨是公民的自由而非公民的权利。权利的实现必须以相对方的义务履行为条件,必须由国家提供保障;而乞讨作为乞丐的自由,其实施不能以国家作为义务主体,反而必须以无碍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为前提,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4)限制乞丐同样是一种文明。
福柯说:“我努力使那些仅仅因其一目了然而不为人所见的东西为人们看见。”乞讨权就是这样一个“一目了然而不为人所见的东西”,笔者愿意作一些福柯所做的工作。
乞讨权究竟是什么?首先应明确乞讨与乞丐个人意志自由有关。从理论上讲,乞丐作为人有意志自由,他可以选择乞讨也可以选择不乞讨,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那样的生活方式。如果选择乞讨这种生活方式,那么他有选择在这儿乞讨的自由,也有选择在那儿乞讨的自由。但作为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如果真的有这些选择自由的话,那么我敢肯定他不会选择乞讨这种不体面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样的前提假设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个人一旦沦落为乞丐,那么其对生活方式是不能自我选择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乞讨已经是乞丐做出的最佳生活方式选择,因为不乞讨他可能被饿死,在生和死之间他选择了生。为了生存,他只能乞讨。这种情况下,乞丐的自由只有选择在何处乞讨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乞讨权是自由权,但这种自由权内容主要是选择乞讨地的自由。
乞丐乞讨是在其不能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情况下,为了生存的需要出于本能的冲动而实施的行为。在这种行为意义上,“乞讨权”是一种社会权利,这种权利在西方被称为“生存权”。生存权就其特性来讲不同于自由权的地方是:自由权是在国民自由的范围中免于国家干预的权利,是要求国家不作为的权利;而生存权是“免于匮乏的权利”,是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即国家负有积极采取措施对社会经济上的弱者如失业者、贫困者和一贫如洗的乞丐进行保护与帮助的义务,以保证这些人能够过像人一样的生活。
在立宪的现代社会,生存权是一种法定权利。生存权在世界上最早受到宪法明文保障的是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之后有关生存权的规定被写进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当中。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在我国的《人权白皮书》中也始终把生存权作为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国务院2003年8月1日生效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生活无着的公民有获得救助的权利,各级政府是履行救助义务的主体。因此,在我国乞丐的生存权是受到宪法和法律 保障的。
在我国,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公平度的下降,农村中一部分农民以及城市下岗职工逐渐脱离主流社会而形成弱势群体,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如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残疾人,因得不到社会保障和救济,生活无着,家庭极其贫困,无法再像正常人那样生存进而逐渐沦为乞丐。据《法制日报》提供的统计,这样的人在中国达上百万。这是改革以来我们追究经济自由和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黑格尔说“历史是恶”,从这种意义上说也许有一定道理。
客观地讲,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有代价的,问题是这种代价应当由谁来承担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代价。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就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呼唤,这种情感和呼唤千百年来一直激荡读者的心灵。但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理想的实现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而且乞丐等天下寒士生存权的实现的义务主体也只能是国家。
不过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社会发展的代价主要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国家并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表现在处理乞丐问题上就是设置“禁乞区”。依据拟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第58条第3款规定,对那些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不得乞讨的公共场所乞讨,拒不听从劝阻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处1日以上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或者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轻微的,可以单处警告,并强行带离现场。该条规定,一是确认城市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不得乞讨的公共场所,即“禁乞区”;二是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关于在城市划定“禁讨区”,这一直是人们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支持者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的确,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有界限的,其最主要的界限是公共利益。因为任何权利,一旦伴随着法律行为就有可能和他人利益,特别是公共利益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多数人权利和少数人权利的冲突。传统的、也是现在一直在使用的解决冲突的方法是为了多数人的权利而牺牲少数人的权利。在城市设置“禁讨区”无疑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它为了保证城市的公共秩序和市民能够享受到“没有乞丐”的环境权,限制了乞丐自由行乞的活动空间,从而对乞丐的生存权构成威胁。因为从广州、上海等地设置的“禁乞”的区域看,除了交通要道、政府机关和一些重要活动场所外,主要是商业区和居民区,而这些地方恰恰是乞丐能获得较充足施舍的地方。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正义所保障的权利,不能屈从于政治的交易或者对社会利益的算计之下。”上述解决办法具有“社会利益的算计”痕迹。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呢?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正义保障权利的解决方法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根据科斯定律,不管权利属于谁, 只要界线清楚, 讨价还价都可以得到对双方最优的“界外效应”量。在城市市民和乞丐之间,他们的权利归属是清楚的。城市市民享有“没有乞丐”的环境权;乞丐有生存权,为了实现生存权有到处乞讨的自由。城市市民的权利和公共利益通常由城市人民政府代表,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种讨价还价的制度平台,那么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可能是:对那些一贫如洗且又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乞讨完全是为了维持生命的,政府提供给乞丐有效的物质生活保障,使他们能够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对那些主要来自一些农村、利用农闲季节外出乞讨以改善生活或者解决子女读书等经济问题的,政府应设法消除城乡壁垒,尽可能地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对那些组织他人乞讨、把生活无着的老人、儿童或残疾人作为赚钱工具的人,政府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对被操纵者给予应有的社会救济和保障。乞丐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放弃乞讨,选择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这样,乞丐和政府之间、乞丐和城市市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消除,社会公平度将会增加,从而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当然,政府在讨价还价中将会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这种代价并不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总代价中新增加的代价,而只是由本来由社会经济上的弱者承担的代价转移到政府身上。洛克认为,依照契约成立的政府“绝不能有毁灭、奴役或故意使臣民陷于贫困的权利。”因此由政府承担这种代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代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和“和谐发展”,特别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应该是实现杜甫等前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