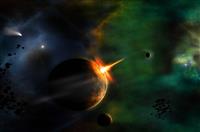内容提要:公私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在当代中国,关于公私问题的认识关系到道德建构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本文纵览古今,对公私观念的三层境界进行了分析,即:以君为本的公私观,以民为本的公私观,以人为本的公私观。作者肯认第三层境界,认为只有以现代化社会为认识坐标,以一般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主体地位的绝对确认作为认识的起点,我们关于公私观的阐释才有可能是合理的。否则,在社会政治主体定位含混不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模糊不分的情况下,诸如“大公无私”,“立公去私”,“无私奉献”等等,就有可能成为个别拥有权势者或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私利、剥夺他人、制造不公正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公私观 以君为本 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政治主体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论题之一,公而不私,大公无私是这一辨题的基本结论。可是,理论与实践总是有间距,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私心、私欲人所难免,谋利、逐利或难舍弃。于是千百年来,有公有私,或公或私,何去何从,论辩不已。早在先秦时代,儒学宗师们就倡导公而不私,汉儒则概括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循至20世纪50年代,“大公无私”的口号仍然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准则,得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提倡。时至21世纪的今日,河南临颍县南街村 [②] 中还有这样的标语:
大公无私是圣人;先公后私是贤人;公私兼顾是好人;
先私后公是庸人;损公肥私是坏人。
那么,上古之私与今日之私可有异同?或私或公的内在规定性与合理性又如何判定?公与私作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理念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公私理念的三层境界略作分析,祈方家正之。
一、第一层境界:以君为本的公私观
中国文化确乎源远流长,据考,甲文、金文均有公字。不过,关于公的本义,研究者见仁见智,说法不一。如若从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在中国传统社会,公与私作为政治概念或政治道德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大体分为两类。
第一类,用以指称君主或国君一族。如《诗·周颂·臣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毛亨传:“公,君也。”与毛传相同的释义又见于《礼记·昏义》:“教于公宫”郑玄注、《论语·子罕》:“出则事公卿”皇侃疏、《谷梁传·隐公元年》:“言君之不取之为公也”范宁注等。又《仪礼·既夕礼》:“公賵元纁束”,郑玄注:“公,国君也。”从文献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至迟在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君主及君王一族通称为“公室”、“公门”,与之相对,卿大夫等臣僚则称为“私家”。《左传·昭公三年》载,晋大夫叔向曰:“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荀子当年入秦,谈其观感曰:“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荀子·强国》)这一类公私观源自先秦,延及后世,例如汉萧望之说:“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汉书·萧望之传》)公室与私家相对,是对于君主与其臣僚的普通称谓。
第二类,用以指称社会一般标准,诸如法规、律法或其他行为规范等等。《慎子·威德》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黄老帛书《经法·君正》说:“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韩非子·有度》:“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这里说的公,似乎指的是政治的或法律的规定,以其具有普遍的权威性而与私相对。
另外,这类的公又涵指社会公认的事物一般标准,如《慎子·威德》言:“蓍龟似乎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这样的公是面向全社会的,成为人们的一般行为规范,个人的意志、欲念要服从公法,否则即是私。如荀子言:“公义明则私事息矣。”(《荀子·君道》)人的行为能遵行公的标准,这在观念上也就是达到了公正。如《白虎通义·爵》:“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当公被视为社会政治的普遍行为标准的时候,公就具有了一般道德规范的意义。[③]
上述的公实际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君主特殊利益集团,二是指社会一般标准。这两种涵指在实际表述上显然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从传统社会君主政治的本质考察,这样的表达在认识的价值依据上是相通的:即“以君为本”,也就是说,区分公或私的价值标准是君主的利益、权威、意志和名誉。
前一层涵指比较明显,以君主以及特殊利益集团为公,当然是以君主的利益作为衡量公私的基准,明明是特殊政治集团的利益,此时却有了公利之名。韩非说:“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韩非子·八说》)这里,韩非表述的“公利”,所谓“明法度”,“塞私便”,其涵指显然就是“公法”,即是后一层涵指的“社会一般标准”。可是,“公法”怎么会是“君主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呢?
在君主政治的权力私有条件下,任何形式的社会一般标准都必然要受到政治权力及其拥有者的控制,社会一般成员作为政治权力的主宰对象,在政治和社会行为方面并不享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实际承担的政治义务规定是单向度的:无非是应役当差,输粮纳税,作良民。而且,即便有谁能“学而优则仕”,进入统治集团,其所承担的义务仍然是单方面和绝对化的。也就是说,入仕者拥有的地位、权力及其分享的利益仍然是王权的某种分化形式,入仕者分享了政治权力以及相关的政治地位和利益,这一切无非是君主的“恩赐”,而非其具有的“法定权利”。他们代表君主行使某些权力,是其忠君义务的表达。这种表达一旦不能充分,或是失去了君主的信任,恩赐就会被剥夺,所有的权力、地位和利益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这里无需赘述。故而,感戴“皇恩浩荡”成为居官入仕者的口头禅;同时,“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数千年来也始终萦绕在掌权、弄权者的心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法”当然不是社会一般成员的利益诉求,其内涵的只能是君主特殊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然而,检索古人之见,有识之士常常举出“公法”与君主相对,认为君主及群臣也要尊奉公法,不能以私乱公。例如,汉末王符说:“夫国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则轨乱绝。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术用则公法夺。”(《潜夫论·潜叹》)北宋李觏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直讲李先生文集·刑禁四》)司马光说:“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罚者,天下之刑罚,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司马温公文集·言为治所先上殿札子》)这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着眼于君主个人与法的顺应,似乎在君主个人的意志、情感之上,高悬着公法的权威。唐太宗李世民认可了这一点,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依照他的体会,君主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喜怒而滥用赏罚,破坏法度。他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贞观政要·求谏》),致使天下丧乱,于是自省道:“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贞观政要·公平》)显而易见,这些认识里含有某种“公平”观念,正像李世民在自撰的《帝范》中写到:“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帝范·赏罚》)
上述见解以今日的理念评判之,亦能令人感到鼓舞。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君主之私”与“法度之公”确乎是像其表述的那样彻底对立,还是实际存在着某种深层的价值沟通?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身利益和政治系统内部利益分配的需要,都必然要求设定相应的政治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在政治系统内建构具有普遍权威意义的社会政治秩序。这就是说,在君主政治时代,君主及其官僚贵族集团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当然要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规范,并以此为基准建构统治秩序。于是我们看到,所谓公法、公议体现的普遍权威意义,正是维护符合政治权力主体之根本利益的秩序诉求,对此,古人曾用他们的语言做了明确的表述。例如南宋功利派思想家陈亮说:“圣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龙川文集·问答上》)“夫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则仁义礼乐无所措。”(《龙川文集·三先生论事录序》)
以“立人极”为宗旨的公法,在理念上与一切私对立,这种对立的极致便是“天下为公”的最高社会政治理念。因而从根本意义上说,公是传统文化孜孜以求的圣人之道的本质或曰“基本精神”,称为“至公”“公道”等等,其中内涵和体现着的正是政治权力主体即君主集团的根本利益。且看如下表述:
夫至公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三国曹羲,《全三国文》卷20)
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罚不用情。刑罚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西晋傅玄:《傅子·问政篇》)
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南宋陈亮:《龙川文集·又丙午秋书》)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凡所以为人道立极,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同前,《经书发题》)
——这种公道与私的对应,在认知方式上无非是儒家文化“道高于君”思维的另一种表述,在公道与君主个人之私相互对立的背后,是公道与君主之根本利益的紧密相连。“道高于君”思维方式关注的是建构君主政治系统的基本政治价值体系和政治原则,维护的是政治权力主体的全部利益,对于个别具体君主与政治价值体系及君主政治根本利益相冲突或不协调的行为,当然要站在符合君主政治原则的立场上予以匡正甚或否定。
据此,这种“以君为本”公私观的深层逻辑是:君主作为公的化身,是君主政治系统政体利益的代表,在道德上理应是无私的。因而倡言者极力抨击君主个人的私利与私意,要求君主立公去私。如《吕氏春秋·贵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
这种公私观将君主的至公本质无限提升,使得号称“天子”的君主恰好与天道相通,正如《吕氏春秋·去私》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后汉荀悦明确指出,君主不应有私利、私意或私欲,所谓“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怨”(《申鉴·政体》)。西晋袁准认为君主应该树立公心:“唯公心而后可以有国,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为国之本也。公也者,为身之本也。”(《袁子正书·贵公》)北宋李觏要求君主御臣不可有私:“天子所御,而服官政,从官长,是天子无私人。天子无私人,则群臣焉得不公?”(《直讲李先生文集·内治二》)明儒王祎也说:“王者能富万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户,岂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无私故也。”(《王忠文公集·卮言》)传统文化关于这方面的认识很丰富,对于专制帝王来说,“立公去私”的真正意义并非在于实际践行,而是在于给至高无上的君主提出了一个高标准的道德境界,使得君主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在不妨碍或损害君主权威至上性的前提下,能对君主的个人行为有所规劝。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规劝内涵的价值准则只能是对于君主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及君主政治体制的维护,而不会相反。
据上,我们可以认为,以君为本的公私观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站在君主政治的立场上,以君主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标的,而倡导的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其中,否定的是具体的个别君主的个人之私,维护和坚持的是政治权力主体的全部利益!
“以君为本”的公私观,其特质是以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作为标定、衡量公与私的惟一尺度,其中从来就没有对于社会一般成员利益或权益诉求的认定,显然,在这个层面上倡导的大公即是大私!
二、第二层境界:以民为本的公私观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重民思潮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之一。从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主流看,西周初年周公的“保民”思想可以视为重民思潮的滥觞,其后,《左传·襄公30年》载穆叔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此一观念又见于《国语》之《周语》、《郑语》,是知民本的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很普遍。再后,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倡言“君舟民水”,及至汉初贾谊放言“自古至于今,
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集·大政上》),以民为本已经成为传统政治思维中的价值准则,成为思想家、政治家们汇析信息、评估政治和议定政策的一个重要参照点。正如孟子征引《太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
正是基于重民思潮,传统的公私观亦展开了第二层境界。这种“以民为本”的公私观有多种表达形式,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天子为天下”说。
“天子为天下”的命题在先秦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如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慎到:“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商君书·修权》:“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这个认识延及后世,极为普遍。总括其说,大体包含三层规定。
一曰,立君是要君主来治理天下。如汉儒谷永:“天生烝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汉书·谷永传》)王符:“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潜夫论·班禄》)宋儒苏轼:“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东坡后集·御试制科策》)陆九渊:“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为民也。”(《陆九渊集·杂说》)
二曰,君主要利民、养民。宋儒李觏:“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安民策一》)明儒邱浚则把这一层意思讲得颇透彻:“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财,奉一人以为君,非私之也。将赖之以治之、教之、养之也。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殚其力,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岂天立君之意哉!”(《大学衍义补·经制之义下》)
三曰,君主要“公天下”,博爱于民。唐太宗李世民说:“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贞观政要·灾祥》)宋儒李觏认为:“夫溥爱无私,君之德也。”(《直讲李先生文集·易论一》)理学宗师程颐说:“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周易程氏传》卷一)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得更明确:“王者以公天下为心”(《读通鉴论·晋》);“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敬帝》)
以上认识的思维逻辑是十分清晰的,“天子为天下”首先肯定君主的主宰地位,然后确立了君主的职责就是养民,而不是以天下之利奉养君主一人。以民的养、教甚至生死作为君主的道德衡量标准,谓之“公天下”,这种认识正是“以民为本”公私观的立论基点。
这种公私观在价值规定上把民置放于君主政治权力的“基础”位置上,在天子为天下的号召下,除了要求君主爱民、养民,还认为君主理应重视政治公正与公平,关注民意与民情,谓之“公议”“公是”。这样的认识可以说先秦有自,如周公之“知小人之依”[④]。其后则为卿士大夫们代代相继,几成共识。如若举其典型,当属晚明东林党人的“公是”、“公议归天下”诸说。
晚明东林人士在学理上传承孔孟儒学正统,坚定不移地拥护立公去私,他们最为重视“公议”之公,论析的逻辑展开是从“反对密奏”、“公论付言官”到“公议归天下”。东林书院创始者之一,史称曾与顾宪成“分主东林讲席”[⑤] 的钱一本就明确提出反对密奏,要求言政公开。[⑥] 史孟麟则进而要求“政事付六部,公论付言官”(《明史·史孟麟传》),直接触及君权的权力分配和政治舆论问题。再如顾允成:“言路者,天下之公,非台省之私也。”(《小辨斋偶存·上座师许相国》)叶茂才:“天下事非一家私议,何正何旁,期于至当而止矣。”(《东林书院志·叶茂才行状》)他们提出的“天下之公”已经越出了台谏言官的狭小范围,泛指群臣百官之公论。在这一观点上再进一步,就是要将公论归于天下之人。
在公议问题的认识上最有建树者,当推缪昌期。他做有一“论”、一“解”,讲述详明,与东林同仁相较,最有宏见。
论曰:《公论国之元气》,见解可划为四层。
其一,“公论”之说始于孔子:“公论之说,昉于夫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段征引见于《论语·卫灵公》,本义是孔子表白自己不曾凭空毁誉他人,似与公论没有直接关联。且征引有阙文。昉,始也。缪昌期之所以不顾文义牵强也要举出孔子,是要给自己的通篇立论找出合理性依据。有了圣人作招牌,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缪子立论之始即颇具匠心。
其二,给公论做界定。缪昌期提出公论始于夫子之言,但夫子没有给公论下定义。于是缪子随机发挥,他列举了三种情况。他说,“天下之论”,不过是论“是与非”。如果是非不统一,“一是一非,一非一是”,这种情况叫做“异”,“不谓之公”。如果是非完全一致,“一是偕是,一非偕非”,这种情况“谓之同”,也不是“公”。那么,什么叫做公论呢?缪子认为公论超出了简单的是非评判:“公论者,出于人心之自然,而一似有不得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者。夫愚夫愚妇何与于天下事?而唯其无与于天下事,故其待之也虚,见之也明。率然窍于臆、薄于喉而冲于口,率以定天下之是非。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谓斯民,其即吾之所谓愚夫愚妇也。”缪昌期讲得很明确,所谓公论即民意,是不受政治干扰,出于自然本心的公众意见。愚夫愚妇的意见成了天下是非的标准。
其三,愚夫愚妇的公论是天地与国家之元气,公卿大夫则是民众公论的代言人。缪昌期说:“夫愚夫愚妇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气所留也。唯国之元气留于愚夫愚妇之论。”元气者,天地国家的生命生气之所在,缪子认为天地国家的命脉蕴聚于元气,通过愚夫愚妇来体现。缪昌期又说;“夫愚夫愚妇之论岂必出之愚夫愚妇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见,不逞意气,无依附,无迂回,无嗫嚅,无反覆,任其率然之偶发,而与天下万世合符。此所谓愚夫愚妇者也。即所谓元气也。”可知在缪昌期看来,天下公论常常由公卿大夫来表达,也就是说,凡公卿大夫能排除私念、杂念,言论与天下通见相合,与万世通理相符,即可视为公论,亦即代表了愚夫愚妇。缪昌期通过一连串的逻辑推导,把“天下之言”说成是天地元气,国家命脉,,借公卿大夫自命为天下百姓的政治代言人,从而给给东林人士的“公议”参政拓展了宽广的社会基础。
其四,君主理应爱惜公论,自护元气,否则元气受损,国亦大伤。缪昌期在文中设问:“有国者之于元气”,是“摧而剥之”,“壅而滞之”,还是要“培而养之”,“宣而导之”呢?答案很明显:“摧而剥之,则为枯为折,而国大伤;壅而滞之,则为溃为决,而国亦大伤。”他举出东汉党锢之祸和北宋熙宁变法为例证。东汉末年,“寺人专政”,李膺、范滂领袖仕林,谣语品题,讽议朝政。掌权宦官“践蹋冠裳,此愚夫愚妇之所痛也。”汉桓帝良莠不辨,对朝臣忠良之言不予理睬,而且“大考钩党,名士皆见屠戮”。结果,“汉之为汉,其余几何”?北宋王安石推行新法,“骚动海内,此亦愚夫愚妇知其不便者也”。凡对新法有异议者,均被贬斥,以致党争不断,“一转为崇宁,再转为靖康。而宋之为宋,其余几何?”真是事实胜于雄辩,汉末君主和北宋皇帝不能正视公论,拒谏饰非,结果不免败亡之厄。缪昌期还特别提醒君主,大凡诋毁公论者,常常将公论冠以党论之名,将天下百姓之言诬为朋党私见。等到天下之论“如沸如羹”,危机四起行将大乱之时,“乃复归咎于公论,冤矣哉。”(以上征引见《从野堂存稿·公论国之元气》)因此不论从哪个方面看,君主“爱惜公论”正是“自护其元气”。
缪昌期将公论释为民众之论,认识上是一大推进。他自命为民论代表,又以民论为国家命脉,气概不小。这样的“公论”,指的正是覆盖了朝廷与社会的政治舆论。缪昌期的潜台词是:卿大夫只要把握住了舆论,就能积极干预政事,实现政治理想。这一主旨在他做的一“解”中得到了深入阐发。
解曰《国体国法国是有无轻重解》。其文曰:“国有三大,曰国体、曰国法、曰国是”。国体是“虚而不可不存者”。缪子曰:“今夫国之有体,如器之有形,而工之有制也。体之有高卑、贵贱、亲疏、内外;如堂之于陛,冠之于履,表之于里,不可并也。”可知,缪子说的“国体”,指的是君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如等级礼制,君臣体制,尊卑仪制等。国法是“画而不可不守者”。缪子曰:“国之有法,如方圆之有规矩,而低昂之有权衡也”。是知“国法”无非是法律政令之类。缪昌期认为,国体与国法具有至高的权威性,所谓“体之有尊而无亵也,法之有伸而无屈也”,故而理应由“人君独操之”。
与国体和国法相比较,“国是”有些特殊性。依缪子之见,“国是”指“棼而不可不一者”,即“公论”。国是的基本特点是“出于群心之自然,而成于群喙之同然”。因而“国之有是”,源在民间,“则人主不得操,而廷臣操之;廷臣不得操,而天下匹夫匹妇操之”。既然百姓形成了共识,那么天下是非就要以此为准。“匹夫匹妇之所是,主与臣不得矫之以为非;匹夫匹妇之所非,主与臣不得矫之以为是。汇真是真非以成一是,故总谓之是。以其宣之士大夫,著之廊庙。国体籍以尊,国法籍以伸,故系之于国”。(以上征引见《从野堂存稿·国体国法国是有无轻重解》)国是一旦确立,则君臣百官非但不可以随意矫改,而且要树为国政方针,与国体和国法形成相维相护之势。这一番辨析展示了缪昌期的基本立场。
在上述的认识前提下,缪昌期又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彰明“国是”需要国体与国法相维系,此三者不可缺一。理由一:“欲明国是,当先存廷臣之体。有体则人无僄言,无僄言所以明国是也。”理由二:“欲定国是,当先守祖宗之法。据法则人无巧言,无巧言所以定国是也。”缪昌期那臣僚体制和祖宗之法看作明定“国是”的前提和保障,有了国体与国法,则人不敢轻率放言和花言巧语,于是国是可明。
二是国是不能混淆不清,否则与治无补。君主只依靠国体国法治天下,未为稳便。缪子说:“国之有是,犹天之有日也”。可是正像太阳经常要被云雨遮掩一样,国是也会常常陷于混乱。“为国是者一,而议国是者多,借议以淆国是者又多。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之中,更有是非,彼此之外,复生彼此,呶呶籍籍,日与媾斗。”国是混淆无序,是非不一,不能形成统一的“真是非”。再加上“士大夫既以私掩,而所谓匹夫匹妇者无权无力”,他们都不能将“真是非”晓告天下,“则天下之人又不能操其是,势不得不转听之人主”。其结果是“人主与天下人相维相制者,唯有国体、国法而已。”这种局面显然大非缪子所愿。
缪昌期认为“是者天下之所共,体与法者人主之所独。”这两个方面“相维相制”,才会促成政治的稳定和顺畅。如果君主不能操其所独,这是“示天下以轻”,为君者权威不足,如何言治呢?同样,假如卿士大夫们不能“存体”、“据法”,国是不明,不能形成“公论”,那么又怎能与君权形成互倚之势而相互维系呢?显而易见,在缪昌期的设计中,由卿士大夫掌握和操纵舆论,代表天下百姓,与君权“相维相制”,这是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条件下,他所能找到的最佳参政方式。
缪昌期的见解固然高明,却也不是唯一之论,如今讲论东林者常常引用顾宪成与首辅王锡爵的一段对白,也反映了相近的认识。据顾宪成自述:“丙戌(万历14年,1586年)秋,予入京补官。娄江王相国(锡爵)谓予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近来有一异事否?’予曰:‘愿闻之。’相国曰:‘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不亦异乎?’予对曰:‘又有一异事。’相国曰:‘何?’予曰:‘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相国笑而起。”(《小心斋札记》卷一七)
顾宪成以“外人之是非”与“庙堂”相对,立意仍在以天下公论的代言人自居,其思路与缪子之见如出一辙。这段对白见载于顾宪成的“行状”、“年谱”、“传纪”等多种文字,可知时人对“外人之是非”的重视,对顾氏之见的赞许,这段对白代表了东林人士“公议归天下”的共同心愿。
“公议归天下”是东林人士的参政方式,这种方式与君主政治的“非公开”本性直接相对。在政治权力私有的条件下,政治机密既没有时限性,也没有区域性,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政治公开都有可能损害权力私有者的切身利益。因之《易传》有言:“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几事不密则害成。”几事,高亨注:“几读为机”。[⑦] 在这里,儒家文化生而与俱的政治理性演化为政治上的机警和深谋远虑。于是孔子教人“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儒学倡导的崇高理想让位于慎言慎行和循规蹈矩的实用理性。然而,东林人士却要以“公议”、“公论”与政治机密相对,以“天下”、“外人”与庙堂相对。这种对峙的背后当然是东林人士深信不移而抱负终生的政治理想。他们当仁不让,自封为“民意代言”,与当权者对阵。其手段是舆论,目的是制约君权,他们要利用“公论”表达自家代表的士人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显而易见,且不论其效果如何,仅只这种方式本身就不同凡响,其中孕育着君主政治条件下最富合理性的“政治制衡”因素。
平心而论,虽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是王权主义,可也确有不少光彩照人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有关“道义制衡”的认识。[⑧] 道即道义,是儒家文化的政治与道德理想价值的凝聚。在儒学宗师的一再引领下,道被参政的士人们用来评估时政,批评君主,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进谏。在实际政治运做过程中,君主的权威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和威慑力,与之相对照,道义原则不过是人们认可的价值准则,进谏无非是话语的规劝,因而这种制衡不具有实践上的政治强制性,而是仅仅作为君主政治的某种调节方式偶尔有效。政治制衡是政治理性最典型的体现,儒家文化中的“道义制衡”所具有的政治理性及其合理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不过,道义制衡只拥有认识上的权威性,它的运作过程被完全纳入了君主政治的运作系统,它的实现程度受到君权及其相应的多种条件的节制。因之,道义制衡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政治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的方式,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相距遥远。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晚明东林人士竭力争辩的“公议归天下”,他们的思路和设计大体上没有越出“道义制衡”的理论框架,也是以道义原则和话语规劝作为其中的基本要素。不过,在制衡的表达方式上,东林人士有所推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明确要求以愚夫愚妇、匹夫匹妇之是非为真是非,从而在传统的道的理想中加入了某种“民意” 的成分,民众公议成了制约君权的力量策源点。二是他们一改传统的代替圣贤立言的话语表达方式,赫赫然以民众公论的代言人自命。这些认识上的细小变化意味着东林人士在思维导向上已经朝向民主政治思维迈出了一步。可是,转念之间,我们又发现东林人士的致思逻辑和政治价值的选择上仍然顶着高高的君父帽子,正像缪昌期张扬国是,却又放不下君主独操的国体与国法,于是他们难得迈出的步子又踱回到尊君的老路上,令论者不无遗憾。
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东林人士关注一般民众的是与非,可是,没有独立人格和法制权利做根基的“民意”是无足轻重的。缪、顾诸子口口声声不离“愚夫愚妇”、“天下”、“外人”,但这不过是传统重民思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在他们的心目中,民依然只是维护君权稳固的必要条件。缪、顾之论尽管在认识深度上超出孟子、贾谊,可说到底也不过如此而已,这毕竟与民治民有的政治民主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东林人士坚持以“公卿大夫”做愚夫愚妇的政治代表,民众的是与非,亦即天下百姓的“利益表达”需要经由特定的士大夫集团做媒介。然而,在东林人士的思维视野中,我们看不到任何针对卿士大夫的监督和制约,代表者当仁不让,被代表者听之任之,其结果难免会出现下面的情况:愚夫愚妇的是与非被卿士大夫的是非所取代,而一般民众的政治利益及其表达仍然是零。一般来说,政治权益“代表者”的产生如果不是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其所执掌的权力没有切实可行的“授权程序”做根基,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有效监督与制约——这一切都被“代表者”理所当然的“自我肯认”所取代,那么,这种“代表”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夺”罢了。
晚明东林党人在“以民为本”公私观的表达上最为激越,然而他们依然难以走出儒家文化的思维盲点。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这种公私观的特质是,以社会一般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与“政治权力主体”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作为标定、衡量公与私的尺度,持论者满心以为“公”在“天下”便是找到了真正通往“立公去私”和“天下为公”的坦途,殊不知他们依然难逃天子“私天下”的彀中。难怪参透了这一切的黄宗羲要捶胸顿足:“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归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原君》)。
三、第三层境界:以人为本的公私观
通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以民为本”的第二层境界实是传统公私观的至高点。由于近些年来,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的“新儒家学派”们的竭力提倡,“以民为本”云云很容易使人误解其中含有现代政治因素,以为大公无私古已有之,连封建帝王及卿士大夫们亦能思之行之。
然而,如果我们稍作思考,就会发现在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私有的政治条件下,社会一般成员不具有政治主体地位,在思想观念和政治价值构成中,也不存有这样的认识。因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能跃升到公私观的第三层境界:以人为本。
在现代政治理念中,人是世界的主宰,一般社会成员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是政治主体,个人的生存、发展和选择的自由得到法律权威的维护,个人的尊严、拥有的权利义务和政治人格则神圣不可侵犯。以此为基本条件而构成的“以人为本”,是以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个人为本,这种理念与传统中国的以民为本有着本质的差异,因而与之相应的公私观境界亦迥然不同。为了说明此中缘由,需要先就政治主体问题略作解释。
依照现代政治学理论,所谓政治主体(political subject)即是政治行为者。由于人的政治行为的多样与复杂,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关于政治主体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简单划一的。至少,政治主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政治主体”,另一是“政治权力主体”。
社会政治主体是从广泛意义上对于政治主体的一种理解。相对政治环境而言,一般社会成员都是主体,也就是具有一定的政治认知、具备政治人格和政治参与意识的人;从现代法制社会的角度看,社会政治主体对于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具有相当明确的自觉。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主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个体的公民、群体的社会政治组织等等,诸如政党或利益集团组织。概言之,社会政治主体指的是政治系统中的人,正是由于人在政治系统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基于人而形成的政治关系,我们所理解的政治,诸如阶级、政体、政治行为和政治运作等等才是有意义的。
政治权力主体是对政治主体的一种狭义的理解。相对运作中的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宰制范围内的一般社会成员,执掌和操作政治权力的成员构成政治主体。这类政治主体基于其特殊的政治角色规定,而在政治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其政治行为所设计的对象具有支配力。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主体主要包括最高统治集团和政府官员,以及在政治权力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党或政治集团。换言之,政治权力主体指的是政治系统中的掌权者,相对政治制度、政治设施和政治输入输出过程而言,他们的主体地位和支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和辩证发展的。简言之,在现代社会,社会政治主体的理念和实际政治行为的彰显与强化,使得相对于政治权力主体的政治客体即其支配的对象物的存在境况具有了不容漠视的相对性,因而使得社会政治主体在其主、客体重叠运作的过程中,对于政治权力主体的制约或限制明显增强,于是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民主性质才会有所保障,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也将不断提升。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公私观,便是我们所认为的“以人为本”的境界。所谓私,主要涵指上述的个人权利与人格等个人主体意识;所谓公,则是基于个人权利或合法利益而形成的公共理性。私有法度,公有秩序,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明有序,与之相应的公私理念便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根基之一。
与前所述相对照,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权力主体”思维得到政治哲学的深层论证和政治操作过程的不断强化,君主及其麾下的贵族官僚集团实际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作为拥有政治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将社会一般成员置放于恒久和绝对的政治客体地位,“社会政治主体”思维的极度弱化不仅没能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政治主体意识,而且,在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思维层面,干脆就将“个人”从中剔除了。于是,源自先秦的公私观念缺少了从“民本”向着“人本”跃升的逻辑阶梯和内在推力,结果导致了公私观念似是而非,混淆不清。无论是以君为本,还是以民为本,公与私在其根本价值准则的认定上是含混的,于是所谓民本或重民无非是“政治权力主体”基于相应的政治理念和实际利益需要而作出的单向度选择,孰公孰私,论公论私,最终的裁决者正是政治权力的所有者。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只有以现代化社会为坐标,以一般社会成员即每一个个人的社会政治主体地位的绝对确认作为认识的起点,我们关于公私观的阐释才有可能是合理的。正因为如此,所谓“大公无私”,“立公去私”,“无私奉献”等等,在社会政治主体定位含混、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模糊不分的情况下,必然会成为个别拥有权势者或特殊利益集团谋取私利、剥夺他人和制造不公正的工具。
——环顾当今之中国,或公或私,亦公亦私,多少不义假汝之名,哀哉!
--------------------------------------------------------------------------------
[①] 本文发表时署名与张长虹合作。
[②] 南街村号称“豫中一支花”,地处豫中平原,临颍县城南隅,紧靠京广铁路。1996年初统计,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742户,3200人,2006亩耕地,面积1.78平方公里。该村实行集体主义管理,对外则参与市场经济,以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为发展方向。
[③]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先秦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门、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平分、公平、公正。本文见解与之相类,略有不同。参见《中国思想史における公と私》,《公と私の思想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P.37。
[④] 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⑤] 钱一本:字国瑞,学者称“启新先生”,武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曾任知县、御史等。因谏言忤旨,免官家居,为东林书院首领之一。
[⑥] 参见《明史·钱一本传》:““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启言事,先臣弗为。今阁臣或有救援之举,或有密勿之谋,类具揭帖以进;虽格言正论,谠议忠谋,已类斜封密启之为,非有公听并观之正。况所言公,当与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
[⑦]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523页。
[⑧] 参阅拙文:《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的政治心态》,载《史学集刊》,1992 年第3期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