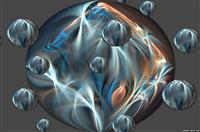凤凰卫视7月15日《社会能见度》节目:中国家庭教会调查,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团体要按规定来办理登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大幅增长,家庭教会相应激增,但一个公开的事实是,这些家庭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规定登记,处于“地下”状态,人数超过千万。这样的组织状态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为何游离于监管之外,为此我们也采访了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解说:于建嵘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小房间来,用于收集和家庭教会有关的资料。他感到,近两年来,随着政策的宽松,他所研究的处于“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也能够见得阳光了。
于建嵘:家庭教会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国家委托的一个项目,国家有个部门,当时它有一次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多部门开会,有一个部门汇报了家庭教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建议,就是说进行打击,我当时提几个看法,我说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打击,到底多少人,怎么活动,当时汇报时发生争议了,争议了有一个领导说那你去搞清楚,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去搞清楚。
解说:于建嵘和他的团队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十多个省展开调查。他们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中国基督徒人数。根据中国宗教事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基督教徒约1000万人,但因为家庭教会的大量存在,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这
记者:根据你们调查的结果,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教徒大概有多少人呢?
于建嵘:西方有一些宗教组织,说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亿二千万,国内也有一些家庭教会说它有八千万,七千到八千万,根据我们的调查,大约四千万左右的这样子,全国的基督教徒应该在七千万左右。
记者:其余的那三千万都来自于“三自”教会。
于建嵘:“三自”教会,应该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因为这个数字很难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
记者: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官方的数据如此之少,而西方的数据又如此之大呢?
于建嵘:官方的数据小,我曾经有一个故事,我到河南省的一个地方去调查,河南省那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很多,教会基督徒也很多,发展得特别快,我一问宗教局的领导,他们一个领导陪我去调查,我说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报呢?他说这个不能,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他说,我说怎么呢,他说又不像种树,种树可以多报一点他说,这个报多了中央领导也不高兴,我们一般总的原则往小的报。
另一个方面,可能现实调查地区也有关,关于统计还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不好确定,你说什么叫基督徒,你不是共产党员,党员要发证书,大家知道,那基督徒他说他受洗了,他有些没有,有些叫慕道友,所以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很难统计,就为这个数字我们开了两次会,讨论,请一批各种人士讨论,讨论之后,我们大概确定在七千万左右是比较确定的。
解说:1950年7月,基督徒吴耀宗先生倡导发表《三自宣言》,即“自传、自治、自养”,号召“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获得全国教徒的热烈响应。到1954年,签名拥护宣言的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占当时全国新教教徒人数的三分之二。但是在这样一个热烈的局面下,根据于建嵘的调查,那时家庭教会就已经存在了。
于建嵘:当时实际上政府也没有完全拒绝他们,因为你们几个人聚会在一起,聚会在一起也没有,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因为一旦变成,大家几个人聚会,可能政府你们都信教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一旦久了之后,它有个固定的场所,它必须固定的人,还有一些比如讲,你神职人员开始产生了,所以政府是当然要打击的。
记者:这个打击大概是持续了多久,在哪一年?
于建嵘:打击应该一直到文革之后,而且文革的时候,而且原来“三反五反”“打反革命”那些政治高压下,文革的时候比较严重。
于建嵘:我们在温州调查,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越打击它,越发展得快。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于建嵘:就这个原因,我当时在温州,我也去访问了很多人,它有一个,它的教义中间有一个赎罪心理,就我遭到打击越严重,我离上帝越近,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带来了反弹,所以很多人加入了这个,我更有动力去发展人去入教,那么这个是反而发展得很快。
解说:改革开放以后,更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在中国推开,一批在六七十年代放弃宗教信仰的人又开始公开信教,而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大量进入教会,城市家庭教会也发展起来,写字楼、出租房或者家庭中,都成为他们的聚会场所。
记者:那现在这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的活动,多半是公开的以宗教的名义进行呢,还是说也有的是偷偷的秘密进行的?
于建嵘:基本都是公开的,我见到这些教会他们现在都不隐瞒。还有很有意思,我们认为信教都是私人的事情,你到湖南去了他都贴在门上,贴对联,我们家信教,我们家有教会贴一个十字架,贴一些对联。
记者:这对联上一般都怎么写?
于建嵘:都是感谢感谢主啊,什么什么嘛,都是这个宗教的一些话语,贴到对联上去。
记者: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是基督教徒。
于建嵘:对对,所以这个中国的,他现在隐瞒下来的很少。但也可能有一些地下的,我们都不知道的,也有,但是那些我分析,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你去和他交往之后他都会说我是信教的,我怎么样,他会告诉你。
解说:这是我们在一次采访中拍摄的画面,老奶奶的孙子讨要工钱被人砍伤,她就不断地向主祷告,这个一无所有的家庭在宗教中得到现世的精神温暖。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基督教的符号,一贫如洗的家庭也不忘在显要的地方贴上关于信仰的对联。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地方政府采取了怎样的管理方式呢?
记者:那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当地的基层政府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
于建嵘:有不一样,有些地方它是一个装作不看见,就我在这一项调查,调查家庭教会,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家庭教会,就问那个地方官员说,你们家庭教会有没有啊,他说没有,没有。我说你看看,因为他那个家庭教会,不像我们说躲在家里,他已经打了很大的牌子,很大很大的牌子。
记者:牌子上写的什么?
于建嵘:叫做基督教聚会区,很大的一个牌子,它也不是教堂,挂了个大牌子,那么我一说,你看看那个地方不是有吗?他说没看见,我说你看看,我都看见你没看见,他说没看见,我说为什么,他说中央没看见,我怎么看得见,另外一种以非法聚会的地方进行打压,还有一些地方,最近一个两个月来,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取缔你这个地方,我现在要通知你这个房主,你不能租房子给这些人,你没办法了吧,所以讲公开对抗有过,公开对抗,也就是所谓非法聚会的名义,但是主要的方式还是比较软,比较软。很多的大量的地方,会装作没看见,没看见,我看不见。
记者:有没有一些家庭教会的成员给您描述过,当他们的活动被取缔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
于建嵘:对,不但描述过,他们还给我看过录像,我到浙江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给我看录像,取缔他们的时候,她说他取缔我们我们也不对抗,我们照样拿着我们的《圣经》,寻找我们的上帝。
记者:那他们的心中会对采取,比如说打压措施的这些人会有愤恨吗?
于建嵘: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当时给我回答两个,第一个,这种苦难可能是上帝要他接受的,我们只能接受它。另外一个说,我们向上帝祈祷,我们祷告,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很少有人问到说,我们去怎么样怎么样,很少的。
曾子墨:关于集会,中国1989年通过的《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但是大量存在的没有按规定到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的家庭教会,他们的聚会显然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规模,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否又会成为“邪教”的土壤呢?
解说:在于建嵘收集的资料中,有关于“三班仆人教”的全部资料。
2006年2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邪教杀人案,一个被称为“三班仆人派”的地下教会涉嫌杀害另一个地下教会“东方闪电派”的信徒多达20人。双方都自称基督教,都被公安部定为邪教组织。争夺信徒是命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规模对家庭教会有什么影响呢?
于建嵘:情况不一样,因为家庭教会它也有一种组织结构不一样的,有宝塔式的家庭教会,有一个总负责人,下面的不同,这个有些发展下来,可能也有几万人,也有些扁平式的,就是互相之间都不隶属关系,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家庭教会一般的,有两三百人,三四百人的也有,也有一千到两千人,但是它没有一个严格的这个人员的隶属关系,比如说我今天这里,可能一个大教堂,很多人来参加活动,做完了就走了,那种隶属关系的,很严格的隶属关系的,往会走向一种很严重的问题。
于建嵘:这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全一样,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基本方式是一个宝塔式的。比如“三班仆人教”,他有一个大仆人,二仆人,下面有使女,各个省有使女,是吧,有各个省,有不同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上下关系的一个教会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应该说组织比较严密,而且人员是比较固定,另外一种现在更多的家庭教会的方式,就是比如讲,它有几个知事,有几个管事的人,我们租了一个地方,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租来一个地方,我们做宗教活动,我们请来一个有宣道的神父,是吧,我们互相之间有管钱的,有管事的,也有几个人,也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它基本上,这种大的现在就是各个教会独立的情况,这个比较多,这种反而比较多。但是在河南的很多都是宝塔式的。
记者:这和所有信众教徒,他的知识架构,他的眼界有关系吗?
于建嵘:有,应该有关系,一般的知识分子,知识比较高的,他不愿意加入那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教会的,而农村有些反而愿意加入这个东西,我就在河南的农村调查的时候,有人就愿意,说这个好啊,兄弟姐妹多了,互相帮助的人多了,我可以找到人,是吧,我出了什么事有人帮我。
解说:在许多家庭教会内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并且他们有专门的培训系统,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教会培养输送神职人员。而这一套体系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没有一个规范的模式。有的甚至处于地下状态。
记者:那内部的学校培训体系是什么样的?
于建嵘:我最担心的是这个,当时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他们都赶过去看我,因为我在那里调查,他们刚好礼拜天去了,去的那一天,我带他们看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学校,他们当时都目瞪口呆,我们到了一个写字楼,外面也看不出是学校,不是写字楼,就是居民楼,坐电梯上去之后,一点都看不出,一个普通的居民楼,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里面有20多个孩子在里面做培训。而且这20多个孩子三个月之内不能离开这个门,包吃包住,你们就在这里。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心里充满着一种幽怨,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你们教他什么,他们怎么来的,从网上招聘来的,有些还是大学生。
记者:要付学费吗?
于建嵘:不要付学费,包吃包住,不要学费,将来还有份工作,你去宣道,你想对有些现在这个社会是有吸引力的,我不是说这种学校本身有什么问题,我担心它什么地方,因为它教育了什么,学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整个社会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不知道,他在里面,我最担心的实际上是这问题,所以我在国家提出来,我说你不如让他公开办,是吧,我好管理。
解说:于建嵘在调查中发现,江浙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一些家庭教会甚至有自己的教堂,或者为了回避行政管理,把新建的楼当作教堂,有的可以容纳几千人。
于建嵘:也有人怀疑有些教会是不是境外资金,这个我讲心里话我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这个也属于人家的核心机密,人家也不一定告诉你,但是我的了解,主要还是靠他们教徒的奉献。
记者:很多人担心家庭教会会成为中国的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最主要就是境外资金由此来渗透,您有这种担心吗?
于建嵘: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担心这个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境外的资金渗透,它终究是有限的,而且你这个国家这么严密的控制,是吧,你的资金来源什么什么都控制,我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怎么对待它们,因为发展规模到一定地步之后,你怎么办,你怎么对待它。你比如讲北京的守望教会,人越来越多之后,你政府你不给他登记,那么你肯定要想办法对付他,政府怎么对付他呢,你是说要老板不租房子给他了,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冒着雪,站在雪地上做祷告,你这回怎么办。怎么对待它可能是我们目前的关键,我认为它稳定或者不稳定,最关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记者: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就您说的,“怎么对待”,这样的一个政策迟迟没有方向呢?
于建嵘:最近两年,实际上据我了解,因为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越来越认识到这问题,所以组织了我们调查完之后,有些部门组织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调查。我当时给中央,对策提了三条,第一,我说与其我们装作不看见,还不如合法地认可它存在,因为没有办法,没有退路,你几千万人,你说取缔能取缔得了吗,取缔不了,那还不如说你合法存在算了,干脆让你合法化。第二点要它登记。第三点,我的观点就是,你的这个教会的学校,你要公开化,你不能搞秘密化。我曾经有一句话,叫做,秘密化有利于邪教的传播,他愿意信让他信去,但是这个信是要管理的。你包括一个人,很多人在这里聚会,你安全也要管一管,是不是,通风道有没有,管理还是需要的,但是这种管理,我的意思就是,不是一种批准制,不是说你批准我就可以信教,你不批准就不信教,不是,但是备案是可以做的,是不是?
解说:河南有一个被称为“哭喊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七灵派”“东方闪电派”等教派,假借基督教的名义与基督教家庭教会争夺信徒。对于普通的农村老百姓,怎样才能区分这些教派和家庭教会呢?
记者:现在有家庭教会他们自己主动地去做这种社团法人的登记吗?
于建嵘:有,但是都没有给他们登记,都不给他们登,有啊,很多,很多。
记者: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主动去登记?
于建嵘:还是想合法化,因为实际上宗教,你研究宗教你就知道了,你越给他秘密化,你越给他压力,他可能发展得越快,宗教的,它这种不登记状况,他是一种他内心的一种非稳定状况,非稳定状况,他要形成的是他的保护。
解说:邪教在中国的危害已然显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河南农民徐双付开创“三班仆人教”,此人自小信教,据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信徒百万。
同期: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那时候傻就傻到这里,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就不敢违背。
解说:“三班仆人”教派的宣教资料声称,他们所信仰的就是全本《圣经》的基督教。徐双付假借神的名义著书立说、传经布道,说自己能行神迹救人脱离苦难,用祈祷为人治疗癌症等。
在九十年代他就买奔驰车、住豪宅、戴价值20万元的劳力士金表,一副眼镜价值一万元,并在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投资,包括修车厂、印刷厂、饮食店、旅社等,这样他可以在很多地方秘密行动。起诉书中显示,他在各地共诈骗人民币2050万元。
记者: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家庭教会,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为邪教,比如说像“三班仆人案”。
于建嵘:“三班仆人教”,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宣道的时候,都是把所有的窗子盖着的。当然你假如都是能够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的话,另外一批人来宣教的时候,说我们必须把窗户关了,怕政府打压,那么马上有人可以识破它,由于你政府的这个宗教政策,使另外一些有歪门邪道的人可能利用,所以他来说,我们要把这个窗户都拉开,拉起来,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信教,政府要打压,那么他在跟邪教,我的观点就是,秘密化往往是邪教的一个最好的外衣。
记者:那在邪教和正规的宗教传播之间,怎么样来区分它?
于建嵘:这个应该是交给教会的事情,交给教会。至于是不是邪教,实际上政府是很难界定的,他说上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那句话那么说的,他们两个争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法律规范是明确的。
记者:但是在不同的家庭教会之间,彼此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组织架构的情况下,即便判断了是邪教又能够怎么样,可能政府是不是,更多地出于保护人身安全的考虑,来判定是否是邪教?
于建嵘:是,这个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宗教你也没有裁判所,你也不搞裁判所,实际上它这个什么问题,我们说交给宗教,也不是交给某个宗教组织,交给信徒们,他们自己的一个判断。你看我在那个,在那个浙江调查的时候,他们就专门揭露有一个“东方闪电”,这样去发展人入教的,他是坏人。
记者: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于建嵘:他们贴墙壁,每个人都发手册,实际上这种人到你们这来,用美女用什么东西来让你传道的,说你们家里生病什么什么,你们不要相信,这叫“闪电派”,它自己内部会发生教徒去抵制它。
解说:同样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河南一位平民女子,自称“女基督”,创立了“东方闪电派”,说自己是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的闪电”,相信她的人,将被她的话熬炼成为得胜者,在千年国度中与她一同做王,用铁杖管辖万国;而拒绝她的人,将遭受各样的刑罚直至灭亡。有关资料显示,他们也拥有了百万信徒。这个组织同样被政府定为邪教。
记者:但像邪教,它一般都会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于建嵘:邪教的特点主要有这几个特点,搞得很神秘,特别神秘,特别神秘,好像天天马上要遭到打击一样,为了所谓逃避打击,搞得很神秘,神秘是它的第一大特点。第二大特点就是说,它一般的有一个相对而言,有一个比较严格的组织系统,说我必须服从什么人,服从什么人,谁管理,这个有个组织,有一个上下关系,第三你一定要付出,是吧,不管你是不是自愿,通过想尽一切办法,你必须要付出,是吧,或者给钱,骗钱骗色是最主要的两样东西。
记者:那还有人担心家庭教会大规模地发展,会对中国现有的执政理念造成影响,特别是如果一些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加入某个家庭教会,让整个组织为自己所用。
于建嵘:这个担心现在是可能执政的人最重要的担心。实际上也不可怕,因为根据我对基督教的研究,我曾经讲了这么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做,精英们不要把基督教当工具,比如搞民主也好,搞什么也好,大家不要把它当工具,它应该归源于一种社会生活,那么政府也不应该把宗教当敌人,因为宗教是没办法通过政府的公权力来消灭的,社会也不要把信徒当异类,更多的信徒的确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他不是想为了,我加入这个东西我将来得天下,没有这个想法的。
记者:那您认为宗教和政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于建嵘: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来是扯不清的关系。从历史到现在,宗教,因为宗教发生的战争,因宗教带来的迫害,世俗权力和宗教之间的,对宗教的利用历来是没有能够完全把它分开,但是越来越到了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关系,是这么多年来,许多现代国家处理宗教与社会政治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准则,政教要分离。所以讲我为什么提出那个观念就是这个意思,要把它回归到一种社会生活。
曾子墨:正如法律所规定的,信不信教是公民的个人自由,但如果他们的组织没有一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无从谈及政府监管和组织的健康发展。两年前于建嵘还在极力地呼吁给家庭教会“脱敏”,如今已经可以有讨论家庭教会问题的宽松环境,也许不久的将来,家庭教会将会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