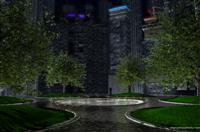摘要:泰勒认为,中世纪的社会观念、教会、主体权利的法律观念、相对独立的自治市、中世纪政体的结构等是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形成的根源;哈贝马斯则认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合法化主题”是“世俗化”、“理性的法”、“抽象权利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主权”、“民族”等五种要素的复合体。实际上,西方政治转型是经过一个从二元分离到一元同构再到二元分离的过程,在国家与教会的二元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它所造成的权力二元以及权利双生为宪政民主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样式。因此,把握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传统资源与现代因素成为认识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那幺,西方社会又是如何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呢?这一分离的动力何在?这显然是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此处仅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两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线索,对比分析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动力资源。
中世纪的社会就像“一块由各种统治形态缀成的百衲布”,这样一种多重统治力量的格局产生了一种“格利佛效应”,也就是:“每个人都被无数绳结绑着,其中任何一条绳子都不足以将他定住,但所有的绳子合起来即足够将他定住。”[1](p322)
对中世纪这块“百衲布”,泰勒的评价可能更为全面。在泰勒看来,中世纪的社会已经不再像古代希腊和罗马那样由政治来界定,而是取得了与政治共同体平起平坐的地位,人们甚至将国家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更为有益的是,教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与政治共同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二元格局。就世俗社会的制度安排来看,主体权利的法律观念、相对独立的自治市、中世纪政体的结构等三种力量为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泰勒从市民社会成长的实践样式和观念形态两个角度出发对西方市民社会形成的传统资源进行评估,为我们理解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提供了一个大纲。泰勒自信地指出:“我们可以从所有上述5个方面中找到西方民主自由的根源”。[2](p11-12)
泰勒的综合式描述显得无懈可击。因为,他所描述的这5个特征是可以追之于历史的,泰勒的反对者亦不能否定这5个特征同民主自由的联系。然而,泰勒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于,他需要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实是,只有在这5种特征发生重要变化,甚至是烟消云散之后,西方社会才看到民主、自由的影子。
泰勒自己亦承认,“在当下和那一时代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阶段,亦即欧洲大部分地区在现代早期企图建立君主‘专制’体制”。但是,泰勒却并没有将一元主义的复现在中世纪的二元主义与现代的二元主义之间建立起联系。他将这样一个决定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事件归因于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即专制主义终于没能求得更大发展,其基本原因乃在于“原本较弱小的国家先在经济上尔后在军事上获得了成功,其中尤其是英国和低地国家,它们所采用的乃是另外一种更基于共识的模式”。[2](p12-13)
泰勒的评价项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形态的,中世纪的社会观、二元政治观以及主体权利的观念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制度形态的,相对独立的城市和中世纪政体的结构显然属于这一类。我们看到,在这两类因素中,后一类制度形态的因素基本上被民族国家的兴起所消解,而前一类观念形态的因素也只是经过世俗化的洗礼和现代化的转义才得以在现代政治当中体现出来的。
就历史进程来看,国家与社会的领域分离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族国家兴起等一系列事件。在这一进程中,首先是教会成为欧洲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宗教改革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教俗权实现分离,将教会对国家的影响降为最低;然后是封建的庄园丧失独立性,被迫融进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与此同时,城市的独立性亦在强大王权的压力下变得岌岌可危……在民族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逐渐解体,从而将领域分离的制度资源消耗殆尽。
领域分离的文化资源亦遇到同样的情况。文化资源发挥效用的方式是潜层次的、间接的。尽管人们很难评估文化资源在领域分离中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主权观在整个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所主张的国家权力不受任何其它权力约束,是最高权力的观点已经全面地否认了中世纪那种将政治机构视为社会组织的观点。在促成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观念形态当中,主观权利的作用可能更为复杂,也更为引人注目。然而,在拉丁文中Jus(ius)与英文中的right、德文中的recht、法文的driot以及意大利文中的diritto之间,其差异是巨大的,只有现代性的反思才能在两者之间实现沟通。[①]
更为不利的是,传统社会,尤其是中世纪的主观权利观念、社会观念等重要文化资源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制度化水平,这就又限制了其效用的发挥。极其重视传统社会,尤其是基督教对近代西方影响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亦认为:“如果我们仅仅是谈论制度水平,那幺它在古代是很低的,它无法实现自由。然而在理念的王国里,它的功劳是很大的”。[3]( p349)因此,过分强调领域分离的传统资源显然并不合适。
在这五种要素中,对市民社会的形成构成最为重要影响的是中世纪的社会现实与观念。泰勒认为,中世纪的社会观是“一个重要的分化,是后来市民社会概念的渊源之一,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根源之一”。[2]( p11)这种社会观的影响极其深远。例如,中世纪那种国家是一种社团的观念直接影响到美国革命的旗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潘恩曾明确指出:“政府不过是按社会的原则办事的全国性社团”[4](p233)限于篇幅及主旨的限制,本文仅从“国家—教会”这一中世纪的二元政治及政治观主题出发,具体考察传统因素对“国家—社会”分离的影响。
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对近代西方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甚至说是近代西方政治现代性之间发生勾连的方式来看,我国学者丛日云认为,经过16到18世纪的惨烈厮杀,“中世纪政教二元化权力架构已经演化近代自由民主政治,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也已经蜕变为近代自由主义”。[5](p105)在谈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与宗教改革者的国家观之间的关联时,美国学者肯尼斯·米诺格(Kenneth Minogue)使用了“翻版”[6](p41)一词,突出了两种体系非同源的相似性。本文认为,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以“国家—教会”为样式的传统二元分离和以“国家—社会”为样式的现代二元分离之间构造了某种文化上的比类和惯性,是以一种“拟制”[②]的方式影响到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的。
以格列佛效应来看,中世纪“国家—教会”二元分离中的国家与教会是所有“绳子”中最强有力的两条。从中世纪的总体情况来看,国家控制了世俗领域,教会控制了精神领域,“政权”与“教权”这两条绳索交织,从本质上将人固定在社会生活的坐标系上。因此,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本质上说是双重的。
基督教二元政治本身就既是现实样式,又是观念形态。古代希腊为西方贡献了民主,古代罗马为西方贡献了共和,中世纪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贡献却恰恰是非政治而又远胜于政治的。当基督宣布“恺撒的归给恺撒,上帝的归给上帝”时,他不但开创了二元政治,还为基督徒的二元政治观提供了一条“伟大的宣言”。在赋予世俗权力以它以前从未拥有过的神圣的同时,也给它加上了它以后一直试图摆脱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阿克顿断定,这句话“是对专制的否定,是自由的新纪元的开始”。其原因就在于:“在至高无上的领域保持一个必要的空间,将一切政治权威限制在明确的范围以内,不再是耐心的理论家的抱负,它成为世界上哪怕最大的机构和最广泛的组织的永恒责任与义务。这种新的律法、新的精神和新的权威,赋予了自由以新的涵义和价值。这种涵义与价值是人们领悟到自由的真理以前,那一时期希腊或罗马的哲学或政制中所不具备的。”[7](p55)
应该说,阿克顿此言道出了中世纪在西方政治史上的独特贡献。当基督徒第一次用“现代”一词将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时,他们在教会与国家之间所采取的态度和做出的区分确实为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增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多元面向。基督教在政权与教权之间做出的这种二元分离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变化”。[7](p347)
在中世纪,人们自然而然地认可并维护着一个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并与之竞争的教会,这造成了西方中世纪的二元世界,成为一种特殊的领域划分,它特别容易发展为国家与社会的领域分离。我国学者丛日云指出:“基督教关于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会与国家的对立到自由主义那里演变为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原来由教会与国家分割的领地现在由市民社会与国家分享,原来个人物分属上帝和恺撒,现一部分属于国家,另一部分归个人自由”。[5]( p96)
宗教的“超验正义”限制了世俗王权的过分扩张,权力有限,国家权力应该受到制约的观念为法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现代西方宪政观念的重要部分。美国宪政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希(C. J. Friedrich)认为:“随着中世纪秩序的发展,一种对统治者滥用其受委托权力的行为积极予以抵制的学说被广泛地确认”。[8](p19)教权与政权的争夺不但让西方文明从一元主义的围墙中伸出一只脚,而且打开了绝对主义国家权力体系的缺口,为西方二元分立的权力体系提供了支撑。在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中,尽管人们看到的是“教会之域”而不是“社会之域”,但是,这一领域的存在与独立却于无形之中为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打造了一堵围墙。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国家与教会分离的事实已经在个人观、国家观、权力观等方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成为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基督徒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观念对西方的政治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宗教改革历史性地成为这种影响的传递者。尽管宗教改革者抨击罗马教会,主张改革教会,主张“唯信称义”,但是,中世纪基督徒所特有的二元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观念基本上被保留下来,并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改造,这使得宗教改革者能够以一种超脱的姿态形成基本的政治观念,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在宗教改革者那里,“属灵的王国”和“俗世的王国”、信仰与理性、民族国家与民族教会、基督徒和臣民等一系列区分使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得以延展,而在此基础上萌生的工具主义的国家理念、以职业为背景的平等理念、教会民主的组织形式等要素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治现代化的进程。[9]
然而,近代以前的领域分离并没有切实的保障,与国家领域相抗衡的社会领域还远没有成熟。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的渗透是经常的,很少受到强有力的抵抗,这常常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形同虚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中世纪,“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10](p284)
随着西方社会世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教会的“绳子”越来越松,国家的“绳子”却越来越紧,中世纪二元均衡的政治结构出现了危机。因此,摆在现代化进程第一位的是对中世纪二元政治的清理,而不是延续。传统二元的破除与现代二元的建立不是一次蜕变,而是一场再生。
中世纪的二元与现代的二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就时间顺序来看,中世纪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二元与现代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二元被专制权力的一元论割裂开来。以世俗政治为基础重新确立二元社会结构正是近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与前提,现代的入口。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Frederich Watkins)指出:“在西方教会与国家本是分立的制度,传统西方文明便运用于社会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如何以纯粹世俗制度为基础,保存这一二元体系,便成了现代政治的课题”。[11]( p49)
泰勒的评价偏重于对传统的阐释,试图揭示其与现代的勾连;与此相比,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更强调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从而为现代二元政治的形成提供了更为成熟的思考。哈贝马斯认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合法化主题”是“世俗化”、“理性的法”、“抽象权利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主权”、“民族”等五种要素的复合体。[12](p197-199)这一论证方式不但以“主权”和“抽象的权利”凸显了政治现代化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双重主题,而且以商品交换、世俗化、理性的法、民族等要素勾画了政治现代化的背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出发,构成了领域分离的现实动力。民族观念和主权观念的出现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成为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政治之维;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则成为领域分离的经济基础;世俗化、理性的法以及抽象权利观念显然从文化的角度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提供了论证。这些要素构成了国家与社会领域分离的现实性,从而为西方政治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全景图式。
尽管人们可以从西方政治传统中找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蛛丝马迹,并且由政治文化传统发现其思想的传承,但是,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分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政治文明二元结构的只能是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二元文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构造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在一系列现实性要素的不断冲击下,西方社会逐渐完成了从中世纪“现实的二元论”向近代“抽象的二元论”[10](p284)的转换,从而实现了现代的领域分离,为新的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观念长久地成为“现代欧洲社会思想的核心”,并“规定了欧洲国家的政治日程”。[13](p64)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近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特征。到16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成为欧洲的普遍政体。法国在欧洲大陆树立了榜样,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王权不但控制了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同时还制服了法国教会。都铎王朝则在英国树立了榜样,他不但驯服了议会,还完全将教权踩在脚下,君主专制政体无情地摧毁了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接下来,人们还来不及为中世纪的封建立宪政体和自由城市制唱挽歌,就又眼睁睁地看着教会权力被吞食殆尽。在16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生活中,西方国家在君主专制权力的指引下,拓平了中世纪多元权力的重重障碍,迅速崛起,形成了一场“上帝自身在地上的行进”。[③]
西方世界的世俗化进程消解了传统的“国家—教会”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文艺复兴在文化领域打破了教会的垄断;宗教改革更是削弱了教会,加剧了传统二元结构的坍塌;尤其火上浇油的是,空前残烈的宗教战争更使得本已风雨飘摇的政教二元格局分崩离析。尽管宗教改革后的教皇专制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其衰落的总趋势是无可挽回的。美国政治思想史家乔治·萨拜因(G. H. Sabine)曾经颇有感慨地指出:“教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基督教思想前所未有的”。[14](p388)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王权得到不断的加强,世俗权力中能够制约和限制王权的力量均无可置疑地衰落了。封建贵族的力量要幺被削弱,要幺被贿赂而保持中立。例如,法国王室就通过免税而使王权的潜在敌手贵族和牧师保持中立;英王亨利七世则趁约克和兰开斯特两个家族在红白玫瑰战争期间大大削弱的时机加强了王权,都铎王朝甚至驯服了议会。
正如莱斯利·里普森(Leslie Lipson)所慨叹的那样,“车轮已经转了整整一圈,设定国家职能界限的最初试验以恢复到原有状态而告终。从希腊人无所不包的城邦理念到布丹(Jean Bodin)或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像一条不断丝线编织在几个世纪之中……”[15](p147)王权的扩张与绝对主义国家谱系的形成再现了一元论的强大力量,它不但葬送了中世纪长期以来广泛存在的二元权力体系,而且在传统二元社会的破产和现代二元社会的孕育之间撕开了一条无法逾越的裂缝。民族国家的革命性不是体现在它对传统的延续上,而是显露在它与传统的断裂上。当亨利八世宣布自己为教会的领袖时,他实际上统一了国家与教会两个领域,建立起一元主义秩序;法国的国王面对俯首贴耳的贵族和僧侣时,他对主权的坚定不移就是建立在绝对主义国家的基础上的。专制的逻辑不仅在于“朕即国家”,而且在于除朕之外,没有国家。当阿克顿说“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7](p316)时,他说出了事实。
然而,阿克顿说出的却不是真理。就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希腊的绝对主义国家经过古代罗马的转型,到中世纪时已经被封建体制和二元政治分散化到最高程度。在这一轮否定的基础上产生了新一轮的否定,民族国家的兴起否定了中世纪的二元社会,复兴了权力一元论的政治结构与主权观念;然而,这种一元论的复兴犹如昙花一现,到18、19世纪,二元论的活力再度得到激发,新一轮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即趋向完成,世俗权力体系的无限膨胀再度得到有效的遏制。然而,此二元非彼二元,“原来以教会与国家分立的基督教二元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二元主义,基于社会与国家分立的世俗二元主义,而重新出现”。[11](p54)以国家与社会分离为基础的世俗二元主义因此而得以建立,奠定了西方政治文明二元结构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打破了封建庄园和城市国家的封闭,而且在旧有地域上建构了市民社会的雏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庄园为了效率必须扩大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并且为了存在下去,国家必须得到远远多于它从传统的封建收入来源所能得到的财政岁入”。[](p23)民族国家出现并在同城市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封建的男爵、地方公国和小王国等种种封建力量基本上被合并为像英国、法国、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从而重构了近代欧洲的政治版图。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认为:“这一过程可能是货币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张的不可避免的结果”。[16](p102)
民族国家的兴起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保护市民社会在动乱、战争或是瘟疫中免受伤害正是民族国家的起因和目的。因此,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需要认真地面对不断成长的市民社会领域,甚至成为市民社会成长的推动力。例如,在法国,皇室需要分门别类地对每个地区征税,这不但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且亦需要得到志愿组织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行会的权力逐渐扩张,为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转变提供了基础。
独立的城市成为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专制权力的发展使一些城市丧失了独立,被融入国家,但是,它却在国家的范围内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国家绝对权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城市享有无与伦比的自由;它们自成天地,自由发展,其势力之大,竟能左右整个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大小城市星罗棋布,互通声气,以致于“城市得以执行自己的经济政策,经常能粉碎障碍,不断为自己取得新的特权,庇护或恢复旧的特权。设想今天的国家一旦取消,各大城市的商会能够自由行动,我们将会有好戏可看!”[17](p604-605)到16世纪时,城市的发展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不但举足轻重,而且出乎意料地突破政治空间的限制而获得更多的自治,变为“城市国家”。然而,这些“城市国家”亦不再是独立王国,它们被纳入国家的同时亦成为限制王权扩张的重要力量。对那些在城市范围内享有自治的“市民”来说,这种城市国家无异于“市民的小型祖国”,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明确地称之为“市民社会”。[17]( p609)
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极其复杂而缓慢,其中显性的因素常常是肤浅的,深刻的因素却又归入琐碎。从1450年到1650年的两个世纪之间,欧洲不但完成了大范围的探险、开发、贸易以及殖民活动,而且完成了政治—经济单位的结构转换。经过破坏性的战争、工资下降、普遍的社会动乱和宗教冲突,到该时期结束时,“一些政治经济单位的结构已根本上转化了”。[18](p165—166)
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它“不仅仅是19世纪德意志各邦国的特殊发展过程的反映,从英国样板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辨别出来”。[19](p11)各国在这一过程中又显露了各自的特性。仅就时间来看,早在17世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就已经在英国初具规模。然而,在有的地区,真正的国家与社会分离可能更晚一些,就哈贝马斯的估计来看,普鲁士直到18世纪结束时亦没有完全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19](p103)
不但如此,而且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亦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过程。早期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为西方政治文明提供了现代性的基础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然而,这一趋势在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逆转趋势”,即“国家和经济的相互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趋势真正消失了。”[19]( p12)但是,这并没有削弱这一观察的意义,事实上,正是在“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的循环往复带动了整个政治文明体系的自我更新。
注释:
[1][英]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2][加]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M]//邓正来、[英]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美]潘恩.潘恩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丛日云.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M],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1.
[6][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美]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9] 佟德志.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体系的影响[J].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1).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 [美]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2]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3] Jack Lively and Andrew Reeve, The Emergence of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The Artificial Political Order and Natural Social Orders, Robert Fine and Shirin Rai, Civil Society: Democratic Perspectives, London, Portland: Frank Cass & Co Ltd., 1997.
[14][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5][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6][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8] [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9]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