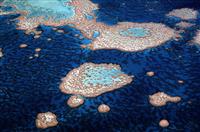激进的政治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对革命者来说,民主只是一个道具,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指示牌
一
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康梁流亡国外,谭嗣同殉难。由此,中国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丧失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只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官僚极度腐败、政体腐朽不堪、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使清政府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在清末十年宪政尝试中,已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个人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写入法典,清政权的统治到底还是败坏了平民百姓的胃口,何况是那些激情如火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回应是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最终酿成辛亥革命发生,二千余年帝制被掀翻,成立亚洲第一共和国。自由、民主、共和思想虽然缓慢却也极其坚定的传播。大小官僚把军人不能干政、法治和公理之类名词烂熟于心,尽管他们觉得这些词多少有些拗口。
当然,辛亥革命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战斗性的鲁迅通过不朽篇章《阿Q正传》对其做了盖棺定论:“革命党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来那个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对这次革命显然抱着不友好的印象,他把革命浓缩为一幅静物素描:静修庵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碎在地上,同时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前的一个宣德炉。
语言是种软性暴力,在表达我们思想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陷阱,在扼杀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历史,还是历史通过我们的咽喉在诉说自己。当我们以为只能全盘否定历史已然状态才能前进,从而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进行无情嘲讽时,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和短视。激进的政治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霍尔巴赫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鲁迅的描述无疑带有某种误导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无是处,技术性的事务缺了他们还真是不行,行政体系中留任原来的官僚也可保持稳定,避免激烈的动荡,更关键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习俗。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算是公共意识的最粗浅的表现。但是,历史在无际的时空中沿着多条通道徐徐前行,我们进入的历史是鲁迅用铁锤、匕首把革命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动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赢得台上台下阵阵喝彩尖叫声。
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不灭追求,富国强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岩左冲右突,寻求一个爆发点。这当口就容不得霍尔巴赫式细水长流的咏叹调了,他们更需要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进行曲,来一个淋漓尽致和践踏一切的喷涌渲泻。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法把这一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导,避免知识精英沿不同方向作无目标的布朗运动,力矩无限,然而合力为零;无法使之成为通向宪政之路的发动机。梁启超被喻为“变色龙”。再说说孙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环,杨小凯在《中国百年经济史》中说他是“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表现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是标准的以屁股指挥脑袋。连孙中山这样被推崇备至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亦不过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毫不为过,这次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严正质疑,他们用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和宪政共和思想启蒙国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过大地。只是北洋军阀专断无能、拥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则的腐烂让他们失去信任。随后,列强步步进逼、强国道路的受挫和日本进攻中国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急剧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知识分子中荡漾开来,如一些学者所说,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是政治运动否定了启蒙。整个民族在上民主、个人自由和共和思想这一课上课铃声刚响,却被匆忙解散。无法避免的为民族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阴影,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面目,为以后的灾难预先埋下了伏笔,以至我们现在还是吃这个亏,在补着这一课。
二
1949年,低吟浅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我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徐志摩们已被无情的旋风扫到角落里,随着无数热血青年抛尸荒沟、山岗和城市后,国民党中央军变成了蒋匪帮,共匪倒成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国人还在看着一支支部队从门前跑过,拉走他们的牲畜、能走得动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抢光他们的粮食和仅有的一点积蓄。窗内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窗外是冻白的夜和摄人心魂的枪炮声,他们在静夜中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与此同时,北方的中国人却在聆听从没有过的美妙音乐。北方的中国人在狂欢,中国人向来值得庆贺的东西非常少,这次是庆贺自己的新生。已逝去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横征暴敛加重了欢乐的份量,他们欢呼一个新国度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新中国,用太阳、不朽、神圣、万岁之类的词与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欢笑是可耻的。虽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现出些许的怀疑,曹禺在话剧《日出》诅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对邪恶伸出愤怒的中指。然而,对未来他显然也不是很乐观,他借剧中陈白露的口说:“太阳会升起来,但黑夜也会留在后面”。他说太阳并不属于我们。细究起来,他表达的却不是对新社会新生政权的怀疑,只是对未来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乱罢了。
既然有智慧的人们都已识趣的闭起了嘴巴,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推脱歌功颂德的责任呢?苏格拉底的存在对任何救世主都是不合适的,于是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在浩大诗篇中对革命的伟岸和领袖的阔大作了由衷的赞美。如果你对他说,几年后,他将作为深藏在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收押拘捕,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会以胜利者的自负不屑一顾。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解放战争的胜利,时间跨度上为一百余年,百年动荡、百年苍茫,在这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九死而无悔。求富求强的路上阅尽人世沧桑。天若有情天亦老!在他们品尝了最多的荣辱欢乐,体味了最深刻的伤痛折磨,经历了鲜血淋漓和死亡纷纷后,义无返顾走上反抗暴政的道路。现实的压抑和心中激情的碰撞、上层统治的腐败和无能、保守势力的强大,却使他们只能选择以暴抗暴的方式,统治集团对革命的残酷镇压和政权更迭游戏规则的缺失使暴力更以加速度的方式加以推演,暴力意识被无限扩散、复制、膨胀,直到形成本世纪最大的图腾:革命图腾。二十世纪历史单薄纸页被革命的烈焰烤焦。本世纪最大人数的死亡,最为惨重的破坏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革命的净化和理想的纯洁;大部分人死亡的理由不是法律的惩办,而是被革命的巨轮碾碎。
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旧有政权一无是处,必须把整幢大楼全部推倒重建。为了革命的胜利和纯洁,原有的统治阶层必须被处死或放逐,他们不配享有人民的称号,新社会的光泽是不会照射到他们身上的。与此相适应,革命者眼中时间不是线性不可复的,他们相信在时空的起点有那么个辉煌的开端,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时候,它是完美无缺的,只是因为人类道德败坏,它在渐渐在变质腐化;或者相信有那么个终点,旧有的丑陋东西总是无可避免,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涤荡一切虚伪、邪恶和腐朽以达到光明的顶峰。与我们相比,西方哲人眼中的时间是线性的,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他的意思是: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旧的恶去了,新的恶也来了,河里的水变了,但只不过是换了些水,水里多了些少了些垃圾都无助于改变它作为一条流水的河的定义。我们时间是圆环状的,可以循环轮回。旧的扫荡光了,美丽新世界才可以破土动工。新建的开始就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其实,当伟人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一个诗人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许多人正跪倒,许多人尽管肉体依然强健,然而精神也已跪倒。
三
1969年4月1日,此时距开国已正好二十年。二十年时间在史册上只是可有可无的几页,对微不足道的个人来说,二十年里却是沧海桑田。胜利的激情已退却,新世界的阴暗面已显示无疑,民主缺失那个暗淡的光点已如洪水泛滥一样不可收拾。革命运动已一波三折,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已被消灭,我们据说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虽然有55万右派作为异已力量被揪出,但并不妨碍我们其它方面的进步,原子弹已经爆炸,卫星已经上天。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家属、好友的人悲痛已化为细微尘埃,人的记忆毕竟有限。但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还没有结束,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宣言依旧激动人心。这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老舍跳了太平湖,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的彭德怀元帅已被打入冷宫,经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重新定义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叛徒、内奸和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此时,全国数千万红卫兵、红小兵怀着比辛亥革命时狂热百倍的激情把一切封资修的东西捣毁,有些已冲出国界,去营救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群众。
如果我们再把眼界放大一点,我们会看到退守到台湾岛的国民党的残军败将忙完了打土壕、分田地,和新加坡等地一道实现了经济上腾飞,号称“亚洲四小龙”。日本从战败恶梦中苏醒过来,经济飞速发展,美国此时已造出第一台电脑,这些在当时毫不起眼的黑旧铁件、电子管、电极等正酝酿着世界上最伟大技术革命的到来,最终使黑格尔坚信的理性世界变成网络世界。
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着,当然我们也没闲着。在此以前,在全国除台湾(这是个叛逆的省份)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报纸上都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社论以及革命实现了“新突破、新进展”的喜报。我们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这时中共九大姗姗来迟。八大新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五年召开一次。八大在1956年召开,到1969年已整整十三年过去了。这样做的理由不是因为战争或者自然灾难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根据江青的讲法是:会议的召开应该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已经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一长串人,如果九大在文革以前开的话,这些人都将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某些人还将进入核心领导机构。
江青说得够爽快的,她抹去一切道貌岸然“阳”的修饰物,毫不讳言革命最终也是涉及权的需要,也要有动物人“阴”的私欲。当其他人唱着道德的高调,江青出格的言语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千万不可忘记,女人是编故事的行家里手,曾有人笑谈如果女人有权对自己编的故事抽税的话,每个女人都会成为百万富婆。何况,伟人已逝,死无对质。有种理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任何世代,对草根阶层来说,历史只是天上卷舒自如的暧昧云彩,我们看上去只是一团迷雾。可有人揭杆而起,用剑指着云彩说你们看,那是头狮子!我们一看,剑上还残存着热气腾腾的血滴哪。对,我们说,那不就是狮子吗?如果后来人有更粗壮的手臂和臀的人提出疑问说那哪里是狮子,分明只是小猫而已嘛,你们怎么一点眼光都没有。我们一看,果然那些云彩就是小猫而已。
中共九大代表的选取是很有特色的,出席九大的代表没有经过选举,而是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下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让我们看看当事人眼里的九大开幕式是怎样的激动人心。迟泽厚在《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回忆了那个激情似火的岁月:1969年4月1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同意不同意,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选举会议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毛泽东面带微笑说:什么人合适啊?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器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手臂,林彪高喊:通过。
温情脉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方式杜绝了机械而无人情味的民主程序,从而也就根除了民主程序安排的可能,这也许是战争时期的恶劣环境的反弹和对同志之情的弥足珍贵的自然应对。然而政治不能指望人的善,革命者亦是有欲望的人,有根深蒂固人所共有的恶。革命战争时期,“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哪”心理形成根据地的聚光灯效应,它和理想主义一道形成的道德约束使恶隐得很深。和平时期来了,就要建立一套完整有力的制度来约束权力,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然而历史的阴差阳错总是让人感叹万千,对帝国入侵的憎恨让人们对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恨之入骨,我们选择了抵制和排斥,不惜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这样,就形成了把情境逻辑中的具体应对超拔为抽象的原则,反过来指导后来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境的情况。然而当革命道德理想失去旧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时,无法挽回走向灾难。
四
有必要回顾一下民主的发展历程。如果以乐观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历史流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历史是宽容和自由渐次战胜暴政和专制的过程,对民主的追求更是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之中。民主的本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直接掌控国家的权力。第二是按照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开选择来做政治决定。不过,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在人类初级阶段,比如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称号,他们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者至少是接近于最糟糕的政体。理由简单而明了: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而穷人总是不可信的。问题还在于多数人并不总是对的,对多数人的崇拜会顺理成章演变为“少数人总是有罪”,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的浪漫主义尝试是个极好例证。基于此,就有了托克维尔的“多数暴虐”,以前我们知道有独夫暴政,不想多数暴虐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福楼拜说得直截了当:今后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现在人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法国大革命的惨烈经历,使有产者对大众民主闻风丧胆,群氓以民主的名义进行财产掠夺、暴民政治,让人们初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然而正如穆勒所说: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历代先贤对民主制度进行更完美的设计的安排,发展出议会民主、自由民主、宪政民主等一系列概念来抵制民主与身即来的浓浓血腥味。尤其是宪政更是从根本上控制国家的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概念,根据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发展出了现代市民社会模式,他们否认契约的一维性,坚信契约论的两元性质,即民众让渡的权力只是部分权力,不是全部。交出去的权力组成国家机器,为了秩序和种族的延续作为妥协,国家可以收税,维持治安、抵御外敌,那些留下来的权力组成社会自治。交出去的小,留下来的大,交出去的是为保护留下来的,以此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对国家如此不放心是因为国家起源于一种必要的祸害。波普尔说:国家是种必要的痛苦,它的权力不应增多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因此,国家不能给予道德化的要求,我们不能指望国家能带我们到天国去,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恶的产物,国家的道德,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一般被认为是低于一般人的道德。
五四运动启蒙的大旗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虽然一度误入迷途,当他晚年以一个罪人之身隐居于江津小城,却对政治进行了通达的考虑,以民主有着精确到位的理解。他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的某些政治现实作了尖锐的抨击,最终归结为对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实际上,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得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标准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只是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才出现斯达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克洛勃)政权制,……而这种局面的出形成,并非是由于史达林心术特别坏,而无不是凭借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秘密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我们若不是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来反对史达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达林倒了,会有无数史达林在俄国及另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达林,不是有了史达林产生了独裁制。”
此后,毛泽东作为当时最大的反对党的领袖衡估着民主的作用。在《历史的先声》一书中,毛几乎都在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诸如此类的话。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新近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回忆》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篇章论述民主的重要性,随便拉出一些题目来看看:《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论英美的民主精神》;《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进行民选吗》;《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等等。单看这些社论题目,我们能想到,对于一个即将瓦解的专制政权来说,它们是如何的心惊肉跳;对那些正浴血奋战的群众来说,它们是如何的鼓舞士气。也能想象这些篇章对内战力量参差消长起了多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积淀的不足,对满怀激情,要把这小小寰球修改成人间乐园的革命者来说,民主只是一个道具,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指示牌。一个与此近乎相同的例子是清末洋务派对科学的追求。那时人们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追求科学是为造铁轮、枪炮和电报电线,他们理解不了科学的真谛,不知道真正追求科学的人压根儿就想不到那些东西,对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只因为宇宙太浩大神秘,他充满探索欲望,这就如同爱因斯旦不屑于走上街头去看因他的理论才得以实现的核能电站。他只是看到宇宙的井然有序,有种无法描述庄严的美,是那样激动人心,以至于他在未知面前喘不过气来。
五
还应说说当时的另一件趣事,广东省博罗县是全省最有名的学“毛著”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九大的小组会上介绍了他们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叫刘少奇,“文革”前,他们把这个地主的名字当成一条罪状,狠狠的批斗:你胆大包天,凭什么和我们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得他改了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成了“五毒俱全”的最大走资派,地主刘少奇也跟着沾边,大队党支部又把他拉出来批斗:你就是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据说经此一翻批斗,社员们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用荒诞时刻的荒诞行为是不足以解释这种事件的,地主刘少奇的经历是一段浓缩历史,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名字会让他如此狼狈,以至于连命都可能不保,他的爷爷或者父亲几十年前随意挥就给他带来的灾难也是始料不及的。地主刘少奇不知是否能挺过浩劫,如果他新时期还活着,如果法律允许,如果他具备足够商业头脑,把他的名字溶入商业的洪流,也许他现在已是亿万富翁,出入香车宝马,坐拥美女别墅。可以挥金如土,可以穷奢极欲。享受富人东山再起的荣誉,接受穷人暗淡低调的献媚。对以往受到屈辱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不再怕红色恐怖铡刀的血红阴影。不过,这样见证着历史的轮回反复和人世的兴衰悲喜,他是否会产生庄周梦蝶或者是蝶梦庄周这样的幻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