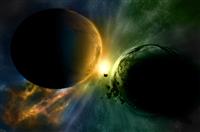“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连起来才成……”
这是一段曾经令无数中国人难以忘怀的文字。在今年的4月2日,写下这段话的那个住在遥远北国的故人——安徒生,就满200岁了。
曾几何时,这位丹麦童话大师在中国赢得无比的荣耀:在上个世纪的1913年,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第一次被周作人介绍给中国读者;1924年,第一部中文版的《安徒生童话集》由新文化书社出版;在1925年,文学权威刊物《小说月报》以整整两期的篇幅刊载“安徒生号”,全面而隆重地介绍这位世界童话大师——这种堪称豪华的高规格待遇,连同此后在中国人心灵里累积了一个世纪的诚心崇拜,换了今天,恐怕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不一定能有福得享。
然而,当包括中国在内的135个国家都在纪念安徒生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却有中国人不断反思,假如安徒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他的童话一定不好卖。
现实确实没法令人乐观。可以想象,这个叫安徒生的人,站在今日中国任何一家大型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就得打退堂鼓:他的书里没有“办公室政治”,没有“血酬定律”,没有“身体写作”,没有“××黑幕大揭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他本人长相丑陋,没法包装成“美男作家”,自然也没有绯闻艳遇隐私可炒作,年龄又偏大,没法归于“文学新生代”;就单说最有潜力开拓的少儿读物市场吧,现在的婴幼儿忙着“补锌”、“补钙”、忙着从3岁开始学英语;现在的小孩从小学就开始看《我不是教你诈》,超前领会人情世故,学会在同学中拉选票竞选班干部;现在的中学生在父母的授意下,利用课余时间恶补奥数和小提琴,模仿《××女生》里面传授的经验:冬天手握冰块练习意志力。有日本动漫和网络游戏,谁还有空看一个老人絮絮叨叨讲为了真爱牺牲自己……要是跟来自欧洲的“近亲”《哈利·波特》相比,安徒生非得自叹弗如:他书中那丁点少得可怜、单薄的魔法,哪有拍成“全是高科技”电影的资本?!
一言以蔽之,安徒生在今天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走投无路、抑郁终老、没有前途的作家。他太简单,不懂得“炫技”,玩文字游戏,把读者弄得晕晕乎乎;他太单纯,以至于很有可能被人视为“矫情”、“装嫩”;他太厚道,没有任何“卖点”,没法刺激读者日益挑剔的视神经;他的作品太超脱,不写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没法成为“厚黑学”式的指导丛书,为国人火烧眉毛的生存困境、婚外恋情、人际斗争指点迷津……
安徒生是幸运的,他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刻,读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头脑复杂、口味怪异,读书的目的也没有现在这样功利。那个时候,人们只是凭着直觉认为好的童话,就应该像安徒生笔下的海,果冻一般的深蓝,安详、宁静、优雅,有一点点忧伤,也不乏欢乐的波澜。父母们会觉得,孩子沉浸在它的拥抱中,一定是幸福的,陶醉在它的爱抚中,一定是自由的。在孩子临睡前读上一小段,他在梦的深处,就会踏入一个不可思议的王国。在生日为他读上一段,他会从中学会感恩、宽容、善良、谦虚等等美德。
安徒生是幸运的。隔着200年时空的距离,我们会怀念他,怀念书中一连串灵光乍现的比喻,无数人会赞颂“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已经接近语言之美的极致。无数的评论家会撇开技巧,极力赞颂他的文字中蕴含着的那种无欲无求的天真,在今天,在中国,如此难得。人们会原谅那个已经200岁的老人,他曾经固执地认为,在大海的下方有湮没在沙砾中的古城,以及不知何故戛然而止的未知文明,还有沉没了数个世纪的船只、宝藏和宫殿。
博尔赫斯说过,具有不朽禀赋的作品“可以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译本之参差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的考验,它永远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安徒生做到了。隔着200年的时空距离,人们心甘情愿地选用另外一套尺度标准衡量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不愿在作出评论时吝啬任何赞美的字眼:安徒生的作品是伟大的,深刻的。它发自内心深处,把握世界上一切美好高尚事物的精髓;它是内省的,尤其是对于善于模糊言辞、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而言,它直视人灵魂深处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它是勇敢而敏锐的,它将日常生活中被屏蔽的精神盲点挖掘出来,摊开在阳光下、书桌前;它是超世俗的,不因实用主义的世俗价值观所左右,从而构建起一个富有宏大维度的理想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