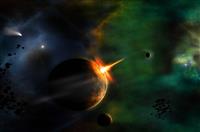一
传统相声中有个学老北京“市声”(北京话就是做小买卖的“吆喝”)的段子。甲乙双方互相比试。甲说上半句,令乙接下半句,并猜出是卖什么的。
甲做小贩状,吆喝道:“江米小枣的——”
乙接道:“粽子,这是卖粽子的!”
甲接着吆喝:“切糕。这是卖切糕的!”指出乙接的下半句和猜的都错了。
甲又吆喝:“修理——”
乙接:“雨伞。这是修理雨伞的!”
甲接:“桌椅板凳。这是修理木器家具的。”
于是,乙急了:“你老是一个马,两个脑袋,叫我怎么猜?”
这个小段子中可知甲利用答案的不确定性,使乙犯错误,回答不正确。
甲说:“俩脑袋还算容易的。我要说‘一毛一堆’。你更猜不着是卖什么的了。”
这是在智力游戏中运用答案不确定性,使甲轻易占了上风。世间有许多行当、也有许多人爱用不确定性,为自己赢得利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从事迷信活动的行当,如算命相面,巫婆神汉等等。
人们算命问卜,求仙供神目的就是求得预知,实际上人间确切的预知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的,那些以预知他人命运为生的职业迷信者,更不会有求得确切预知的能力,可是他们又要表现出自己的预知能力,因此就尽量用“一个马两个头”或“一个马多头”答案对付求卜者。算命行当内部流传的秘诀《方观成之互关》中特别告诫吃此行饭的人们说,对于求卜者“若紧处何劳几句,急忙中不可乱言。只宜活里活,切忌死中死。”什么问题都要用活话对付,给自己留下广阔的余地,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里“不确定性”是他们的法宝。
传统相声揭发算命者“算”你家里兄弟几人,可以说是运用“不确定性”取胜的经典。卜者不明确向求卜者说,他算定对方家中有几口人,而是用“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来比喻。
乙:“我是独生子。”
甲:“这很对。桃园三结义,你命中注定是三兄弟,可是你命硬。只孤独出你一枝来。”
乙:“我兄弟二人。”
甲:“这很对。你本应兄弟三人,咕嘟(北京土话,指刚刚出芽)出一枝,还剩两人。”
乙:“我哥仨。”
甲:“这很对。你兄弟三人,桃园三结义嘛,都在一枝上。”
乙:“我兄弟四人。”
甲:“这很对。桃园三结义,哥仨,再咕嘟出一枝儿,不是哥儿四个吗?”
乙:“我哥儿五个呢?”
甲:“你哥儿一百个也没关系。除了桃园三结义哪三位以外,你九十七个哥儿们都在那一枝上咕嘟呗!”
这就是利用形象的多义性,可以做出多种含义的回答。关键看你是不是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当然这是极通俗用多义性对付求卜者的。当然,传统占卜术、预言术中有比这高级多的。但不管怎么高级也离不开不确定性这一点。
古代占卜术注重形象性,因为形象是多义的,甚至是有无数解的。这就给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开拓了无限的空间。《周易》中不仅八卦、六十四卦都用自然现象或自然和社会中的种种具体事物作为象征,就是其卦辞、爻辞也多用有具体形象的事物象征。如爻辞为“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树荫里有鹤和鸣;我有好酒,请您来喝一杯)。这是一组形象,能够包容大量的答案。
唐代大预言家李淳风非常有名,据说是他写作的预言图书《推背图》是用诗和图画来表现的。这是用双重形象来扩大答案的多义性。《红楼梦》第五回里太虚幻境薄命司里的“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图册就是借鉴了《推背图》的写法。许多红学家对《红楼梦》80回以后情节推测的分歧,许多来自对这命运图册的解释。它的不确定性,给了红学家们特别宽阔的想象余地,有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外交家也偏爱不确定性。有个笑话说,有人问外交家某件事行不行,当外交家说“行”的时候,那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当他说“考虑考虑,研究研究”,那就是“不行”。如果说“不行”呢?那他就不是外交家(淑女与外交家正相反)。当然,守此道不知变通也有误事的时候,小布什那样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攻打伊拉克,萨达姆就是不信,以为是外交家的语言,也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据说是受了希拉克坚定反战的误导),结果是国破家亡,身为天下笑。
二
居上位的统治者大多偏爱不确定性,因为居上位者天然地具备了一种“势能”,居高临下,有许多便宜之处。这种势能的优越如何能发挥出来呢?关键在于没有确定的社会规范。有了确定的规范,社会上下全都照此行事,首先束缚了在上位人们的手脚,使其优势不能充分表现和发挥。
春秋时期,鲁昭公六年,郑国把刑法铸在鼎上,使众人皆知,以便遵守。虽然这种“法”只是要人们遵守的条令,远不是界定人们权利的现代法律,但公开了,也比藏之秘府好。可是这招致保守派的反对(也包括孔子)。孔子说“刑之轻重,不可使人知也”。唐代孔颖达在疏解为什么刑法条文“不该使人知”时说“贵之所以为贵,只为权势在焉”。也就是说在上位者之所以为“贵”就在于他有权势,而“权势”说具体点就是居上位者有对人和物处理的权力。他们管理着社会上的芸芸众生,刑法就是其管理工具之一。如果这个“刑法”是秘密的、不确定的,对于在上位的管理者就方便得多;在下位者也因为不知道刑法的深浅,不知道偶有过犯,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所以“常畏威而惧罪也”。也就是说,刑法保持不确定性,老百姓才能常常处在恐惧状态,才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以求得自保。而且,黑箱操作本身的神秘性就会使芸芸众生敬畏。
当时的保守派认为上古“圣王制法,举其大纲”,不把刑法订得那么细密,人们犯了法,再由执法者依据“大纲”“临其时事,议其重轻”。这样便赋予了执法者极大的权力。现在刑法条文都铸在鼎上,人人得见。“贵者断狱,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验于书,更复何以尊贵。威权在鼎,民不忌上,贵复何业之守?”人人都知道了法律条文,上下都照此行事,贵人们不敢增加,在下位者又可以根据公开的条文说三道四,那么在上位者的优越性又到哪里去了呢?因此保守派坚决反对法律条文的公开化。
当然,反对者所持的理由并非只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它使“贵者不得为贵”,要是只有这个理由,似乎只为“贵”者考虑,而儒家历来是以全社会和全体人民代表自居的,以社会公正的体现者自居的。因此,他们还提出刑法不公开、不确定是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因为犯罪是千奇百怪的,有的人犯的“罪”虽轻,但其动机是“大恶”,不可原谅;有的人犯的“罪”虽重,但究其原因,却是情有可原。如果法律只以“大纲”形态存在,这就给了执法者以充分的余地,让这些执法的圣人们宽大那些虽犯重罪、但其心尚不甚恶、因而可以原谅的人们;从严惩处那些虽犯轻罪,但却是不可宽恕的人们。这样才能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这种说法把执法的在上位者都想象为“圣人”,几乎把他们看作是上帝,能对人间的一切作最公正的判决。既不漏过大恶,也不会冤枉良善。法不确定,才能够使他们的“公正”充分发挥。使恶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能保护善良。这种说法是颇能欺骗人的,我们传统政治学中往往是把统治者预设为“尧舜”的,特别是当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是尧舜。怎么能用缜密的律条束缚尧舜的手脚呢?我以为别说他们不是“尧舜”,就说是“尧舜”,长期掌握极大的权力,没有监督,没有对立权力对他的限制,久而久之,他也会成为暴君。
不确定性作为传统管理的思维模式一直波及至今。在方法论上,我们长期以来特别钟情“辩证法”,实际上就是在实际权力之外,又授予居上位者一种话语权力。辩证法是认识动态世界很好的一种方式,但因为它是阐释“动态”事物的,往往是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运动状态会产生多种结果。在上位者具有话语权力,这样他们便通过这个权力、利用事物辩证关系的不确定性,使有利的结果永远向自己倾斜。这是许多从荒谬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深有体会的。
在治理国家方面,长期没有公开颁布能够细致界定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是“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治天下”。当时只有这两部法律是公开的。文革当中《宪法》被撕毁,只剩下一部《婚姻法》。在管理人和管理物时只是靠政策,而政策又不公开,当时由于各种运动面临着各种处理的人们非常多,他们整日凄凄惶惶,不知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那时谈到中国广大的人群,不用法律意义清晰的“公民”,而用含糊至极的“人民”与“敌人”(连国家主席都会失去“人民”称呼,而变为敌人)。一切都是黑箱操作,没有权力的只是等待宰割罢了。
领导人发布的指示也尽量把话说得极不确定,例如,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最高指示有言“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都要给以出路”。这段话非常有趣,它既给了被清理人员以光明前景,又把执行的权力完全给了有权处理人的人们。其奥秘就在于不确定性。不“给出路”是什么人呢?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与犯一般错误的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分子。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很宽松的(就当时的环境说),被处理的人大多会作第一种想法,于是他就会有光明感;可是它也使得被定入有“敌我矛盾”劣迹的人们不能拿着我不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挡箭牌去要求“给出路”。
当然执行者在落实政策时还有一套“实施细则”,其中关键在于打击面定是多少,至于谁给出路,谁不给出路,由于最高指示的不确定性,那就完全看执行者了,有很大的偶然性,也就说看你的“命”(无可奈何谓之“命”)。如果执行者秉性仁厚(当时这是被视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就给了出路;如果是执行者阶级斗争觉悟高,被清理者便活该倒霉。我认识北师大一个朋友,他是十六岁考上北师大数学系,为人极倔犟,十八岁便被划为右派,63年又被划为反动学生。1969年返校,系军宣队长(当时学校被军队和工人管理)对他不错。有次在校园碰见该同学,队长主动跟他打招呼:“去哪里了?”这位以为军宣队在监视他,便气呼呼地回答说:“去莫斯科了!”那时“苏修”简直是罪恶的渊薮,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而他竟敢如此回答,真是找死。就凭这句话,军宣队长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何况他是内蒙人,内蒙大抓“内人党”,把大批的党政干部打成“苏修特务”!队长没理他,后来私下对他说:“人们见了面总要打个招呼,我毫无恶意,你赌什么气呢?”后来还是给他分配了工作,回到内蒙教书。而人民大学的一些“四清”时被清理出的同学,在1969年落实政策时不给出路,都遣返回乡,与“四类”分子一起监督劳动,直到文革后才解决问题。这种或吉或凶的反差极大的结局,便使得被处理者时时处在恐惧之中。
史前的氏族公社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不仅熟悉,而且大多有血缘关系。此时人们的行为规范,大多是受到习惯法和本群体舆论的约束(周礼中就包含一些氏族公社的习惯法),这种约束反映了人之常情,并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孔子对“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向往,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今天的人们也完全可以想象。一家子里,家长的表率作用、七大姑、八大姨的口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血缘联系中的温情都是维持这个家庭的纽带,兄弟姊妹、父子叔侄之间,不可能完全按照明晰确定的“家庭公约”行事。这就是人们经常乐道的“人情”。可是当国家出现以后(尽管这个国家带着很浓重的家庭色彩),随着所管辖范围的增大,人口增多和人的流动性加大,人与人之间不仅不了解,
十分陌生,而且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处在管理地位、或说统治地位的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天然地与在下位者处在利益的对立面,他们更是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些人感到用那种不确定性的方式统治,一方面符合传统和习惯,另一方面也更能照顾到自己的利益。他们有时也用“家庭温情”一套“劝导”被统治者牺牲“小我”的利益、以服从大家庭的利益,这就不免有些虚伪,因为所谓“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这些大家长的利益,如同一二十年前,苏联强调其卫星国应该保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苏联的利益一样。此时社会管理者如果关注自己的长远利益,就应该平衡各个利益群体不同的要求,并驾轶明确的规范。
古代中国的社会基层往往是按照宗法网络组织起来的,周代数百年统治中,君主与宗子一体。最高统治者与大家长就是一人。秦代以后,虽然家国一体性分离,统治者不再是大家长了,可是由于“家”“国”的同构性,“国”与“家”的关系两千年来就没有扯清楚过。皇帝还常以“大家长”自居。常常把被压迫的“臣民”说成是“子民”,“臣民”由于“隔膜”有的还真的把皇帝看作自己的“老子”,使残酷的统治和压迫总带有一点“脉脉温情”的色彩。因此那种不确定性的统治方式,不仅在统治者那里有市场,就是在被统治者看来也不觉得它悖于人情。这种社会规范的不确定性被改头换面,长期流行,不仅说明统治技巧的既能一以贯之,又有花样翻新;也表明当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没有消失时候,它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如果那些具有确定性的法律又是秦法那样明确而细密的恶法(参见“睡虎地秦简”),人们更会觉得那些虽不确定但却带点人情味规范更好一些。
现在中国社会处在向工商社会、市场社会的转型期间,与之相适应的是建立法治社会、公民社会。人与人应该建立平等的契约关系,每个人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契约一定要明确,不能搞什么模糊性、不确定性。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群体与个人之间也是这样。现在许多“合同”由于权利义务订得不明确而对簿公堂。有的法学家说国人契约意识与法治国家人们还有很大距离,契约的制定的细密性和明确性与契约双方对利益要求和关注也不匹配。特别涉及掌握着公共事务权力的人们依照明确的法律行政,使各种具有确定性的社会规范逐步建立起来,平民百姓,有所适从,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