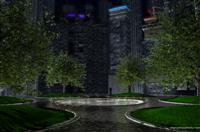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大钊、李达和毛泽东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译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 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 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 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 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入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
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 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 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 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入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