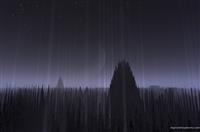如果我不能写得太快,那么就要写得慢一些、更慢一些,记下“毒奶粉”事件以来自己的感受。这场导致一万几千名婴儿住院、几倍于这个数字的孩子受影响,这件事情真是糟糕透顶。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还能够说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等待人们去说么?环顾四周,发现许多朋友与我一样,再次陷入极度失语当中,忍受因为无语和发不出声来的折磨。
是因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还是因为该说的,早已经说过了?抑或是面对这样残酷粗砺的现实,我们的语言已经完全失效,它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现实?找不出任何一种话语能都与这样的现实相匹配?
某种折磨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失语与发声的挣扎和挣脱中,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而仍然找不出言词,找不出任何可以采取的方式。然而在这样的沉默中,我们会不会由此而变得麻木,变得熟视无睹,变得见怪不怪?这是有可能的。而这种时刻,也正是我们的死亡之日,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死亡。
类似的死亡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已经经历过多次。下面是我亲耳听来的事情,当时我除了感叹之外,并无其它反应。这几天每每想到此事,会觉得自己参与隐瞒了一件可怕之事。
大约是2005年春节,我见到了乡下的表姐。她告诉我她们那个地方当年秋收的稻谷不能吃,因为用了一种剧毒的农药,有人将这种稻谷的皮糠弄下来给猪吃,结果猪吃死了。种田人对这种事情的处理办法是——将这批稻谷全都“卖去了上海”,当地人再买别的稻谷回来吃。
表姐是一位养猪能手,她没有说起自己家的猪栏里发生类似的事情;她也识字不多,见识有限,我不知道她说的“上海”是否确切。但是有一件事情肯定是确切的,那就是她们买来外地的稻谷自己吃,将认为有毒的大米悄悄卖到了别的地方。并且这件事情在当地完全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众人皆知的。
这种事情我听了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去向什么部门反映、向什么人汇报?我不能想象,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有某一张办公桌的后面坐着这样一位官员,他能够耐心地听我将事情说到底,而不觉得我是神经病?!或者我能够受得了他那种傲慢、轻蔑的眼光,在他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为什么要自讨那个其辱?“这种事情,多了去了”,我是这么给自己找台阶的。
哀哉,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便深知自己的努力没有意义。我的心里是不是居住着一个老牌靡菲斯特,那个只会嘲笑的魔鬼,对我们任何的行动报以冷笑?它的使命就是使得我们丧失任何对于事情的新鲜反应,将我们的热情浇灭,令我们行动意志瘫痪?在这个意义上我与那位没有谋面的官员是一致的,我们都被一种符咒控制住了,感觉不得动弹。就像接受了一种药物,尽管口、鼻、眼还是接受外部信息,但是从手臂到心灵,已经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应对,如同得了麻痹症一般。
而我为什么又要知晓这些事情?是什么人偏偏将这种事情放到我的面前来?让我忍受如此晦涩、无力和困顿?在这个意义上,我痛恨听到这类丧失或灭绝人性的消息︰每听见一次,就意味着我的人性又一次沦陷,我的心灵里又造成一个大窟窿,我的头脑内又留下一个深坑。我们不得不与这种东西同处一室,不想忍受也必须忍受,不能忍受也必须忍受。百般无奈之中,最好是退居一角,仿佛冻僵和冻伤一般。
从前也有朋友将这样那样的消息发给我,关于一位乙肝患者不能入学,她才有十五岁;关于一块被强占的土地,面积不大但是使得一家几口人流离失所;关于一位在狱中的朋友,他与怀孕的妻子来我家时,给我们带来了离奇的影像。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然而,我的人性被冻伤了!这是无法测量的!日日陷入这种无用、无效和无能为力,陷入这种无语和沉默,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变成了一堆狗屎,或者当了只会干活、不会说话的奴隶。我与周围人欢笑、插科打诨,但是,就是不说出心头那件最大的困惑,那些难言之隐。
说,还是不说,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判断的问题。
而我们丧失最为严重的,则是一种起码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