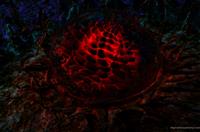在一次有关神学与道德的会议上,有基督徒说道德的基础是上帝,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无所不知的全能上帝赏善罚恶,丝毫不爽,上帝的正义是人间道德的保证。但有人问:“如果没有上帝,基督徒是否也行善?”基督徒答曰:“这个‘如果’并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的确,对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上帝的存在不是或然而是本然的,因此,基督徒行善也是必然的。不过,在非基督徒看来,上帝存在的保证是人的信仰,而人的信仰在根本上是或然的,比如,妥斯陀耶夫斯基笔下那个摇晃在信与不信之间的人,这个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恰恰是隐含在基督教道德内的逻辑。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上帝存在与否的实质性道德意义是:善是否有善报,恶是否有恶罚?上帝不存在的虚拟问的是:如果善无善报,恶无恶罚,基督徒也行善拒恶吗?
不管基督徒怎样回答,这个问题都是尖锐而引人深思的,因为它揭示了两种最为基本的德行:有限德行(有上帝才行善)和无限德行(无上帝也行善)。
有限德行和无限德行的人性根源是有限与自由。人的有限性展示为:人是有死的,他时刻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中,他有抗拒死亡的本能;人有肉体,他有满足生理需求以维持生命机体的本能;人是脆弱的个体,他有依赖求助于他人、社会、工具、神灵等等的本能;人有理性,他有寻找行为理由的本能。与之相应,人的自由性展示为:人可以自由选择放弃上述一切本能,比如选择死亡,选择饥饿,选择孤独无援,选择悖谬。
人性的双重性内在地规定着德行的基本可能。
1.德行的自我限度与超越
自我既是德行的基础又是其首要限度。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我想先区分德行主体和自我并重新审理道德关系结构
以“张三舍己救人”为例。在这个例子中,“张三”是德行主体,“己”是自我,“人”是别人。从事实上看,张三和自己是同一个人,但在道德行为结构中却是两者,因为上述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乃在于张三舍弃了“自我”拯救了“别人”,在此,自我与别人都是张三这一德行主体行为施与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一行为包含了双重关系,即张三与自己、张三与别人的关系。俗常道德观总是将德行主体与自我混淆在一起,看不到两者的差异和两者之间的道德关系,从而将德行主体与他人的关系设定为唯一的道德关系,忽略了德行主体对自我的道德责任。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有所谓“发现自我”和“自我觉醒”之一说。有人叹曰:多少年来我们只知道对别人、对集体、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党负责,惟独不知道对自己负责;我们关心别人、关心集体、关心民族、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党,惟独不知道关心自己。在我们的道德世界里,“自我”从来就只是一个被否定、被抛弃、被遗忘的存在,德行主体与自我的关系只是一种消极的否定性关系。80年代初的“发现自我”和“自我觉醒”暗含了对德行主体与自我关系的新体认,即意识到德行主体对自我负有道德责任。可惜的是,因为多种原因,这一意识并未真正成为伦理学批判的现实思想资源,以使迄今为止的伦理学仍然是遗忘自我的伦理学。
由于遗忘和忽略自我,自我存在的权利与德行限度的问题便一直未得到真正的关注和适当的理解。比如说,一旦我们意识到德行主体对自我负有关怀、保护的责任,或者说德行主体有关怀、保护自我的权利,“舍己救人”作为一种绝对命令的正当性就是可疑的。从客观上看,他人生命和德行主体自己的生命在价值上并无高低之别,对他人的道德责任与对自我的道德责任也没有等级之分,因此,谁也没有理由和权利要求德行主体为救助别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此意义上,为保护自己而拒绝救人是无可非议的。
德行的切己性总是将如何对待自我的问题带到德行之中,这是一个复杂而尤须深思的问题。从以上这个极端的例子也可发现,在德行与自我的关系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其一是有条件的德行,即于己无害是行善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德行主体便放弃行善;其二是无条件的行善,即不管是否于己有害都行善。无疑,前者是最一般的日常德行,它的主要特征是自我保护优先的原则;后者则是罕见的超常德行,它的突出标志是无条件地行善。
传统伦理学大都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甚至认为前者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德行,因为德行是不能有条件的,以自我保护为条件也不行。传统伦理学的这一看法显然无视了人的有限性和自我存在的权利,从而对德行的日常样式及其正当性不屑一顾。要纠正传统伦理学的这一弊端,不能简单地颠倒它对前者后者的态度,而要小心区分保护自我的有限德行和超越自我的无限德行,更为人道地理解和看待德行的现实,杜绝道德理想的专制。
须留意的是:对保护自我的有限德行要给予更多的人道理解,但不能以之为自我沉沦的借口;对超越自我的无限德行要给予更高的敬意,但又不能以之为普遍的道德命令。你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反抗纳粹的暴政,但你不可以要求别人也这样,因为你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放弃生命,以道德的名义也不行。因此,在纳粹枪口下沉默而不反抗的大多数自有其沉默而不反抗的权利,这是有限而脆弱的生命的悲哀和无奈,对此,除了理解你能说什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纳粹的枪口下沉默而不反抗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它默认了邪恶,如果所有的人都只沉默而不反抗,纳粹的灭亡就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以生命为代价反抗纳粹的人是英雄,他让保护自我的沉默者愧疚。
2、德行的现世-来世限度与超越
德行的内在自我限度也可以转换成德行的外在现世-来世条件问题。在一个缺乏现世-来世正义的社会,日常德行是困难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德行自我处于危险的无庇护状态:一个人守信于人,人可能失信于他;一个人真诚待人,人可能蒙骗于他;一个人扶危济困,人可能恩将仇报。在一个确有现实正义的社会,失信者、蒙骗者和恩将仇报者将受到惩罚,而在一个没有现实正义的社会情况可能刚好相反。
于是,在特定社会中的德行主体总有一个如何面对社会正义的问题。是天下有道才行善,还是无论天下是否有道都行善?或者说是在乎行善的社会条件呢还是不在乎?对前者的肯定答复即有限德行,对后者的肯定答复即无限德行。
有限德行的主体总希望恶有恶罚善有善报,至少善不要有恶报。无论是高限的善有善报还是低限的善无恶报,都是对社会正义的要求。我称善有善报的要求为有偿德行,称善无恶报的要求为无害德行,它们都以自利和自我保护为德行的前提,这种前提须落实为现实的社会正义。
传统伦理学大多无视有限德行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将德行归之于纯粹主体的无自我的自决,片面肯定无限德行而忽略了德行主体对自我的责任以及社会对德行的责任。传统伦理学的这一偏执导致了如下后果:其一,将要求社会正义的有限德行作为不纯粹的德行而排除在伦理学的视野之外,最多只是将它看作考察无限德行的一个反衬性背景;其二,社会正义问题被看作与德行无关的社会学问题,忽略社会对德行的责任,将德行状况的好坏归结为个人品性和道德教化问题;其三,以社会正义为先决条件的有限德行作为最一般的日常德行其正当性未得到充分关注,从而使传统伦理学远离日常道德实践。
当然,我们可以说最高的德行是无待于社会的,正是在一个颠倒善恶报应的社会中行善方现出德行本色,但那不是日常的德行而是超常的德行。日常的德行主体顾念有限肉身而在乎自我的现实存在,这种顾念与在乎自有其人性的根源和自然权利,它应得到理解与尊重,而不是蔑视,在此基础上的道德才是人道的。缘此,社会正义对日常德行负有不可推卸的人道责任,一个颠倒善恶报应的社会没有权利要求它的成员道德,或者说要求一个人在非正义的社会中行善往往是残酷而不道德的,比如要求一个人在事实上不允许说真话的社会说真话,无异于将他推入火坑。因此,要切实地改善一个社会的德行状况必须首先改变社会的正义状况。一个极不道德的社会如果总是将不道德的根源归结为个人的修养和教育,而不反省自己的道德责任以求现实社会的整治,这个社会的日常道德状况将是不可救药的。
不过,有限德行的逻辑只是强调有限德行的条件,只是说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日常德行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在不允许说真话的社会不说真话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显然,不能强求个人在不道德的社会道德,但个人也不能因此而在不道德的社会不道德。换句话说,在严重缺乏正义的社会,个人德行决不能是外在强制的,它只能是纯粹的自愿,即只有他自己有权选择放弃自我而献身道德价值,任何外在的道德强制都是不道德的。
所谓无限德行正起始于有限德行不可能的地方,它不在乎个人得失乃致于失去生命,它在超乎人之常情处显示人的另一种可能:自由地藐视社会不义而自由地行善。不过,无限德行作为纯粹自由的个人选择不能成为普遍的道德命令。
3、德行的根据限度与超越
无论是舍己救人还是救人不舍己,无论是天下有道才行善还是天下无道也行善,均涉及德行选择的根据问题,而有限德行和无限德行的区分也更深刻地反映在德行的根据上。
通常,我们说一个行为是善的或恶的,总得有什么依据,总得有某种标准。我们凭什么判断行为的善恶?我们根据什么行善?或什么是善恶?这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这里的“有什么”、“凭什么”“根据什么”、“什么是”的“什么”就是“德行的根据”,而“总得有”乃是俗常伦理学的基本信念,即“凡德行均有根据”是不言自明的,而“德行无根据”则不可思议也不予思议,伦理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这个根据。我称这种倾向为伦理学上的根据主义。
弗莱彻在《境遇伦理学》中谈到道德决断的三种基本方法,即律法主义方法、反律法主义方法和境遇方法,他的境遇伦理学旨在提倡后者而反对前两者。弗莱彻的论述之引起我的很大兴趣,不仅在于他对三者之差异的深入分析,更在于我从中看到了伦理根据主义的三种基本样式,因为三者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却有基本的一致,那就是对德行根据之存在的信念和寻找这种根据的冲动,不同的只是寻找这种根据的方式。律法主义者相信德行的根据是客观规范,他们在圣经和自然习惯中去寻找这种规范;反律法主义者反对客观的善恶标准,他们认为德行的根据是主观观念;境遇主义者反对前两者,认为德行的根据是在特定境遇中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原则。
伦理根据主义这三种基本样式暗示了最为深刻的德行限度;凡德行都必有根据(或标准),人们总要依据某种标准才能作出道德决断,没有根据的道德决断是不可思议的,问题仅在于:什么样的根据是正当的?
弗莱彻对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的批判也基于这一假定。在弗莱彻看来,律法主义不顾德行的具体境遇,以抽象的道德规范为标准来判断具体行为的善恶,这样做常常是行不通的。比如一个人为救无辜者而对谋杀者说谎,一个人发现信守某个约定会给很多无辜者带来灾难而违约,一个人为救无辜者而背叛某个暴君向无辜者告密,在律法主义者看来都是不道德的。对律法主义者来讲,凡说谎、违约、背叛、告密都是恶,凡说真话、守信、忠诚、保密均是善。显然,律法主义的上述道德决断是靠不住的,因为说谎、违约、背叛、告密、说真话、守信、忠诚、保密等行为本身并无所谓善恶,即无内在德性,它们只是对某类行为的抽象描述,其善恶取决于特定境遇中的行为动机与结果,即是否出于爱,具体而言,是否为了和事实上达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依此标准,上述行为就是善的。
看来,境遇性的功利主义标准比抽象的律法主义标准更有资格成为道德决断的根据,更不用说反律法主义那种随心所欲的主观标准了。问题在于:境遇性的功利主义标准能为一切道德决断提供根据吗?或者说它具有普遍有效性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其限度何在?
别尔加耶夫在谈到伦理学悲剧时提到道德境遇中的这一现象:当你同时面对两种善的冲突时如何决断?对境遇主义来说十分简单,选择大善(大利)牺牲小善(小利)。问题是善的大小可以算计吗?比如多数人的生命是否比少数人的生命更有价值?我们是否有理由和权利为了多数人的生命而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弗莱彻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苏格兰妇女明知道她一个患病婴儿的啼哭会把她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以及整个群体暴露给印地安人,但她仍然抱着他,结果所有的人都被杀害。一位黑人妇女发现她婴儿的啼哭会危害大家,便将这个孩子掐死,结果大家平安过关。弗莱彻问:“哪位妇女的行为正当呢?”回答当然是后者。不过,被杀的孩子是无辜者,保护无辜的孩子也是母亲的责任,因此,
这种正当是否也因无辜者的血而显得可疑?
准确的说,上述功利主义的道德决断只是人类面对道德两难所表现的无可奈何的“明智”,而不是什么“善断”。这种明智恰恰以恶为代价(黑格尔称此为绝对精神的狡计)。无论功利主义怎么算计,无辜者的血是抹不掉的。就此而言,道德两难揭示了人类道德决断的限度,或者说人一旦被抛进道德两难的境遇是无法行善的,在此,任何善的决断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比如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索菲的选择。纳粹军官要索菲选择让女儿死还是让儿子死,她感到无法选择。这种无法选择感正是道德决断的限度。最后她在极度的胁迫之下疯狂而本能的选择了让女儿去死,从此女儿那双向母亲求助的绝望的眼睛便成了她逃不掉的道德法庭。
别尔加耶夫称这种事实上无法选择的道德两难为“悲剧”,并认为悲剧是道德的最高形式。作为道德的最高形式,悲剧指的是人对无法选择的道德两难拒绝选择的痛苦担当。我将这种痛苦的担当称之为最高的无限德行。从根本上看,根据都是人为的约定,它没有绝对的正当性,不管是律法主义的绝对规范还是境遇主义的相对功利原则。人为的德行根据十分有限,它最多只能用于了然的善恶之间的决断,而不能用于善与善之间的选择。两难德行的境遇是一种无德行根据的状态,在此只有明智与愚蠢的选择而没有善与恶的决断。以牺牲一种善为代价选择另一种善就既选择了善也选择了恶,这就是道德的悲剧。
境域伦理学以功利主义的算计算掉道德悲剧中的恶与罪,使之成为道德喜剧,从而毫无罪感地面对无辜者的血,这种明智的德性实在可疑。一些法国游击队战士告诉A•米勒,他们在二战期间的主要生活手段是说谎、做假、偷窃、残杀,不仅要杀死敌人,有时为了保密和别的目的也要杀死自己人。于是米勒问他们:是否什么都允许?他们回答:“对,一切事都允许——同时一切事都禁止”。“一切事都允许”,因为“明智”,“一切事都禁止”因为“不道德”。因此,米勒评论说:“如果要杀人和说谎,一定要是处于最紧急的社会必然性的压力之下,还要具有深刻的犯罪感——此时此刻找不到任何更好的办法”。游击队战士和米勒都不同程度地体认到了别尔加耶夫的“悲剧”所具有的无可奈何的深刻的犯罪感。境遇功利主义者弗莱彻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应该把他的‘犯罪’一词改作‘遗憾’,因为此种悲剧性境域正是遗憾的理由,而不是悔恨的理由”。经此一改,悲剧即无,也无须担当不可避免的罪。因此,那些在战争中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杀人的英雄是无罪的,战后他们无须忏悔和不安,只有那些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杀人的刽子手才是罪人。这样的道德逻辑乍听起来颇为顺耳,但总有些令人不安,比如那些决定在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的人,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为了拯救更多的人,他们选择了让几十万无辜者去死,在这些决定者中有的仅有遗憾,有的却有摆不开的罪感,谁更道德?
罪感是道德悲剧感的直接表现,它先于任何功利理性的推断而直面人的德行限度,它不根据任何人为的准则来取消道德两难的无根据状态,它是拒绝决断又不得不决断中的痛苦与犹疑,它不认可道德两难中任何决断的正当性,以正视和担当罪的方式咀嚼被迫选择的后果,因而它是一种担当不道德的悲剧的德行,是无限德行的最高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