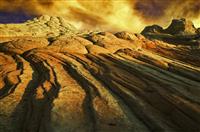去年年底,曾经读到法国社会学家杜兰(Alain Touraine)的文章〈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1。杜兰在文中说法国知识份子有理性与实践相脱离的「传统」:「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是奔达(Julien Benda),他曾经高呼《文人的背叛》(即La Trahison des Clercs,下文采用内地常用译法,译成《知识份子的背叛》),要求知识份子起来捍卫真理,他后来成为斯大林分子」。对于朱利安·奔达生命的最后十年的言论和行动,我未曾作过甚么详细的研究,但是,就读到的奔达1946年为此书写的再版前言中对斯大林主义抨击激烈的言辞来看,杜兰的这个结论是值得置疑的2。
在1946年再版前言中,奔达不仅从他的唯理主义出发完全否定辨证唯物主义,而且在「知识份子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节中,明确地批评知识份子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背叛自己的职责。譬如,他直截批评斯大林在「五年计划的演说」中的朝令夕改是「今天的状况若是把别的真实作为必要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受作为真实的昨天的断言所约束了」,而且引用传记作家马克·维希尼克(Marc Vichniac)的话,即「革命家列宁的伟大力量就在于有决不拘泥于前一天自己作为真实所说的话语的能力」,并把这句话与墨索里尼的「要警戒前后一贯这种死亡的陷阱」相提并论3。此外,他还认为知识份子遵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压抑个人自由也是一种背叛4。当然,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右翼把攻击共产主义作为否定民主主义的一种手段5。从1975年版的《知识份子的背叛》的爱迪安勃尔(Rene Etiemble,1958)序和196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勒沃夫(Andre Lwoff,1975)的序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么一种情况,即使1950年前后一段时间关于时局的言说与法国共产党非常接近,但是他没有停止过对左翼的批判,因为这种「同路」是有条件限制的。奔达说:知识份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但是,对左翼的政治也必然有不同意的东西。涉足于政治的知识份子的职责,是向人们诉说正义与真实6。近日读到法国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的两部关于战后法国知识份子的著作的中译本:《20世纪的两位知识份子:萨特与阿隆》和《知识份子与法兰西激情》7。这两部著作对奔达战后的言行都有涉及,从中可以知道战后奔达的一些言行和政治倾向,即40年代末,「当时站在第一线反对右派并履行对右派反击职责的,经常是非共产党的左派」,奔达也是其中一位。1948年他在《欧洲》杂志上写道:「法国人民必须在这两个集团极其在法国领土上的表现形式之间作出选择」8,所以,战后与右翼的对峙中,奔达又继续与法国左翼做过「同路人」。最严重的是1948年夏天,他作为法国知识份子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波兰召开的世界知识份子保卫和平大会。而这次会议是由苏联主持的9。
除了1946年再版前言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之外,以后他的言行也未必始终与法国共产党或斯大林主义分子保持一致。例如,战后,1939年脱离共产党、不久就被德国人杀害的作家尼赞(Paul Nizan)不仅被法国共产党和第3国际再度称为叛徒,而且指责尼赞是德国占领时期向维希政府内政部告密的「员警」。当1947年萨特(Jean-Paul Sartre)起草了一份为尼赞恢复名誉并指责共产党不实的诬陷的呼吁书的时候,奔达也在这上面签了名10。当然,那以后的一段时期,奔达被斯大林主义分子引以为自己的友军也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应注意到爱迪安勃尔在《知识份子的背叛》的序中的提示:「我也希望诸位忘记斯大林主义者们那种对奔达的别有用心的过度阿谀和谄笑。今天他们对自由的知识份子感到很不愉快,爱留特利乌斯早已不是他们的友军了,斯大林主义者们的心中奔达他也走进了『背叛的知识份子』的阵营中去了」。而且,作为当代修道僧进行着艰难的修炼的奔达不等于就是神,只是接近先知圣贤的人,何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像萨特,我们能把他称做斯大林主义分子吗?中国的鲁迅,不是也站在与右翼对抗的第一线,曾经为 「别有用心的过度阿谀和谄笑」所包围,为之所动吗?
正如勒沃夫在序中所说的那样这种过激和极端主知主义、唯理主义不容易为人们广泛接受。比如罗杰·法约尔(Roger Fayolle)就不那么赞赏奔达。他说「揭露非理性主义和歌颂理性的过程中的这种偏执本身,不就是奔达所揭露的『弊病』的一种极为有趣的表现吗?」11当面临许多现实问题,特别处在法国左、右两大阵营非此即彼的论争中,他自己也常很难自圆其说。正如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中所说「一个纯粹理性的人是一个抽象化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决不会存在,同时,每个人又都是由他的有意识的活动和非理性的体验而构成的」12。就在《知识份子的背叛》出版后的3年多,1931年1月18日奔达在一篇〈为了欧洲及法德互谅而反对过分民族主义的宣言〉上与其他185名知识份子一起签了名。1934年他又在《大众报》刊出的题为〈呼吁斗争〉号召警惕法国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宣言上签名。这是一次由非共产党左翼知识份子发起的签名,事后他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因为最近在一篇被认为是「左派」的宣言上签了名,我被指责违背了我要求知识份子具有的那种永恒性。我答复如下:我之所以在这篇宣言上签名,是因为它在我看来是对一些永恒原则的保卫战。随后,我又被邀请在另一些文件上签名,它们出自暂时的、具体的政治活动,我拒绝了。我坚信,作为知识份子的作用体现在对一种神秘主义的保卫,而不在于对政治的参与。左拉作为知识份子的作用在于提醒人们尊重正义......有人对我说:您不应该签名,即使为了左派的神秘主义。您既不应该是右派,也不应该是左派。我回答说,左派的神秘主义对知识份子来说是可以接受的13。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参与倒反而是一种背叛。3年后他又参加了一次反法西斯的签名。事后又如此辩解:几天前,有个委员会向我征求签名,为了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抗议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屠杀。我拒绝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明年法西斯主义者战败并全部被屠杀,我将热烈鼓掌。我不赞成人类生活中的宗教信仰,我赞同的是对一种原则的根除,它体现在人类生活中。我不是人道主义者,我是形而上学着。恰恰相反,于是便有了我的这种做法14。
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中的分析,正巧指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奔达那种立场的弱点:人们的理性把神圣看作神秘主义,而现实社会中所谓的神圣却犹如宗教信仰。所以,他经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西里奈利的著作中认为,奔达在30年代起就是与左派「同路的中间派的知识份子」15,这一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们不能苛求奔达,因为奔达也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这样圣职者──知识份子滋养的土壤,他在《知识份子的背叛》的最后也言说了自己对未来知识份子立场的悲观的预见。他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里,要求人们至少在捍卫正义和真实(这是一个底线)的同时,固执地坚持他的「唯理主义」(注意!他没有说单有理性就能保证正义与真实的出现)。正义和真实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伦理规范,作为这个社会的精神生产者与传播者难道没有必要提倡乃至过分强调这种坚持吗?所以,在极权主义猖獗的狂澜到来之前,奔达也参与了现实的斗争。我们再读读另一位20世纪大师阿伦特(Hannah Arendt)50、60年代的那些著述吧!(如《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等)她对现代社会中正义、真实的日益消失、或被歪曲和模糊的危机,也是充满了一种激情进行批评和发出警惕的呼唤。
问题是为甚么奔达会倾向左翼?
奔达1867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比利时犹太人血统的富裕的商人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法兰西传统教育,但是,少年时代一度又沉湎数学的学习,人文学科的基础与理性的追究这两方面都对他以后的「主知主义」、「唯理主义」产生很大的影响。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后,21岁那年不得意又进入高等工艺学校,但是出于天性的对实学的应用科学的厌恶,第三年退学。24岁那年服役入伍,退伍后有重操学业,转入巴黎大学学习历史哲学与「批评的方法」。30岁那一年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对他的世界观的奠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从此把他引入了笔耕生涯。我们在读《知识份子的背叛》时,从他对法国民族主义的右翼(从巴雷斯到莫拉斯)的激烈批判中也会感悟到这一点。「从德雷福斯事件后,把作家分类为左派作家和右派作家是很常见的」16。总的说来,奔达倾向左翼,我想这和他是犹太人有关,有一种需要自我防卫的潜意识,因为法国是欧洲最具有激烈的反犹传统的国家(希特勒上台之前甚于德国),而右翼总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
奔达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的声誉的。尽管奔达一生著述甚丰,但是,仅从《知识份子的背叛》的两篇序读来,就可以知道至少奔达生前在法国文坛不是头上戴满了光环的幸运儿 勒沃夫在序中说,虽然他强烈地、热情地、果敢地提倡普遍的价值,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已经预见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即将盛行为世人敲起了警钟,是一位预言者,但是,因为他是个反潮流者、是个桀骜不羁的精神人、自由人。他逆时代潮流而动(如当本格森主义最时髦的时候反本格森的直觉主义、反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厌恶流行、狂热、结社、运动、党派。非正义、谎言和不合理都会引起他的愤怒,所以,生前成了文坛的「被活埋的逝者」。 他也曾为这种被边缘化感到苦恼,甚至曾经向「爱迪安勃尔诉说了作为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的困难的状况』」。从他的两部自传性的著作《一个知识份子的青春》、《当代的修道僧》中我们不时也可以读到他那孤寂的心情与处境。他是从新闻写作创作步入文坛的。他的小说创作似乎不太成功(他早年的小说《圣职授予仪式》也曾经获得1912年龚古尔文学奖的提名,遗憾的是最后表决时,评委的投票是5比5,未能得到多数通过),然而,他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领域中却名声大振,「他具有刀笔之才,他的好些敌手都为之胆战心惊。他在法兰西文学中可与瓦莱斯和布卢瓦媲美」17。其中最出名代表作的就是《知识份子的背叛》。
这几年在中国读书界受到欢迎的波兰裔英国学者鲍曼(Zygmunt Bauman)高度评价《知识份子的背叛》,把它称作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宣言」,自那时起「这种关于知识份子们具有某种特殊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使命的理解便统治了受教育阶层的自我意识──即使有人声言反对」(着重号系笔者所加)18。但是,对于中国读书界来说,朱利安·奔达的名字还是比较陌生的。即使在20世纪末在讨论人文精神的缺失时,或兴起一阵顾准热、陈寅恪热时,乃至因为高行健主张文学要脱离政治引起论争时也未见国人言及奔达及其《知识份子的背叛》。想必随着最近几年国内翻译、出版西人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论著的增多19,中国的读者也会关心起奔达及其著述来。
注释
1载《二十一世纪》网路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第9期,2002年12月。
2萨义德(Edward Said)也根据1946年的再版前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奔达重新出版他的书这次增加了一连串对于知识份子的攻击,这些知识份子是和纳粹合作的人以及不加鉴别地热情拥抱共产党的人」。《知识份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页15。
3、4、5、6 Julien Benda, La Trahison des Clerc, Grasset and Fasquelle, 1975,P96-97,14。
7、8、9 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份子──萨特与阿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页267,页272-273 。
10西里奈利:《知识份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页180-183。
11法约尔:《批评:方法与历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279。
12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123。
13、14、15、16 《知识份子与法 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页87-88,页109,页44。
17《当代法国文学词典》(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5。
18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页260。
19已经出版的大致有: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份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兹纳涅茨基(Znanetsky)《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和詹森(Paul Johnson)《知识份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份子:萨特与阿隆》和《知识份子与法兰西激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古德钠(Alvin Gouldner)《知识份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柏格斯(Carl Boggs)《知识份子与现代性的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罗宾斯(Bruce Robins)《知识份子:美学、政治与学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戈德法布(Jeffrey Goldfarb)《「民主」社会中的知识份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以及萨义德《知识份子论》(三联书店,2002)、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诺齐克(Robert Norzick)等《知识份子为甚么反对市场》(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