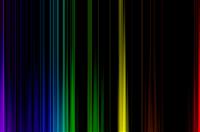储朝晖:
我从1983年开始做教育的实地调查。目前中国的教育确实问题很多。我归结为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办的是谁的教育?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1949年提出一个明确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1953年就开始办重点中学,1954年对办重点中学质疑,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向工农开门。58、59年大跃进,就不办重点中学了。62年又开始办重点中学。文革中重点中学办不下去了。1978年后又大办重点学校。在高考指挥捧作用下整个教育成为少数人办的教育。六十年来在公平和效率、教育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还是培养少数人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事实上,直到现在,可能有更强大的力量来办少数人的教育,而不是办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教育。
第二是办什么样的教育。把教育当成一个工具,还是通过教育来真正培养人。把教育当成本身有主体性的独立自主的存在,还是把教育当成一个工具,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我们的教育没有自主性。现在讨论教育的问题,它的本质不是教育,而且教育之外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刚才有人说学校曾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就是学校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过度的行政化,这个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我认为不是用冠冕堂皇的词能表达的,实际上它是封建专制的思想、封建专制的理念在起作用,而不是讲的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什么在起作用。
由于经过改装的过度的封建意识、过度的封建管理体制、过度的封建教育方法起作用,所以使得教育不是我们说的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些词所表达的内涵,依然是内含封建的教育。
第三怎么样去办教育。我们采取办教育的方式,简单来说是通过政治方式来办教育,不是通过办教育的方式来办教育;采取的完全是官本位的方式,对学校的管理完全是采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不是符合学校特性的管理方式。有的人就说中国所有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其实下面所谓的校长都不是校长,只是一个执行者。那么办学过程中,它的第一依据就是第一校长发的红头文件,而不是每个具体的校长、每个具体的教师他们自己的思想,更不是每个学生成长发展的真实需求。如果这种办教育的方式不改变,教育就没有好结果。不管是杜威的儿童中心理念,还是陶行知所提出的一些理论,我认为都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大众的利益。教育要想真正办成人民的教育,就必须使它是以人民愿意接受的方式办教育,人民需要的方式办教育,每个人成长发展需要才应当是教育教学的第一依据,这是一个基本目标。这个目标不能满足的话,就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目前,我感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杨老师说我们78年完全是倒退到一九五几年的教育方式;但是我觉得能够倒退得更多一点会好一些,如果能够倒退到1949年,甚至倒退到更前一些,我觉得当时办教育的方式是更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更符合教育的专业特性,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1949年全国政协《共同纲领》所提出的办教育的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这个方针是真正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利益的教育方针。现在我们做出的纲要,如果能够回到六十年前,就是1949年这样的办教育的方针,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是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倒退。但是,我们七七年恢复高考以后,当时恢复的是一九五几年的那种办教育的方式。五七年办教育的方针远远比1949年的方针要落后。这个方针到1952、53年,甚至从1951年开始批判《武训传》起,52年开始就整个倒退到更加落后的苏联方式上去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真正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样一种教育。事实上,这个教育方针并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了,而是当时中国各种社会力量一个共识。为什么讲呢?1986年曾经在延安工作的黄乃一到安徽去,当时我接待他的。他说三十年代末、四零年前后,他们当时为了写一份确定中国共产党文教方针的文件。当时找到陶行知的一篇文章,叫《生活教育之特质》,是陶行知1936年写的。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大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生活的,要满足生活的需要;第二个特质是行动的,认为这个教育不是挂在口头上的,要去做的;第三个特质是是大众的,不是少数人的,不是少爷、小姐的;第四个特质是前进的,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第五个特质是世界的,就是我们现代通俗讲的有国际视野的,是把教育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加以界定的;第六个特质叫有历史联系的,我们的教育不是悬在半空中的,是古今中外的延续。黄乃一说看到这篇文章茅塞顿开,后来就把这一精神吸纳到文件中。
所以,当时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的六大特质事实上跟后来讲的民主、科学、大众的方针是一致的。这个我做过一些史料的考证,包括延安当时成立的陶行知研究组织,也成立了其他的研究组织。我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早期是中央研究院的教育研究室,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些研究,提出了教育的方针,提出来民主、科学、大众的这个新民主主义方针,代表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精英对教育的前卫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要把现在普遍实行的国家主义教育转向以人为本的教育。事实上,有很多人不认同我这样一种说法。我记得在05年,有一次在武汉开研究余家菊的会议,他是典型的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我就说中国1950年后办的就是国家主义教育,我一提出来就有很多人反对。我们的教育是要为每个具体的人服务的,只有在这个基础、前提下,它才能更好的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复兴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的前提,仅仅强调教育一定要为国家怎么样的,教育一定要为某个组织怎么样的,最终必然是办不好教育,教育必然走向一个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当中去,因为这样做目中无人。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今年年初2月4日《光明日报》访谈的时候,我也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了。
第三个问题,要完全彻底的消除阶级斗争的理论对我们教育的影响。我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对我们教育不仅有影响,而且影响还很深。包括幼儿园小孩子、小学生唱的歌,包括很多的教材内容,包括一些口号,墙上贴的很多标语,生活当中很多老师教导的方式,背后都潜存着阶级斗争的理论。包括很多的规章制度的设计、要求,背后都有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根基。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消除阶级斗争这个理论的影响,那么想办好教育,我认为很难。因为这个基础就弄错了,这个大前提就弄错了,直接影响到健康人格的成长。
所以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在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基础上,再谈教育怎么改进。
徐景安:
朝晖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怎么体现“以人为本”呢?全社会都提以人为本,企业、学校、政府都要以人为本,那么教育领域怎么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雷祯孝:
教育问题,我有几个调皮的考察,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东平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您说的要退得再远一点更好,我现在退到先秦来说。因为我读了整个先秦的诸子百家的原著。我是学化学的,不得已我啃原著。读来读去,我读出古代思想两条线索:一条是人才思想史,一条是奴才思想史。
国家教育就是,你听话,你执行我的。而且,很有意思,用“教育”这个词来称呼这个行业,古代没有。古代不叫教育官员,他叫学官。
我们很想得到帮助,希望知道“教育”成为一个行业的统称,是从何时开始的?是谁主张谁批准推向全国的。“教育”这个词,现在我们开始质疑。就是用“教育”这个词称呼学校求学孩子成长这个行业是否是最好的称呼。
我们希望外文很好的朋友帮助查一查用英语注释英语的education,把那些注释的英文再查一查是什么意思。我们预感,education可能更多是办学,求学,管理学校,指导学生学习、研究、尝试创业等等意思,而翻译成为“教育”,也许并不算准确。
有人说,可能“教育”这个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而日本翻译时,也许正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为了大批量培养工业需要的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的人员的时候。
《孟子》说过人有三种快乐,其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也许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教育”一词,但是很显然孟子并不是指一个行业,而是指一个行为。好像过了很多朝代,也没有人响应。现在是电子古书,很容易查。我们查了很多著名学者的全部原著,没有查到“教育”这个词汇。例如姜管老庄孔,墨晏荀韩吕,直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的《日知录》里都没有“教育”这个词。目前我考察到是从王阳明才开始提到四次。此后严复介绍外国的education,翻译过来就用了“教育”这个词。
我常常困惑,为什么荀子写《劝学》而不同时写一篇《劝教》?为什么《四书》里有一本《大学》而没有一本《大教》?为什么不把“北京大学”改成“北京大教”?如果把北京理工大学改成北京理工大教会怎么样?为什么不把“物理学”改成“物理教”?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用“佛学”来称“佛教”?为什么不把“学问”改成“教问”?为什么整部《论语》,没有一个“教育”这词?为什么整篇《师说》没有一个“教”字?为什么把有大的研究成就的人叫“学者”而不叫“教者”?
学与教,到底谁为了谁?
《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礼记••礼运》:“闻来学,不闻往教。”
九个字、八个字、七个字,是不是阐明了同一个思想:学是主体,教是辅导。一个好教师一定是保护鼓励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的。
闻来学,就是听说那些穿着草鞋、走千百里路去求学的故事。求学是内在的,学生为主体,儿童为中心的。我就说古代这个思想和杜威、陶行知他们是呼应的,也就是那个时候是呼应的。
我们再查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看那个“教”字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原文:“上所施,下所效也”。“教”字的核心含义是要被教者仿效、服从、顺从、依从、接受。古时候的“政教合一”、“以法为教”,都是以服从作为“教”的核心含义。我终于明白了。所谓“教育”,就是按我的意志办,你们所有的人按我的意志成长,变成我想要的这种人。
我感觉到我们的“教育”,调皮一点地说,这个行业应不应该叫“教育”?我都觉得要研究、要考证。
面对中国学校、学生、考试等现状,社会上有三种态度。第一,我们十分理解那些对教育现状歌功颂德的歌德派,我们理解他,因为他要吃饭,他要升官。第二种,我们非常尊敬,对教育弊病的抨击、揭露的缺德派。还有第三个态度,就是我们渴求呼唤探索解决问题的立德派。这个立德是我自己杜撰的,不知道以前有没有。
要解决问题不容易,因为这个事太大了,你要解决教育部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三年到四年中央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文件,国家,包括国务院、中共中央,鼓励下面探索解决教育问题。我就觉得有这个精神在里面。
所以,我跟东平商量,我们有一伙儿人都想主办一个杂志叫《办新学》。办学,就是以儿童为中心,有没有办新学的人?全国很多。尤其我到广东去,办新学如雨后春笋。我在广东不管走到哪,人家都给我介绍,说这是什么什么教育的“创始人”。
我建议你这个讨论会,北京开一回,广东开一回。探索那些办得好的,能够给我们启发的,能够生长出来新的办学方法,如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会不会更好?我觉得要关注办新学解决问题、探讨问题的人们,更加需要去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办新学、探索解决问题的这些人。
徐景安:
雷教授讲的最有启发的三句话,歌功颂德那些歌德者是缺德,明明我们的教育办得那么失败,他还在歌德那是缺德。对教育时弊批评的所谓缺德者还是有德的,还有良知。我们的目的是要创、要建,就是立德。非常赞成雷教授的意见。
蔡维钧:
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三种关系一直在中国教育领域处于模糊的状态。
1、党和教育的关系。中央管到大学教材这样一个微观的具体的教学业务的话,那么中国教育的改革就非常难以推进。学术自由这个大学的宗旨就不能实现。不知道哪个国家会这么做。党怎样处理和教育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2、政府和教育的关系。总理温家宝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我们的教育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是否也应该建立一个服务性的教育部呢?现在教育部是管教育,而不是服务教育,这是一个主和客的关系问题。如果把教育部当作教育的管理者,我们关于教育的思考就永远不能前进,教育问题就永远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变。目前的现状是违背国务院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精神。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就永远没有教育家,只有官员。
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遵从教育自身的规律,然后才谈得上搞什么样的教育。我们把教育变成被支配的工具或为什么服务的工具,这样的教育就是一个工具事业。教育只有回归教育本身,回归于为人服务的教育,才能真正的走出教育的困局。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真正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这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
这三个关系要理清楚,下面的路才好走。
第二、我只讲一句话,教育比军队重要。
第三、回归人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不以国家为本的教育,不是以民族为本的教育,更不是以政治为本的教育。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就是回到学生自身,在学生和老师的互动中承担文明的传承、人格的塑造和人的自我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功能。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因为教育培养目的是工具,工具是要有人使用才能有作用的,现在金融危机,企业倒闭多了,使用学生的少了,每年近700万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如果学生可以创业,也可以做事,从我被使用,到自我展现,从而大大减轻社会就业的压力。教育从工具教育变成主体教育,我们的教育事业就有新思路。否则,我们被管理,我们被教育,我们被作为工具,我们的思路,我们的思想都没有了。中国的教育被窒息,民族的希望就渺茫了。
徐景安:
教育是党管、政府管,把教育作为与资产阶级争夺的场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虽然不提这个口号了,但还是这种思维模式。我不管,谁管呀,学校不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场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堡垒?这个扣必须解,又怎么解?这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