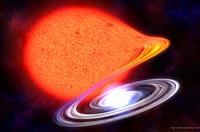有一年秋天,蒲松龄搬到村外关帝庙修改《聊斋志异》的稿子。院墙东倒西歪,大殿窟窿朝天,只有两间西厢房还牢靠些,使用写过字的大仿纸糊了糊窗户当作书房。
一天晚上,月亮滴溜圆,照得天地明晃晃的。蒲松龄写到半夜,站起来舒展舒展胳膊腿儿,正想抻铺睡觉,忽听破门“吱扭”一声,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前头那人瘦高个儿,眉、眼、嘴耷拉着,叫人一瞧就抽凉气;后头那人是锉子,黄眼珠滴溜骨碌乱转悠,都是秀才打扮。
蒲松龄一打量,就端详出不是正儿八经的人,起身问道:“两位大哥尊姓大名,来此贵干?”瘦子弓着麻秆腰说:“我姓甄名贵,他是胡仁老兄。敢问大哥是蒲先生———台甫松龄吗?特地前来拜望拜望。”蒲松龄连忙回答:“我是蒲松龄,两位大哥有何见教?
请说吧。”
甄贵瞅着桌子上一迭稿子问:“这是先生的大作《聊斋志异》吗?我们已读过几卷了。”“我也看过,我也看过。”胡仁也抢着说。蒲松龄一时还猜不透他俩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正纳闷,只见甄贵从怀里掏出两锭银子,双手托着,恭恭敬敬地送过来:“蒲先生,这是俺弟兄俩的见面礼,请收下吧。”
蒲松龄一摆手:“趁早收起银子,有什么话只管说就是了。”
胡仁一把抢过银子,放大嗓门说:“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打开窗子说亮话吧,就是劝你把那本坏书《聊斋志异》撕个稀巴烂,再不就一把火烧他娘的!”甄贵接上说:“蒲先生是明白人,小弟也就直言相告了。《聊斋》一书传出后,说什么闲话的都有。这等书只宜当作笑料儿,公之于世万万不可。
我这可是‘忠言’啊!”
蒲松龄咯噔一愣,心想:自从几卷聊斋故事手抄本传出去,有的叫好,有的恼怒,有人出重金收买,有人告到衙门,请求县太爷摘下我的秀才帽子……不过,像这两个陰陽怪气的家伙半夜三更上门唬我,还是头一遭儿!甄贵见蒲松龄发愣,胆子就大了起来:“先生既是读圣贤书,可知道什么叫‘非礼勿言’吧?念书人净写些男欢女爱的事,还要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蒲松龄寸步不让地说:“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什么?”
胡仁不耐烦起来:“别说那些配对成双的事,拣大事问他。
我说姓蒲的,你指鸡骂狗地骂皇上和父母官该当何罪?再说,张嘴就骂,成何体统?”蒲松龄毫不示弱,拍着桌子说:“昏君和赃官也骂不得吗?陷害忠良,贪赃枉法,不骂还行!”
胡仁一蹦老高,拍着屁股喊:“好,好,巧言善辩!姓蒲的,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蒲松龄反唇相讥说:“二位是干啥的,我说不上。不过,你们虽然戴着秀才帽子,说不准都没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吧?”
胡仁被蒲松龄敲打得咋唬起来:“好,算你一嘴说对了!实话对你说吧,他是陰曹地府的秀才,我胡大爷是得道的狐仙,今天就找你算账来了!”蒲松龄觉得头皮一炸,心想:生平不做亏心事,哪怕半夜鬼叫门!我倒要看看这些丑八怪有啥能耐!鼻子“哼”了一下:“你们本来就不是人!甄贵者,真鬼也;胡仁者,唬人也;我说得可对?”
胡仁嗷嗷地质问说:“对,对又怎么着!我们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啥把鬼狐的八辈子祖宗都骂了?”甄贵也嚷起来:“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先生大笔一挥,把俺们狐媚和唬人的看家本事全抖搂出来,这不成心要人家的难看,专门砸人家的饭碗吗?”
蒲松龄“噢”了一声:“闹了半天,是我的那些鬼狐故事得罪你们了?不明白的是,我写的鬼狐有好有孬,褒贬分明,怎么得罪的,我还不知道呢!”胡仁说:“你把耳朵里的驴毛掏干净,好生听着:先说第一卷吧,有《捉狐》,有《咬鬼》,有《狐入瓶》,还有《画皮》……”蒲松龄截住说:“慢讲,我先说说,娇娜和清风,难道不是胡(狐)家惹人喜爱的好姑娘?王六郎宁可继续做鬼不寻替代,难道不是贵(鬼)本家的好儿郎?”
甄贵忍不住地问:“为啥要写些坏狐、坏鬼呢?”“为啥要写?”蒲松龄理直气壮地说:“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丑类!陽世间不都是好人,陰间和山林里就那么干净?我所写的鬼狐,有好有坏的,有不好不坏的,有从好变坏的,有从坏变好的,就事论事,不抱偏见。做坏事的‘正人君子’不如禽兽;做好事的禽兽,也值得大书特书!”
甄贵嬉皮笑脸地问:“先生你看俺弟兄怎样?请费费神为俺二人立个传行不行?”蒲松龄忍不住笑着说:“哼,二位倒真是难兄难弟,可惜我看不出你们有什么德行!也没法将二位写成两条腿的人。”
胡仁一蹦老高:“少和他啰嗦,干脆来痛快的吧!姓蒲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把我们的劝告当成耳旁风,咱话是一句,今晚要不烧书,就怪不得我们手下无情了!”胡仁也虎虎地瞪起黄眼珠说:“老老实实照办,万事皆休;不然,先让你大儿子死给你看!”
蒲松龄被这两个家伙缠磨了大半夜,累得实在够呛,正寻思摆脱的办法;只觉眼前一黑,定睛看时,哪里还有什么甄贵和胡仁!他踉踉跄跄走到床前,想和衣而卧歇歇。刚躺下,猛听得咚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有人大喊:“大爷,不好了!俺大哥死了!”蒲松龄顿觉天旋地转,心如刀绞。
来送信的是蒲松龄的侄子。蒲松龄共有三个儿子,因日子窘,从小饥一顿饱一顿的,身板都不硬朗,老大落了个气喘病,蒲松龄为他寻偏方,请大夫,心血花费不少,却去不了病根,天一凉就犯。儿子死得这么突然,不由得老泪横流。过了一会儿,蒲松龄勉强坐起来说:“侄啊,你先回去,我,我随后就家去。”
侄子嗯了一声走了。
蒲松龄望着桌子上那盏油灯,心乱如麻。儿子死了,我这个当爹的倒去送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擦了擦泪,刚想起身回家,两扇破门“吱扭”一声,又被人推开了,进来的竟然还是甄贵和胡仁。“蒲先生,唉,太不幸了,令郎年轻轻地就这么死了!
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啊!”“姓蒲的,不是兄弟埋怨你,早听人劝,也不至于如此!”“若是不烧书,谁敢担保你再不出事了!”
甄贵和胡仁一唱一和,蒲松龄差点儿气炸了肺。俗话说:“一人拼命,万夫莫当”,蒲松龄在气头上,不知哪来的偌大力气,一个箭步跃到桌前,伸手去拿鸡毛掸子,没想拿错了一支大号毛笔,又急转过身子,抄起了顶门杠子,喝道:“你们这两个瞎了眼的狗东西,竟敢害死我的儿子!告诉你们,就是我全家都被害死,《聊斋志异》也要公之于世!说!为啥害死我的儿子?”
甄贵和胡仁吓得老母猪筛糠,缩做一团,扑通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先,先生饶命,你儿,你儿子是病入膏肓,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借,借此敲你的竹杠。你不烧书,我们也害不了你全家;不光害不了,你小儿子还福大命长呢!”
蒲松龄真想照他们头上抡一棍子,又不愿弄脏了手。一愣神,甄贵和胡仁一骨碌爬起抱头溜出门外。蒲松龄拄着杠子喘着粗气,听得门外传来了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啊,这老小子可真厉害!”“熬了一宿,不光碰了一鼻子灰,还差点挨了顶门杠子。”
“你怎么不使出龇牙裂嘴的本事呢?”“你怎么不拿出披头散发、伸长舌头的本事呢?”“要不咱再进去试巴试巴?”“别,你没见他攥着笔、举着杠子的凶相?”“谁说不是,我看他就像喜欢吃鬼的钟馗!”“我觉着他如同专门捉妖的张天师!”“罢,罢,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蒲松龄听见装没听见,压根儿就没把它们放在眼里。他放下笔,扔掉杠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门外。但见月明星稀,蓬蒿满院,甄贵和胡仁早已无影无踪。他穿过关帝庙空荡荡的院落,向回家的小道上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