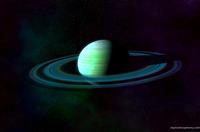文:罗洛·梅
一天傍晚,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一位国王正站在他的窗前,隐约地听着宫殿另一端接待室里飘出的音乐声。国王因为刚刚参加了一次接待而感到浑身疲乏,他望着窗外,泛泛地想着世间的事情,但没有考虑某件特定的事情。他的目光落到了下面广场中一个男人的身上——显然是一个普通人,他正走向那个拐角处想乘电车回家,许多年以来,他每个星期有5天都要走同一条线路。国王在想象中追随者这个男人——描画着,他回到了家,敷衍地吻了吻妻子,吃过晚饭,询问孩子们是否一切都好,读读报纸,上床,或许与妻子做爱,或许不做,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又起来去上班。
突然,一种好奇心占据了国王的思想,这使他有一会儿忘记了自己的疲乏,“我想知道,如果将一个人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关在一个笼子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因此,国王第二天叫来了一位心理学家,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并邀请他来观察这个实验。然后,国王让人从动物园搬来了一个笼子,而那个普通人被带来关到了这里开始时,那个人紧紧表现出了困惑,他不停地对站在笼子外面的心理学家说:“我必须要去赶电车,必须要去工作,看看什么时间了,我上班要迟到了”但后来到了下午时,那个人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强烈地抗议,“国王不能对我这么做,这是违法的,是不公平的”。他的声音强而有力,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
在那个星期接下来的时间里,那个人继续着他的强烈抗议。当国王散步经过笼子时(就像他每天所做的),这个人会直接向这位最高统治者表示抗议。但是这位国王每次都会和他说:“看看这里,你能得到大量的食物,你有一张这么好的床,而且你还不需要出去工作,我把你照顾的这么好——所以,你为什么还要抗议呢?”接着几天之后,这个人的抗议减轻了,接着过了几天就停止了。他静静地呆在笼子里,通常情况下拒绝谈话,但是心理学家能够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仇恨像烈火一样在燃烧。
但是几个星期以后,心理学家注意到,在国王每天提醒他说他被照顾的很好以后,他似乎越来越好像会停顿一下——仇恨会推迟一点时间然后重现在他的眼睛中——就好像是他在问自己,国王所说的话是否有可能是事实。
又过了几个星期,这个人开始与心理学家讨论,说一个人被提供食物和安身之所是一件多么多么有用的事情,说无论如何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命运生活,并且说接受自己的命运是明智之举。所以,当有一天,一群教授和研究生来观察这个被关在笼子里的人时,他对他们非常友好,还向他们解释说,他已经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说安全感和被照顾是非常重要的,还说他们一定可以看出来他的选择是多么合情合理,等等。多么奇怪!心理学家想,而且多么可怜——他为什么那么努力地想要别人赞同他的生活方式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国王走过挺远时,这个人便会在笼子中隔着栏杆极力奉承讨好国王,并感谢他为他提供了食物和安身之所。但是当国王不在院子中,而他又没有意识到心理学家在边上的时候,他的表情便迥然不同——闷闷不乐,愁眉不展。当看守人隔着栅栏递给他食物时,他经常会打翻盘子或弄翻水,然后他又为自己的愚蠢和笨拙感到尴尬不安。他的谈话开始变得越来越单一不变:他不再谈论他关于被照顾之重要性中所涉及的哲学理论,相反他开始只说一些简单的句子,像是一遍又一遍反复的说“这是命”这句话,或者仅仅是咕咕哝哝自言自语“这是命运”。
很难说这个最后阶段是何时开始的。但是,心理学家开始觉察到,这个人的脸上似乎已经没有了特别的表情:他的微笑不再是奉承讨好的,而仅仅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就像是婴儿在肚子被笑气所麻醉时所作的鬼脸。这个人依旧吃着食物,不时地与心理学家谈几句,他的目光是遥远而模糊的,而且尽管他看着心理学家,但似乎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看到他。
现在,这个人在毫无条理的谈话中,再也不用“我”这个词了。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笼子。他不再有愤怒,不再有仇恨,也不再有合理化。但是现在他已经精神错乱了。
那天晚上,心理学家坐在自己的会客室里,竭力想写出一篇总结报告。但是他却很难想到恰当的措辞,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内心有一种巨大的空虚。他不停地用这些话来尽力消除自己的疑虑,“据说,什么也不曾失去,物质仅仅是转化成了能量,然后能量又转变回物质。”但是他还是情不自禁的感觉到,某种东西确实已经失去了,在这个实验中,宇宙的某种东西已经被带走了,剩下的就只有一片空白。
本文摘自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第五章 自由与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