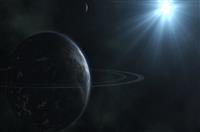“你都能记得些什么样的梦?”我问干因塔扎,她在她的丈夫利亚塔扎之前来到我们的露营地,她同时也是皮特展特扎拉地区女性的领袖。
我们是在之前一天离开阿利斯—斯普林斯的,沿着狭窄的小路开了11个小时的车才来到皮特展特扎拉地区。戴安娜为我和我的妻子、女儿备齐了所有前往土著地区必需的特别通行证。我们还请干因塔扎的表姐作为荒野向导。她是一个和善的女人,带着迷人的微笑,有着一双非常细的腿。她的丈夫在阿利斯住院,她原本在那里照顾他。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孙子,这男孩有着深色的脑袋,上面梳着一圈极为精细的淡亚麻色小辫子。他一路上安静地躺在祖母的膝盖上。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坚固的老汽车,那是一辆很适合做骆驼香烟的广告的汽车。我们就在这辆车里一路颠簸在荒野的小道上。他们两个都不会说英语,而戴安娜要顾着开车,所以我们就只能用微笑和富于表情的呼叫来沟通了。当我们到达露营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们摊开睡袋,完全没有意料到那漫天的星斗。我从没见过那么多星星,无尽深远的星云在漆黑色的天空中放射着光芒。
这天早上干因塔扎来到我们的营地,我们正在吃西方的花生牛油三文治,她靠着篝火坐下,那上面正煮着一铁桶的开水,她坐着,等着我们给她递上一杯茶。戴安娜很自然地向她祝福,那是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事实上二十年前戴安娜确实曾被干因塔扎家族收养过。在互相介绍完之后我们沉默了一会。我觉得自己很傻,一点都不知道与我的荒野老师相聚的任何礼节。这时她看到了戴安娜的儿子,六岁的克里斯多夫,她露出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微笑,这微笑一下子就跨越了我们之间的障碍。谈了一会儿之后我们都觉得自然了,我想是她先提起梦的话题的,她可能知道这是我这次来澳洲中部的目的。
她思考了一会儿我的问题,回答说:“别的人记得那些包含了舞蹈和歌唱的梦,这是别人记得的梦。现在我不做梦。”
最初,她这种区分被遗忘与被记住的梦的方法让我很吃惊。为什么她的人民只记得那些包含了舞蹈和歌唱的梦呢?我觉得这太专断了。在我沉默的时候,她又用皮特展特扎拉语向戴安娜说了更多的话。
“她的丈夫有一次看到一种新的舞蹈,然后就把它教给了人们。”戴安娜翻译道。干因塔扎再次强调了梦中的舞蹈和歌唱的重要性。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文化之间对于梦的理解有多么大的差异。她相信梦是为了她的人民而做的,梦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她告诉了我们她曾做过的一个梦:
我们围成圈跳舞。我们邀请所有人加入我们。圆圈变得更大了。
我马上想到了干因塔扎为扩展人民对土著文化的理解所做的一切工作。她曾邀请人民来到她的土地并谈论自然与土地这些大家都熟悉的话题。她的人们不情愿与欧洲人(指白人)分享知识,她努力改变着他们的这种思想。她是土著社区中出众的联络者之一,她把越来越多的外面的人邀请到他们之中,进入她的圆圈里。
在她讲完这个梦后,我评论说她的梦反映了她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努力,她努力让人民理解她的土地,努力扩展这个圈子。戴安娜翻译了我的评论。
干因塔扎很茫然,戴安娜花了差不多五分钟解释她的梦可能与她个人的生活有关。最后干因塔扎不冷不热地回答说:“可能吧。”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对她来说,梦就是属于人民的。梦与个人及内在心理相关的想法对她来讲确实是十分古怪的。我甚至不用再试着从包里翻出荣格学派的技艺了,从荣格学派的角度看这个梦,会认为这个梦关系到:在圆圈扩展中,她获得了关于自我以及完整的增长的感受。但又有谁在乎这个解释呢?我的解释完全不会影响这个梦对她的价值。很显然,在她的世界里,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属于她的社区的,比如说土地。梦对她就像土地一样,土地存在于它与人民的相互关系里,而对我们来讲,土地是属于个人的。如此,对她来讲,值得记住的梦时那些具有集体价值的梦,而我们则在梦中寻找对个体及自我的价值。但至少,我们双方都承认梦是具有某种价值的。
沉默再次出现了。古老的红色山脉俯视着我们的帐篷。小克里斯多夫的沙地里骑着那沾满尘埃的自行车。我那出于大学学龄的女儿还在熟睡。我们用车运来一大塑料桶的水,用来煮茶、煮咖啡和洗碗,当我被派去拿些水的时候,我觉得得到了解脱。桶里溅出来一些水,几只秃毛狗舔着那些还没来得及渗入那铁锈色的沙地的水珠。我妻子迪尼、戴安娜还有干因塔扎围着篝火在谈话,这让我想起一些土著绘画,他们用很多“U”字形围在用虚线构成的圆圈周围,用来表示围着营火的女人们。
就是在这个时候,利亚塔扎在一片扬起的灰尘中进入了营地。当他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向他做了个日本式的鞠躬,也许因为这是我唯一熟悉的外国文化的礼仪的缘故。他望了我一会儿,然后用皮特展特扎拉语向戴安娜喊了些什么,他们就大笑起来,我也故意咧嘴一笑,手里还拎着水壶。
我帮他把干木头从货车里卸到柴堆上,然后就又去洗大塑料桶里的碟子,戴安娜已经在里面注满了热水。我很高兴又感觉到自己在做熟悉的事情了。
戴安娜把所有的事都搁置起来,从露营顾问变回了人类学家和翻译的角色。我们就是在这会儿和利亚塔扎谈起了鹰的飞行的。
利亚塔扎要出去办些事,干因塔扎和她的表姐还留在这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继续问问题,但我很想知道关于“荒野电报”的事。这是在土著人之间使用的一种联系方式,对于我们西方的高等知识分子来讲那是不可能的。我是从大卫·泰斯博士那里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的。他是一位在墨尔本的教授,他十分出色并深受他人的敬重,他出生的阿利斯-斯普林斯,和土著人一起长大。他告诉我说,在学院训练期间他曾经休过一年假,为的是要感受一下真是的世界。他决定靠拣橙子为生,和土著人肩并肩地工作。这些土著人中有许多都与自己的部族完全失去了接触,他们住在澳洲大学城市的边缘,切断了与祖先的联系。
其中有一个和大卫一起拣橙子的人。一天,他突然转向大卫说:“我妈妈死了。当我捡起这个橙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就在那一刻启程,回到了千里以外的北部,正好赶上他母亲的葬礼。而在这之前并没有任何关于她生病的消息。
对于大卫讲的故事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并把它归于神秘现象,从此我就对荒野电报十分感兴趣。在我的工作中,我也常常会感知到一些我原本该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这正是我尝试锻炼的接收能力。
梦的工作会创造一种达到感应程度的亲密关系,它毫无疑问会引发许多无意识的行为,但是在这亲密地感应关系中进行的交流似乎并不是经由感官,不像是经由谈话或对姿势的观察,而是通过一种直接的、即时的对他人心理状态的体验。我把这种非同寻常的传送方式称为“共验交流(symbiotic communication)”。这种交流常为梦的工作带来惊人的效果,所以我十分想多了解它一点。在前往澳洲中部的途中,我预感到土著人会为我提供相类似的经验。
当我在悉尼教授实习课程时,一位女性告诉我,她曾获准为土著表演戏剧。她交叉往来于澳大利亚的各地,通常自己都不知道下一站到哪里。然而她却发现人们已经在荒野的小路上等着她的到来,他们说知道她要来,也知道她来做什么,这里没有电话,也没有别的旅行者领先她一步来传递消息。甚至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到达那些地方,通常她都只是随意走。那么他们又怎么会知道的呢?无论如何,过了几个月,她也像土著们一样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名实习生并不是为了引人注意而编造了这个故事。尽管她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但她的迷惑仍然是真实和深刻的。这又是一个神秘事件。
我不再理会荒野礼节的困惑,直接让干因塔扎直截了当地向我说明“荒野电报”的事情。她对我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向我们解释了它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我感到鼻子抽搐了一下或者有点痒的话,那么我就知道有陌生人要来了。”她事实求是地说。干因塔扎的表姐点着头,重复着她的话。干因塔扎像是在解释一种语法一样继续说着。“如果我感到臀部有什么东西,那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的配偶身上了。同样的,如果是我的上臂,那么指的就是我的姐妹或姑姨们。我的大腿则与儿子和舅舅叔伯们相联系。”当干因塔扎提到这些部位时,她的表姐也一边在自己身上拍着同样的位置。“这对于所有的皮特展特扎拉人都是一样的吗?”我问道,同时也被她那如此寻常的解释困惑住了。她们都点了点头,似乎这是每个人都通用的交流系统。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如此系统的、集体的、生理的超感官语法。
她们解释说这似乎只在某个亲属身上,他们就会从这个基础的电报语法获知。作为一种交换,我也讲了一个我们家的故事。
当我的侄女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哥哥就发现,只要我的嫂子一大盹,十五秒以内,在另一个房间的小婴儿就会开始哭闹。我哥哥是个头脑非常清醒的律师,他对此作了仔细的观察。他告诉我,每天他太太在上床睡觉前会看一会儿书,只要她一打盹,他就开始计时。几个月以来,时间从没有变过,十五秒钟一到,哭声准会传来。
那另外一个世界的两位女性完全理解我所说的。
这让我想起了同样也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研究,那是1967年在苏联进行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心灵感应最容易在家庭成员、爱人、儿时的朋友之间发生”。帕沃·那乌莫夫博士在莫斯科的妇产科诊所进行了他的研究,他说:“母子间的生物联系是无可争议的。在诊所里,母亲被放在离婴儿很远的另一个房间里,她们不可能听到婴儿的声音。但是,当婴儿哭泣时母亲也表现出不安。或者,当婴儿感到疼痛,比如在接受抽血检验的时候,母亲也表现出焦虑。而她此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医生在对她的孩子做什么。”这种与生俱来的心灵感应具有双向的联系,这是它存在的一个标志:当母亲处于某种疼痛时,婴儿也会哭闹。那乌莫夫博士总结说:“在我们的样本中有65%的人具有这种交流。”
在到澳洲之前,我举行了一次会谈,在那里我遇到一位十分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夏威夷本土老人,他用十分寻常的语气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当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和祖母散步,祖母望了望天上云彩的形状,然后说她的一位亲戚去世了。这确实发生了。第二天,消息从另一个岛屿传来,她提到的那位亲戚没有生病就突然死去了,时间就在他祖母看云的那一会儿。
到目前为止,对于这种神秘沟通方式的最完整叙述来自于20世纪的伟大探险家劳伦·麦卡特雷,他于1971年10月15日下午刚过3点的时候发现了亚马孙流域的源头。他的这个功绩来之不易,远比19世纪尼罗河源头的探险活动艰苦。在麦卡特雷发现亚马孙河源头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尼罗河是最长的河流。当用它三角洲的南运河进行估计之后,亚马孙获得了这项殊荣,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麦卡特雷的诚实和可信经得起考验,不容置疑。
他的故事被彼得鲁·波佩斯库忠实地记载于《亚马孙辐射束》当中,这是一本颇具影响的书,由彼得鲁和麦卡特雷一起撰写。在书的封套上写着:“亚马孙流域有一个迈奥鲁纳部落,他们是高傲的猫人,当麦卡特雷第一次接触这个部落时就遭到了他们的绑架,并且被深深地拉进他们那神秘而古老的文化当中。他发现自己在通过心灵感应与他们的头领巫师进行着交流……”
那头领巫师向麦卡特雷传递着复杂的“思想”,传递着他对于自己部落未来的伟大设想。在这些传递结束了一阵子之后,他才找到既懂葡萄牙语又懂迈奥鲁纳语的人为他进行翻译。在部落外几乎没有人懂他们的语言。在这被麦卡特雷称之为“辐射束”的交流之后,他们开始了口语的谈话,这些谈话完全证实了这位探险者与巫师间非言语对话时所传达的内容。
在他那西方科学思想的怀疑与轻视被驯服后,麦卡特雷翻译询问了关于神秘传递的事。他得到了一个简单的回答:这叫“古老语言”。头领巫师在自己的家族中世代相传或者是传给学徒。翻译只是知道有这种语言,但是并不会使用,只有头领巫师才会。
现在我很激动,我也想在梦的工作中通过共验交流来传递我的感受。
当对他人的梦进行工作的时候,我想告诉他我的体验,这些体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通常它们也反映了做梦者所体验到的气氛。
一些情绪似乎是客观存在于空间里的。它们就像是在梦里一样,是一种环境。
比如,在一个体验到害怕的梦里会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当在梦的工作中进入这样的梦的环境时,这种恐怖的气氛也会被梦的工作者直接体验为害怕的情绪。因此在倾听梦的叙述时,我体验我自己的感受,我的体验既是我个人的反应,同时也是心理“天气”的晴雨表。做梦的人把我带到梦的幻景里,她与此同时,也向我透露着她的“气候”。此刻,我最清晰的内在体验可能就是发生在我的内在系统里的她的“天气”。当清醒的意识尝试更接近梦的世界时,这种经验的和感情上的混淆就会发生。我不仅仅把个体理解为粒子,个体还是情感领域的接受点,个体可以像收音机接收电波一样接收别人的信息,或者可以像变色龙的皮肤一样,可以感应环境的色彩。
与材质之间产生共验,并通过对这种共验的自我观察而达到与材质之间的交互作用,这其实是西方意识历史里的一种古老技术。它被称为炼金术。它不仅仅是科学的前驱,也是一种对抗得力量,对抗日渐膨胀的客观观察,以及这种客观观察所导致的科学的霸权。在古老的炼金术中,存在一种流动的媒介,它由三方面组成:被处理的材质、工作中的炼金术士以及连接这两者的创造想象。通过自我观察,炼金术士参与了他所处理的材质的神秘世界,炼金术士成为一种媒介,材质通过他表现它自己。比如,当对铅做工作时,炼金术士体验到那称为抑郁的沉重与黑暗的忧愁。这不是由铅中毒引起的,他的情绪被认为是来自他做处理的铅的沉重的世界。同样的,在梦的工作中,梦的材料所表现得情感也会出现在梦的工作者的自我体验中。
皮特展特扎拉人通过对外部感官知觉的体验,形成了他们集体的语法。这是干因塔扎和她表姐为我提供的最好例证。这可用来说明人类有能力即时地参与到他人的经验当中。我很想继续问问题,但是利亚塔扎这会儿不在,我决定等待。
(本文摘自心理分析新视野丛书之罗伯特·伯尼克所著的《探索梦的原野》)
—————————————————————————————————————————
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创办人:申荷永
研究院简介:http://www.psyheart.org/16/12.html
研究院QQ群:79448734
电话:400-878-3393
官网:http://www.psyheart.org/
专业学习论坛:http://www.psyheartbbs.org/forum.php
申荷永新浪微博:“荷永”
申荷永新浪博客:“洗心岛”
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关注“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每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