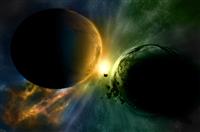窗微合着,半开半闭,阳光退出院子,不疾不徐地。屋外菊花开得亢奋,一段和煦时光。外婆依在沙发一处,拥着她的毛毯——应是母亲幼时的毛毯,那如点点秋水般的眸里,藏着一整片星。
怀念外婆,是从一段古远的菊香开始的。
菊花是厚重的,在我看来。花期一瓣瓣各忙各的,花的颜色,无非也就是橘黄一朵,雪色一朵,胭脂红一朵,争吵着,哗啦啦就开了。萎时,只余着一支枯败的梗和孤零零吊着的蕊,在寒风里发颤。花瓣里掖掖藏藏的纹路怕是与外婆的皱纹商量着生长,于是花开得欢乐就在外婆的额上的沟壑里安逸的栖着。她的眼睛浅浅眯着,没有一丝杂质,像是黎明叶尖上的露珠。
母亲说外婆喜欢拿着扫把,将院子里外打扫干净,她的眸中容不下一粒灰尘。然后握一把小剪刀,坐在院前,细心修剪着花枝。一簇簇雏菊在砌过的花坛里,明媚的仿佛要唤回春天。
外婆在园前挑拣,我自以为,外婆的一生恰是一朵开在岁月长河里不败的菊。
我没有见过外公,幼时并不在意是否有这么一个宽厚的背供我做一场儿时的游戏。长大了,方才知道外公的早逝。三毛说
:“也许爱并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年深日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兴许如此,所以当外公逝去后,对于外婆来说也只是失去了生活的一部分。思念至深,也是淡淡的。她未曾在我面前落下一滴眼泪,对于她多舛的一生来说,丧偶是上天对她开的最大的玩笑——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公婆需要她。她变得异常坚强,做工之余,还兼顾了做麦芽糖的重活。一双粗糙又变形的手,哭诉着她一生的悲痛,如沙漠胡杨的根,不甘且挣扎着,把手抓向了天空。所有疼痛是水槽里满载的水,多一滴就会溢出。
可她笑呵,她唱啊,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如孩童般俏皮的上翘着,那是一种经年不朽的好看弧度。她唱:“新中国的天是明朗的天……”世间带给她无尽的伤痕,她却报之以欢快的歌谣。
中午十分,母亲的心突然一阵绞痛,然后发疯似的跑向外婆的病床前,让小舅舅扶起外婆。彼时外婆眼角流出几滴不忍离去的泪,然后沉沉睡去。屋外几朵未凋零的雏菊仿佛诉说着外婆一生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