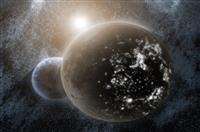父亲的年青时代,结交过许多蒙古朋友,个个是豪气万丈的汉子,血管里流的是成吉思汗的血;个个是喝酒赛马的好手,跨上马,能望见的地方皆是天下。那段只属于父辈的,壮志未酬的奔腾年代,如今我只能从他们的酒桌上略知一二。
我头一次踏上草原,人还没马脖子高,得父亲抱我上马背。父亲熟练地翻身上马,我坐他身后,看蹄下浅草逐渐化成一片迷离的影。父亲先扯着马不让快跑,待到山脊梁了再纵马下隘口。枣红马嘶鸣着斜冲而下,一路扬起遮天蔽日的黄沙,好像天上的太阳也撵不上地上的马尾巴。营地东边漫过一阵潮水似的云彩,牧民们正把羊群赶到山阴处去。
当时,我的心中尽是兴奋,害怕半分也无,因我知道父亲决不会让我摔下马去。
等我长高些了,力气大了,父亲终于让我掌马缰。不知怎地,只是他非要骑一匹马候在旁侧。我好不容易能痛痛快快放开来骑,路子也就特别野,什么单手握缰,半个身子挂在外边去捞草海上的花儿,就是那些牧民都不常去的野场我也非得跑上一跑。总而言之,我胆子特别大,命却不能跟着大,每年都有几个不慎坠马的被他们受惊的坐骑踏死。多年后我得知,父亲诸如此类的坚持,只为意外来临时他的女儿不至于和那些人一个下场。
说到底,我与父亲乘的还是同一匹马。
我已很久不见父亲骑马,只是有时想起父亲与他的老朋友喝醉了击杯大笑,笑里旧日豪迈一晃而过。父亲是否把过往也付了一杯残酒呢?我不知道。七月又上草原,我早已经能够熟练驰骋。只有很少的时候,我会将自己与父亲当年策马疾奔的背影混淆,仿佛不经意间低下头,看到的仍是他紧握马缰的手。父亲仍没有上马的意思。我跑出一段,勒马回望,父亲手插裤袋,挺拔有力地站着,好像刚做成一件什么大事。夕阳在他背后下沉,像个烧红的煤球,将他整个身影照成黑糊糊的一片。
我突然想到,父亲所谓一辈子的事业,其实一人而已,然而这人不能给他多少,却要花去他的半生。从小到大,从第一次跨上马背到独自一人纵马狂奔,他握住我缰绳的手一点点松开,我也一点点离他远去,奔向更广袤的天地。因为他懂,直到生活这匹烈马不可能再将我摔下,直到我征服生活如同驯服我骑着的马,到那时,他会放手,注视他唯一的女儿奔向远方。
而我也将懂,懂他的路他的苦他的人生。
“爸爸——”一个声音在草原悠长的薄暮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