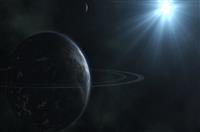姥姥家的那条巷子很美。
绿树掩映之中,整齐的瓦房和陈旧的草屋交错杂陈,恰似一盘杀得正酣的象棋子儿。早晨,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好几户人家的房顶上就冒起袅袅炊烟,似云似雾。
姥姥家在一条小巷的深处,十分清静。挂满丝瓜、豆荚的篱笆上,绿油油的叶子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下,给人一种幽美、恬静的感觉。
小时候,姥姥家的院子是我的乐土,它承载了我童年时期的幸福时光。
院子里种着许多水果,有葡萄、梨、苹果、草莓和橘子。最让我喜欢的便是那葡萄架和葡萄了。
几支枯木干架起了整个葡萄藤。枯木的树皮已经风干裂开,露出了浅棕色的木杆,与枯木成明显对比的则是那绿得发亮的葡萄藤。
每逢葡萄结出来的时候,姥姥就会和我一起拿着剪刀将熟透了的一串一串的葡萄剪下。姥姥长得比我高,所以她很容易就剪下一串,而我只得在一旁端着盆子接葡萄,“菲菲!接住了啊!”姥姥慈祥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好的!”我举着大盆子,随着葡萄的位置来回移动,一会儿跑到左边,一会儿跑到右边,“哐当”一声,一串葡萄乖乖地落在了我的盆子里,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耶!成功了!
”我高兴的欢呼。
我迫不及待地将新鲜的葡萄拿去冲洗,忽然发现,姥姥家的葡萄竟是极好看的。熟透了的,紫里透着蓝,蓝里仿佛又透着红,比紫水晶还要美;没熟透了的,绿里透着黄,黄里仿佛又透着白,比翡翠还要美。放入口中,入口即化,甜甜的。葡萄呀!它可调皮了,只给你尝一点甜头。于是就这样,我似乎一个人把整个葡糖架上结出的葡萄都吃光了。
葡萄架边上,还有一个“老爷爷”。
它可老可老啦!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已经长得特别粗壮了。小时候我最爱的一件事莫过于荡秋千,姥姥姥爷知道了,便在它的树枝上系上两条粗粗的麻绳,麻生下方拴着一块小木板,我整天就坐在上面荡呀荡呀,从日出荡到日落,从不觉得厌烦。
“你说,它都这么老了,怎么结出的梨子还是那么的甜,那么的好吃?”我常常好奇地问姥爷。
“它想让你开心呀。”姥爷笑眯眯地看着我。
几年之后,姥姥家装修,水泥代替了青石砖。那个葡萄架,那棵梨树,那一片草莓都已成为过往,只剩下苹果树和橘子树孤独地呆在哪儿。
小巷深处的故事,一直住在我的心理。我距离它越远,它却变得愈加清晰。